
历史这东西真真假假,尤其是文官拿着笔的时候,能把有些皇帝写的是非特别多
就比如说朱见深!
清朝人编《明史》,一提到他,总绕不开那几件事: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万贵妃,一个叫汪直的太监,还有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西厂。
那他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呢?会被史书这样记载?。
要说原因吗?也挺简单的,就是这位皇帝在位的时候,差点把清朝老祖宗建州女真给灭了。
这仇,打不过还写不过了吗?
1464年,朱见深刚接班当皇帝的时候,那局面可真叫一个惨淡。
他爹明英宗朱祁镇,之前御驾亲征玩脱了,在土木堡被蒙古人俘虏,大明的脸面和几十万精锐一块儿丢得干干净净。
虽然后来侥幸回来又复了位,但留下的朝局简直是个火药桶:宦官势力尾大不掉,文官们忙着拉帮结派打口水仗,北边蒙古骑兵隔三差五就来叩关,辽东那片黑土地上,女真各部也开始蠢蠢欲动。
说是个烂摊子,都算客气了。
十八岁的朱见深,坐在这烫屁股的龙椅上,第一把火就烧得出人意料。他爹复位后,干过一件特别不得人心的事——冤杀了保卫北京的大功臣于谦。
朱见深上台才几个月,就下旨给于谦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还把他儿子召回来当官。
这一手,漂亮。等于向全天下宣告:忠奸善恶,我心里有杆秤,跟着我干,亏待不了忠臣。
朝廷上那股因为“夺门之变”和于谦之死而郁结的阴冷之气,总算是透进了一丝亮光。
这还不够。他还有个叔叔,朱祁钰。
当年英宗被俘,是他挺身而出当了皇帝(景泰帝),稳住了江山。
后来英宗回来复辟,把他废了,死后连个皇帝的名分和像样的陵墓都没有。
这事儿,一直是皇家一块不敢揭的伤疤,也是朝臣们心里的一根刺。
成化十一年,朱见深力排众议,正式下诏,承认他叔叔朱祁钰的皇帝身份,恢复“景泰帝”的尊号,并按帝陵规制重修了陵寝。
诏书里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景泰以往过失,朕不介意。
”这话听着是宽恕,实则更是安抚。告诉所有曾经在景泰朝为官、心里打着鼓的人:过去的事翻篇了,都安心做事吧。
就这么几招,朝廷里剑拔弩张的气氛缓和了不少。
他又重用了一批像李贤、商辂这样有能力、口碑也不错的景泰旧臣,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处理实际政务上。

眼瞅着,这个年轻皇帝像是个能稳住局面的人。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内部的疙瘩刚捋顺,外边的刀子就狠狠捅进来了。而且这一刀,来自一个将来会要了大明命的地方——建州女真。
首领董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看准了明朝辽东防务空虚,联合其他部落,频繁入寇抢掠。
到了成化三年,气焰嚣张到了顶点,竟然连续攻破连山关、开原等重要边镇,铁蹄所过之处,烧杀抢掠,超过十万边民遭殃,辽东大地尸横遍野,哭声震天。
告急的文书一封比一封血泪,重重砸在朱见深的御案上。
这一次,年轻的皇帝脸上没了犹豫,眼里闪过的是他祖辈朱元璋、朱棣才有的那种狠厉。
他没有再说什么“抚慰”、“羁縻”的套话,直接给前线将领下了死命令,核心就八个字:“捣其巢穴,绝其种类。”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不要击溃,要歼灭;不要赶跑,要根除。
他任命大将赵辅挂帅,调集京营和辽东精锐五万人马,同时以宗主国的身份,命令朝鲜出兵,东西对进,形成钳形攻势。
然而,朱见深并非一味蛮干。总攻发起前,他使了一招“阴”的。
他派了一个叫武忠的将领去“招抚”。
武忠有个特殊身份——他出身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算起来是“亲戚”。
董山一看明朝来使是“自己人”,警惕心大降,再加上或许也想趁机讨要更多封赏,便带着手下大小头目一百多人,大摇大摆地来赴宴。
结果酒过三巡,伏兵四起,这百来号建州女真的核心领导层,被一网打尽,全部成了阶下囚。
首领被擒,群龙无首,建州各部瞬间乱作一团。
直到这时,明朝大军才像出闸的猛虎,直扑建州女真的老巢(今辽宁新宾一带)。
这场战役,后来在史册上留下了一个冰冷而形象的名字——“成化犁庭”。
犁庭扫穴,顾名思义,就是像用铁犁翻耕庭院一样,把敌人的家园彻底摧毁。
根据明军当时的战报记载,这一仗打得异常残酷,明军分路进剿,“强壮就戮,老稚尽俘”,斩杀六百余人,焚毁营寨四百五十多座,牛羊物资掠夺一空。
被诱捕的董山在混乱中被明军处决,另一个重要头目李满住则在逃亡途中,被执行合围任务的朝鲜军队杀死。
这还没完,在此后的几年里,明军又组织了五次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务必斩草除根。

经此浩劫,建州女真元气大伤,部族星散,人口锐减,此后近百年间,再也无法对明朝辽东构成实质性威胁,边关获得了难得的安宁。
然而,历史在这里埋下了一个致命的伏笔:那个被明军斩杀的董山,正是后来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的五世祖。
这场几乎灭族的仇恨,像一颗深埋的种子,被爱新觉罗家族牢牢记住,在一百多年后,长成了参天大树,反过来吞噬了大明江山。
西北边陲,同样狼烟不息。
河套平原这片水草丰美之地,被蒙古鞑靼部占据,成了他们南侵明朝的跳板,就像一把刀子顶在明朝的腰眼上。朱见深在这里,启用了一位传奇将领——王越。
王越是个奇人,他是文进士出身,却有着不输任何职业军人的胆魄和军事天赋。
成化九年,王越做出了一个大胆得令人咋舌的决定:放弃消极防守,长途奔袭,直捣黄龙。
他亲自挑选了四千六百名精锐骑兵,人人配双马,携带干粮,借着风沙掩护,悄然出塞,日夜兼程奔袭八百里。
蒙古人根本没想到明军敢远离城墙,深入草原腹地。
当王越的骑兵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鞑靼人的红盐池老营时,蒙古人还在悠闲地放牧。
明军铁骑冲入营地,见人就砍,逢帐便烧,杀得鞑靼人魂飞魄散。
此战斩首三百五十五级,更重要的是焚毁了其积聚的大量粮草、毡帐和器械。经此一役,鞑靼部主力远遁,此后近二十年不敢在河套地区长期驻牧。
成化十六年,王越再次上演千里奔袭的拿手好戏。
他得到情报,蒙古小王子的王庭设在威宁海子(今内蒙古集宁附近)。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王越率精锐骑兵发起雷霆夜袭。蒙古人毫无防备,仓促应战,乱作一团,连小王子(达延汗)本人都差点被俘,只身狼狈逃窜。
明军缴获无算,再次给予蒙古势力沉重打击。王越这两次远程奔袭,彻底扭转了明朝在西北边防上被动挨打的颓势,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
除了东北和西北这两场硬仗,朱见深在位期间,还成功镇压了持续多年的荆襄流民大暴动,平息了广西的土司叛乱,实实在在地巩固了帝国的统治。

客观地说,正是他这二十三年的铁腕治国和积极拓边,把父亲丢掉的疆土和尊严挣回了不少,为他儿子孝宗朱祐樘那个被称为“弘治中兴”的治世,打下了相对安稳的基础。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对外强硬、屡建功勋,对内维稳、拨乱反正的皇帝,在清朝官修的《明史》里,被塑造成了什么形象呢?很不幸,他成了个近乎脸谱化的“昏君”样板。
清廷的史官们,花费了大量笔墨,津津乐道于他如何专宠万贵妃,甚至暗示他纵容万氏谋害皇子(此事历来争议极大,并无确凿证据);如何宠信太监汪直,设立特务机构西厂,搞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缇骑四出。
而对于他指挥的、差点将其先祖灭绝的“成化犁庭”,对于王越收复河套、夜袭威宁海的赫赫战功,要么在字里行间轻轻带过,语焉不详,要么干脆避而不谈,仿佛这些决定帝国命运的战事从未发生。
这种写法,简直是对历史彻头彻尾的高明“抹黑”。
他们把政敌阵营里一位有作为的统治者,硬生生描成了沉迷私情、宠信奸佞的糊涂皇帝。
这么一来,自己夺取江山的行为,不光显得顺天应人,反倒像是“替天行道”、拯救百姓于水火的义举。
所以后世读史的人,要是只抱着《明史》死啃,很容易就觉得朱见深是个荒唐君主。可要是把眼界放宽些,翻翻战场上的记载,看看他处理的那些棘手政务,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当大明朝走到中年危机、内忧外患缠身的时候,他被迫用强硬手段稳住全局。
他确实有缺点,比如太依赖身边近侍,这和他童年坎坷留下的心理阴影分不开;他的手段有时也格外狠厉,就像对建州女真的打击。

但他绝对不是平庸之辈,更不是《明史》里写的那种只懂沉溺后宫、任用小人的昏君。
朱见深被抹黑,根本不是因为他个人品德或能力不行,而是一场跨朝代的、精心策划的历史叙事战。
根源很简单,就因为他当年“成化犁庭”那把铁犁,挖得太深、太狠,伤到了后来胜利者的祖宗根基。
历史固然是胜利者书写的,但那些用刀剑刻下的痕迹,还有故纸堆里被刻意埋没的功绩,总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显露出本来的样子。
朱见深的故事就是这样。
他就像个被人故意涂花了脸的船长,在狂风巨浪里,用不算优雅甚至有些粗暴的方式,死死稳住了快要倾覆的船舵,为后人多撑了一段航程。
至于脸上的油彩是谁抹的,为啥要抹,那就是历史深处,另一段藏着幽暗心思的故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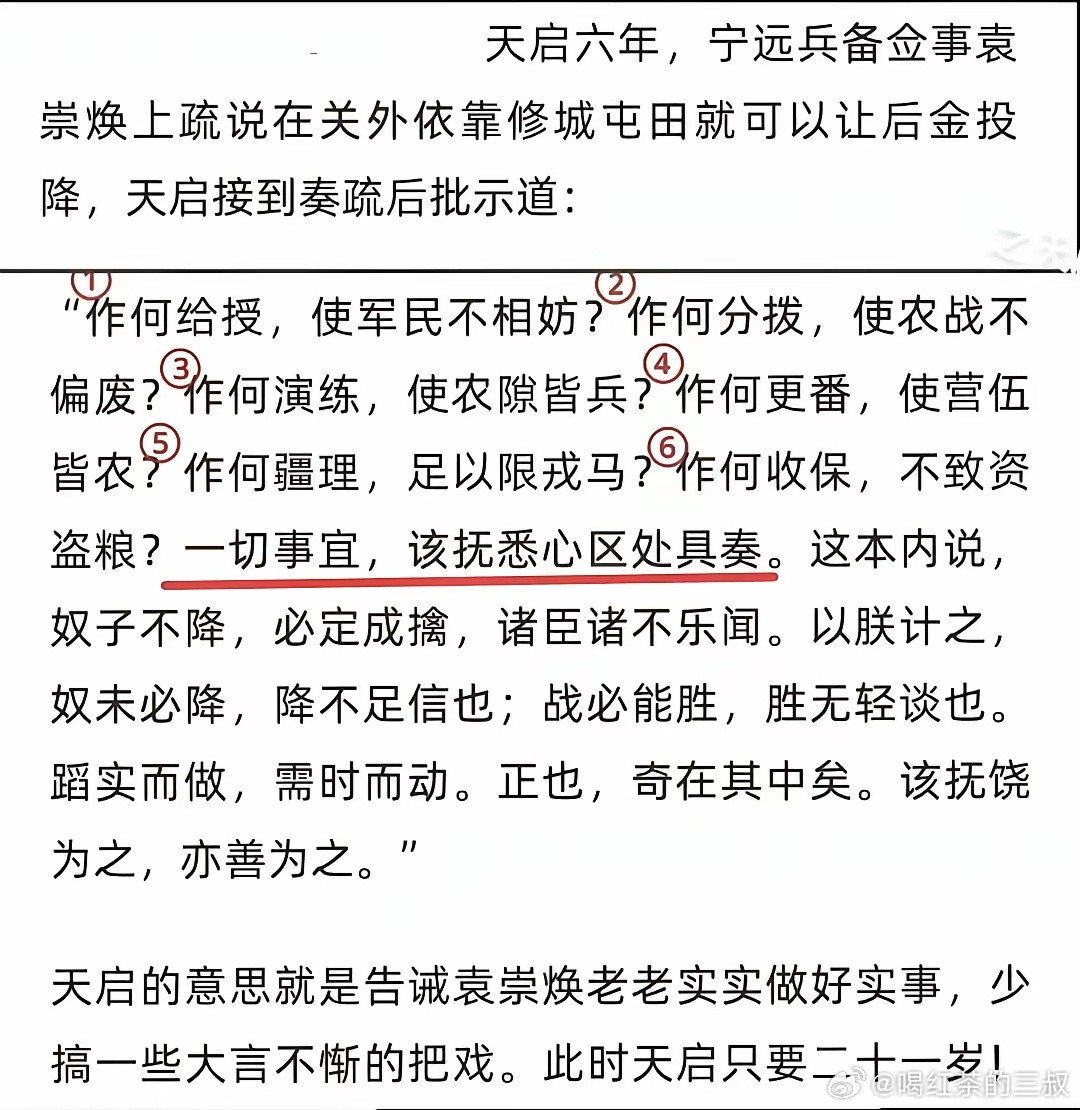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