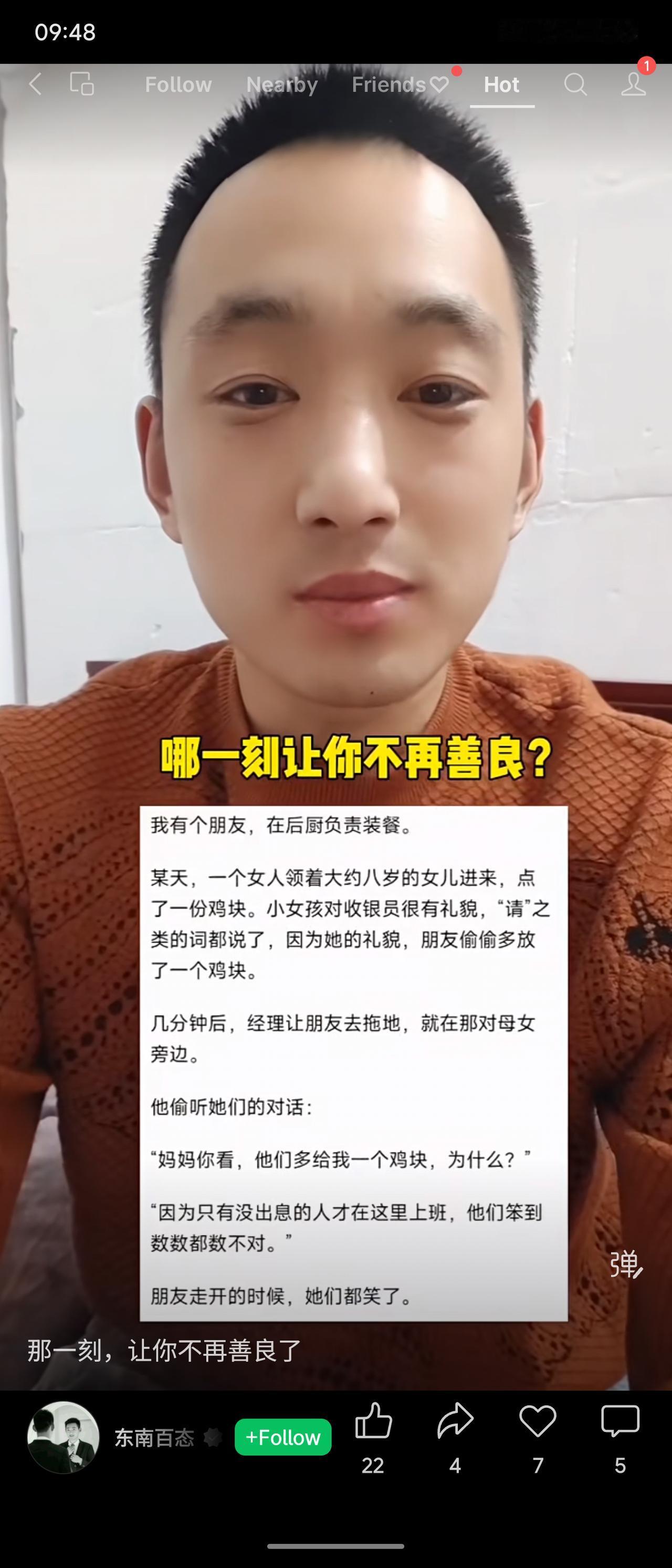我这辈子最痛的事,是背着亲手做的嫁妆进城送女儿出嫁,却连女儿的面都没见着。
我是个老裁缝,守着小镇上一间小小的裁缝铺,一辈子和针线打交道。就一个女儿,十八岁那年,她说要去省城纺织厂做工,我没拦着,只给她缝了一整套新衣裳,千叮咛万嘱咐,让她照顾好自己。
女儿走后,我每天守着裁缝铺,盼着她来信、盼着她回家。她每月都会寄信回来,说厂里的日子挺好,让我别担心。
转眼三年过去,一天,我收到了女儿寄来的包裹,拆开一看,是一双红缎婚鞋。
鞋面上绣着鸳鸯,针脚细密,一看就是她亲手绣的。包裹里还有一张字条,字迹娟秀:“爹,厂里给我介绍了个技术员,人很好,年底就结婚,您不用惦记。”
我拿着那双红绣鞋,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又喜又酸,喜的是女儿长大了,要成家了;酸的是,她要在外地扎根,不能陪在我身边了。
从那天起,我关了裁缝铺的门,日夜不停地赶制嫁妆。棉衣、棉被、床单、被套,还有我亲手缝的几件新衣裳,每一件都透着我的心意,我想让女儿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年底一到,我背着沉甸甸的嫁妆,坐了一天一夜的车,终于到了女儿所在的省城纺织厂。
按照女儿字条上的地址,我找到了婚礼现场。锣鼓喧天,张灯结彩,很是热闹。可我挤进去一看,整个人都僵住了。
新郎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哪里是什么技术员,分明是个干部模样。而新娘,穿着红嫁衣,戴着红盖头,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不是我的女儿。
我冲上去,抓住身边一个厂里的人,急着问:“我女儿呢?我女儿阿云呢?这不是她的婚礼吗?”
那人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一个劲地劝我:“大爷,您认错人了吧?这里没有您说的人。”
我知道,他们在骗我。我没走,在厂里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下来,每天都去厂里打听女儿的消息,一个个问,一个个求。
就这样,耗了半个多月,终于,厂里的一个老门卫,看不下去了,偷偷拉着我,说了真相。
他说,我女儿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厂里的党委书记。为了保住那个干部的前途,厂里就安排了一场假结婚,让我女儿嫁给一个快要调离的老工人。
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被送人了,而我女儿,被调到了遥远的边疆农场,还被警告,永远不准回来。
我听完,浑身发冷,像被人泼了一盆冰水,连站都站不稳。我可怜的女儿,她得多害怕,多无助啊。
我想起了那双红绣鞋,想起了她字条上的话,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不敢想象,她写下那些话的时候,心里是何等的绝望。
后来,我打听着,孩子被送到了城里的福利院,又被人领养了。我在福利院门口,蹲守了半个月,风吹日晒,不敢离开一步。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从福利院里出来。那婴儿的脚上,竟穿着一双红缎鞋——正是我女儿寄回来的那双,被人转赠给了这个孩子。
那是我的外孙,是我女儿唯一的念想。我激动得浑身发抖,起身就要冲上去认他。
可我刚迈出一步,就被福利院的院长拦住了。她冷冷地说:“大爷,这孩子是何局长领养的,你一个乡下人,别自不量力,惹上麻烦。”
我看着那个抱着孩子远去的背影,看着那双熟悉的红绣鞋,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眼泪模糊了双眼。
我终究,还是没能认下我的外孙。
我背着那沉甸甸的、没送出去的嫁妆,回了小镇。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嫁妆,都锁进了家里的樟木箱里,再也没打开过。
每年,到了女儿生日那天,我都会做一碗汤圆,放在院子里的空椅子上,就像以前,她还在身边的时候一样。我坐着,看着那碗汤圆,一言不发,坐很久很久。
转眼,十年过去了。
有一天,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找到了我的裁缝铺。他身姿挺拔,眉眼间,有几分我女儿的影子。
他说,他是我女儿的儿子,当年被何局长收养,如今考上了军校,特意来小镇,找他的外婆,找他的外公。
他从包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我女儿抱着襁褓中的婴儿,眼神空洞,没有一丝笑意,看着让人心疼。
我看着照片,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我多想,抱着他,告诉他,我是他外公。
可我终究,还是没相认。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双手工布鞋,那是我特意做的,尺码和他的脚刚好合适。
我把布鞋,塞进他手里,声音沙哑:“你妈……会做这个。”
年轻人接过布鞋,红了眼眶,重重地给我鞠了一躬。我别过头,不敢看他,怕自己忍不住,说出真相。
他走后,我坐在裁缝铺里,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手里攥着一双没缝完的布鞋,眼泪,一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