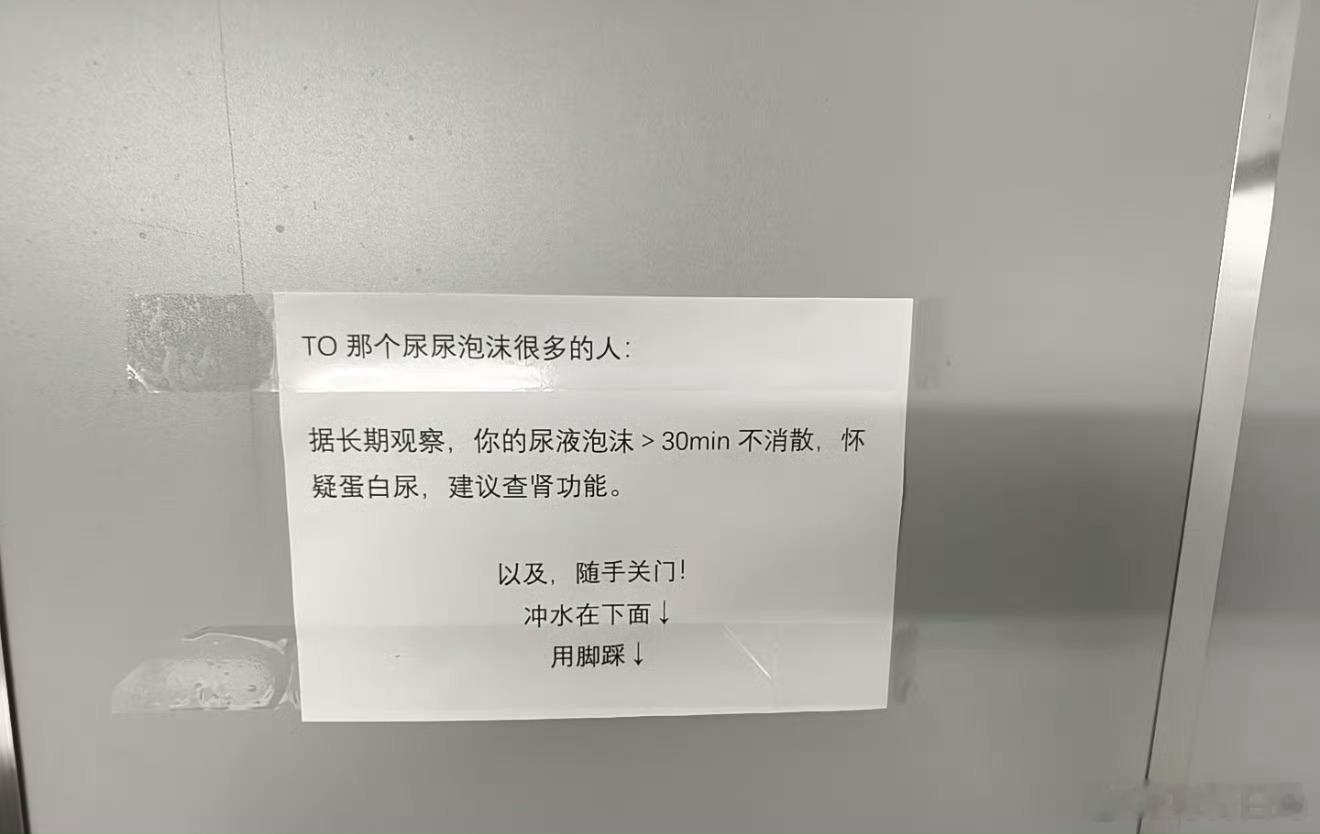我大伯四十八岁,在城里当仓库管理员十五年,右手搬货搬得变了形,最后却被公司以“业务调整”辞退,连一分补偿都不肯给。
他是从乡下进城的务工者,没什么文化,只会埋头干活。仓库里的货,重的轻的,他都一手扛,十五年下来,右手的指关节肿得老高,弯都弯不直,成了永久性的变形。
他以为,勤勤恳恳干活,就能安安稳稳干到退休,能给老家的堂妹攒够大学学费。
可没想到,公司突然通知他,业务调整,用不上这么多仓库管理员了,让他收拾东西走人,没有经济补偿,连这十二年的加班费,也说没有记录,一分都不给。
我大伯急了,他每天加班,有时候忙到深夜十点多,怎么可能没有加班费?可公司一口咬定,考勤记录里,他都是正常下班,没有加班痕迹。
他心里清楚,考勤机被动手脚了。每晚下班,他都用手机偷偷拍考勤机,指纹打卡的时间,总被后台篡改成正常下班点。
但他不怕,考勤机的边缘,总留着他右手变形的指印——那是他常年打卡,刻在上面的痕迹,擦都擦不掉。
他一共攒了三十七张照片,都拍得模糊,却能看清考勤机上的时间,还有边缘那道显眼的指印。
这些照片,他没存在手机里,也没藏在出租屋,而是小心翼翼地夹在堂妹小学的作业本里。
他跟老乡说:“纸比手机安全,他们就算找上门,也不敢撕孩子的作业,这是我闺女的念想,也是我的证据。”
协商不成,我大伯咬了咬牙,找了法律援助,把公司告上了仲裁庭。
仲裁庭上,公司的律师看着他拿出的三十七张模糊照片,冷笑一声:“单方拍摄,没有第三方佐证,属于无效证据,不能算数。”
周围的人都替他捏了把汗,我大伯却异常平静,他默默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泛黄的纸条,轻轻放在桌上。
那是工友们手写的便签,每张上面都写着“今晚加班至10点”“我和他一起加班到深夜”,落款处,有工友的签名,还有具体的日期。
“这些,都是和我一起加班的工友写的,他们都能作证。”我大伯的声音沙哑,却字字清晰,右手因为紧张,微微发颤,变形的指关节,格外显眼。
律师的脸色变了,再也没了之前的傲气。
没过多久,仲裁结果出来了——支持我大伯的诉求,公司需支付他十二年的加班费,加上违法辞退的赔偿金,一共八万二。
听到这个结果,在场的人都替他高兴,可我大伯没有欢呼,也没有笑,只是慢慢站起身,走出仲裁委。
他蹲在仲裁委门口的台阶上,掏出手机,拨通了老家的电话,声音温柔得不像话:“闺女,爸赢了,爸的指纹……能换你大学学费了。”
电话那头,堂妹的哭声传来,我大伯挂了电话,用粗糙的手背,擦了擦眼角的泪。
半年后,在之前上班的工厂门口,多了一个小小的修鞋摊。摊主,正是我大伯。
他的修鞋摊很简单,一张小马扎,一个工具箱,摊位的显眼处,贴着一张小字条,字迹歪歪扭扭,却看得清清楚楚:“免费帮工友修考勤卡”。
每天,都有工友来他这里修考勤卡,他一边修,一边跟大家说:“考勤卡要保管好,加班的证据,更要留好,别让自己的辛苦,白白白费。”
他的右手依旧变形,却稳稳地拿着针线,一针一线,修着工友们的考勤卡,也修着那些和他一样,在城市里默默打拼的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