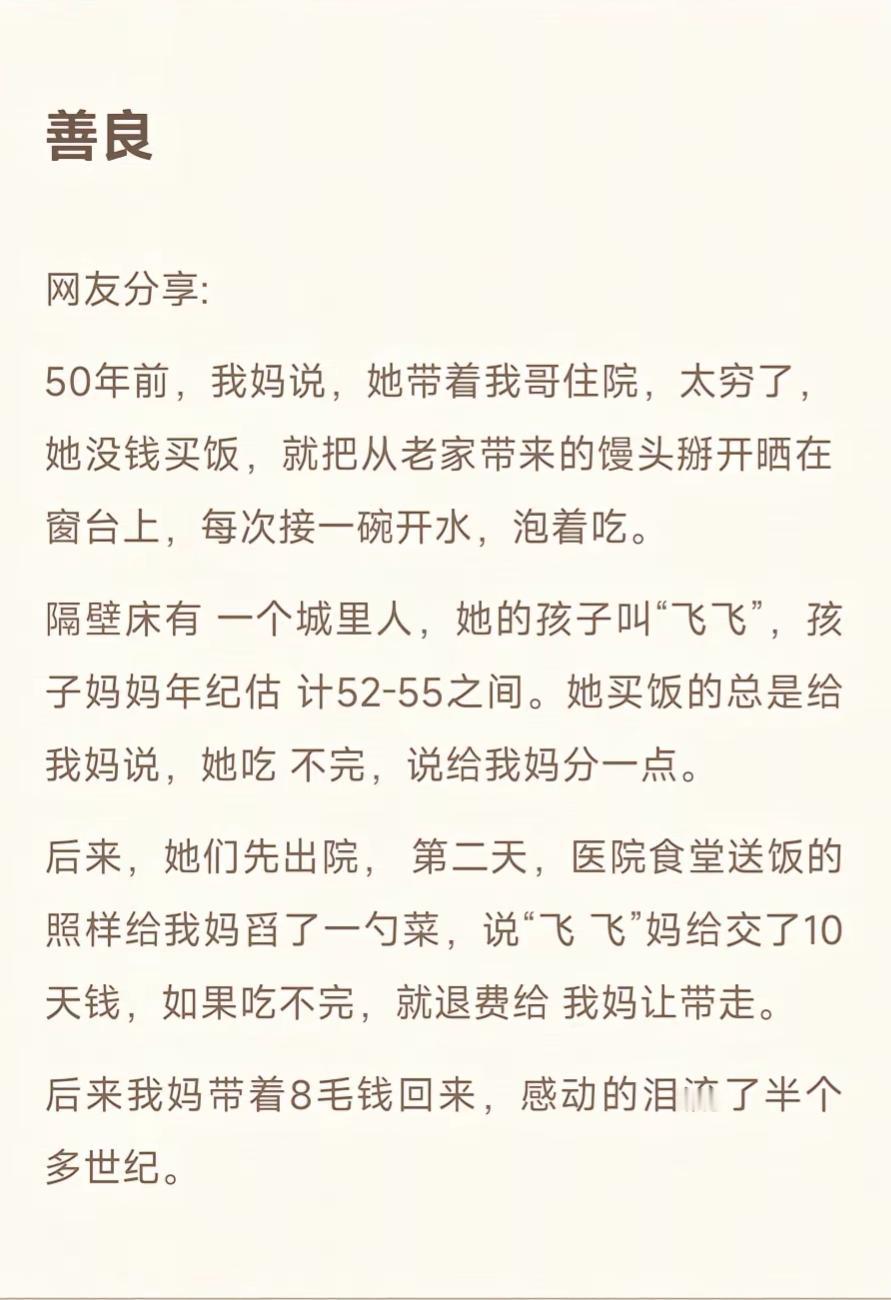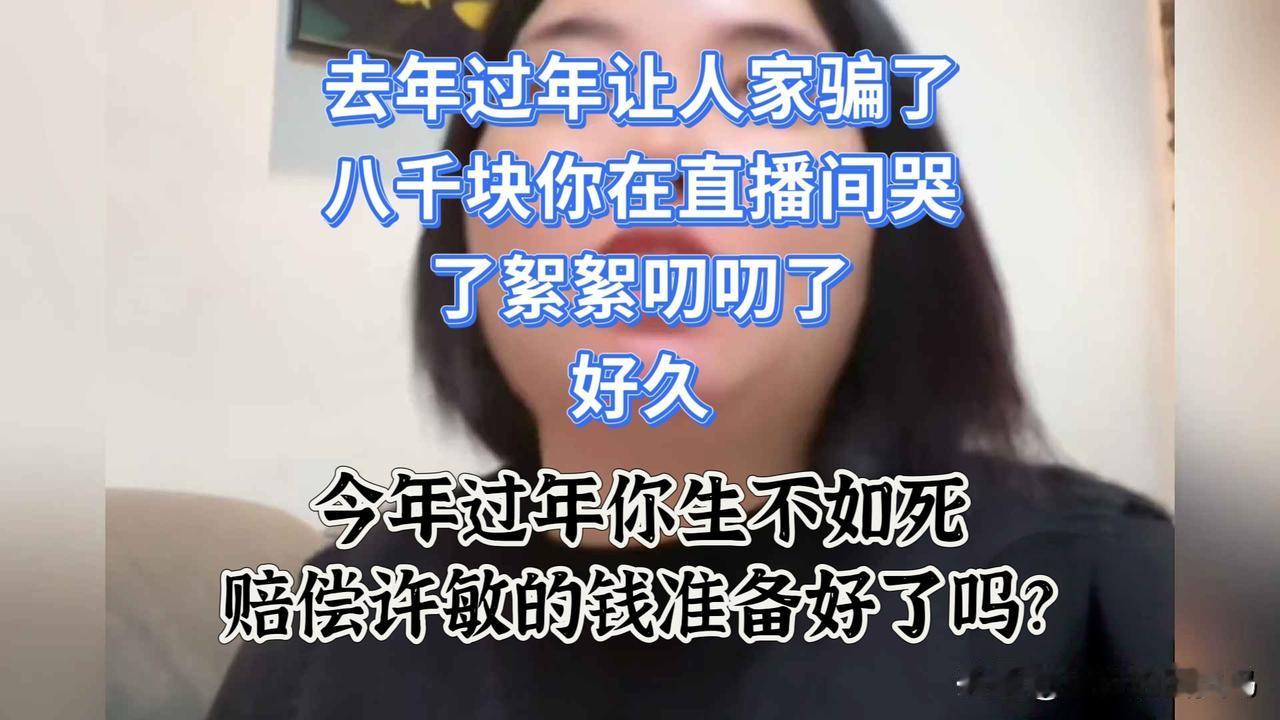我二叔火车司机退休,每月退休金八千五,一年小十万。二婶在社区超市打工,自己交社保,每月也能领一千八,俩人退休金年年涨,多活一年就多赚十万。 二婶天天把“多活十年就是一百万”挂在嘴边,管着二叔的烟酒,盯着他查体。二叔呢,笑呵呵地全应着。我们都觉得,二叔这是被“拿捏”住了。 可慢慢地,我觉得有点不对。二叔每月去医院那几天,回来总有些走神。有回我去他家,正碰见他戴个老花镜,在阳台的小本子上写写画画,我一走近,他就合上了。厨房里炖着汤,二婶在唠叨芹菜汁的好处,二叔“嗯嗯”地应着,眼神却飘向窗外。 那天下午,二婶去超市顶班。二叔忽然从屋里拿出那个小本子,招手让我过去。“侄儿,你帮叔瞧瞧,”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些地方,现在还能去不?”我接过来一看,愣住了。本子上密密麻麻,不是养生笔记,而是站名:陇海线的、京广线的,有些小站我都没听过。每个站名后面,还歪歪扭扭画着个小花,或者写个“豆沙包”“辣汤”。 “开了一辈子车,这些站我都记得。”二叔点了根烟——他偷偷藏的——深深吸了一口,“你二婶总说,多活一年,多赚十万。可我想着,要是能再用这退休金,把这些站一个个走回去看看,那才叫真赚了。”他翻到一页,指着“三门峡西”后面画的包子,“87年冬,在这儿困了八小时,站台有个大娘,硬是塞给我一袋热包子。” 我忽然懂了。二婶算计的是年岁,二叔惦记的,是那些被火车甩在身后的光阴和人情。 秋天,二叔真的行动了。他悄悄买了车票,说去老战友家玩几天。二婶帮他收拾行李,嘴里还在念叨养生经。我送二叔去车站,他背着旧帆布包,步伐轻快得像个小伙子。火车开动前,他冲我眨眨眼:“别告诉你二婶,我去给她淘换正宗灵宝苹果,她最爱吃那个。” 三天后二叔回来,果然抱着一箱苹果。二婶一边埋怨他乱花钱,一边迫不及待削了一个。她咬了一口,突然不说话了,抬头看着二叔。二叔有点紧张地搓着手。 “还是那个味儿,”二婶轻声说,眼圈有点红,“三十多年前,你第一次跑车回来,给我带的就是这个。” 后来,二叔还是定期去医院,二婶也还是熬芹菜汁。但他们的生活里,多了一些别的内容:偶尔会一起翻出旧地图,指指点点;二叔的收音机里,常放起那些铁路沿线省份的戏曲。阳台上,二婶养的花旁边,多了二叔捡回来的几块奇怪的石头,他说是从老站台上带的。 有一次,我听见二婶在电话里跟老姐妹说:“……钱嘛,够用就行。我现在觉得,人活着,心里有点惦记的事,也挺好。”窗外,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安静地交叠在一起。
猜你喜欢
严查陈小群,成了网络流行语。现在坐庄的都是打一枪换个地方,不像以前的长庄,最后
2026-01-16
方向在向上
世界上有两个字,叫善良网友说,50年前,妈妈说,带着我哥去住院,太穷了没钱买饭
2026-01-16
咪咪等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