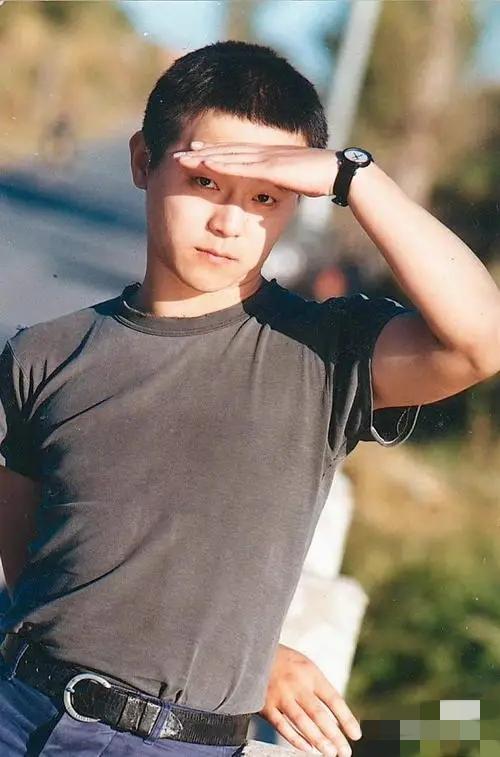1994年,26岁的 杨澜非要和银行上班的丈夫张一兵离婚,转身嫁给了体重200斤,身价百亿的 吴征 ,有记者问她:“你嫁给吴征,是因为钱吗?” 1994年的北京,秋意已经浸进了胡同深处。杨澜拖着行李箱站在央视大楼门口,刚录完《正大综艺》的样片,领带夹别得一丝不苟,可心里的波澜却没处安放。她掏出钥匙打开家门时,丈夫张一兵正在厨房炖着排骨,砂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是她从小爱吃的玉米排骨汤。 “回来了?”张一兵转过身,白衬衫袖子卷到肘弯,手腕上的电子表闪着绿光,“刚银行发了福利,给你买了条围巾,米白色的,配你那件风衣正好。” 杨澜看着他把围巾递过来,指尖触到柔软的羊毛,突然觉得喉咙发紧。“一兵,”她深吸一口气,“我想离婚。” 张一兵手里的汤勺“当”地掉在锅里,溅起的油星烫红了手背。“为什么?”他的声音很轻,像怕碰碎了什么,“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不是你的问题。”杨澜别过头,不敢看他的眼睛。这段由父亲牵线的婚姻,曾是亲友眼里的范本——张一兵是银行的业务骨干,做事踏实,会在她晚归时留一盏灯,会把她爱吃的菜摆在面前。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当她在镜头前和各国政要对话,当她深夜趴在书桌上改策划案时,两人之间的沉默越来越长。 “我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传媒专业,下个月走。”杨澜把离婚协议书推过去,钢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格外清晰,“我们……不是一路人了。” 张一兵盯着协议书上的字,看了很久,最后拿起笔,在末尾签了名。“我知道你志不在此。”他把围巾轻轻放在她手里,“去做你想做的事吧,别回头。” 那年深秋,杨澜提着行李箱走进纽约的地铁站,风裹挟着落叶卷过站台,吹起她米白色的围巾。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她是最勤奋的学生,笔记本上记满了关于媒体伦理的批注,课后总泡在图书馆,看遍了近十年的《纽约时报》合订本。有次赶论文到凌晨,她对着电脑屏幕啃着冷披萨,突然想起张一兵炖的排骨汤,眼眶有点发热,却很快被窗外的晨光驱散——她知道,有些路一旦迈开脚,就不能回头。 转机出现在一场华人媒体论坛上。1994年的纽约,枫叶正红得热烈,杨澜穿着黑色西装坐在听众席,听见台上一个声音洪亮的男人正讨论亚洲媒体的转型。“真正的传媒人,不该只做信息的搬运工,要做文明的摆渡人。” 她抬头望去,台上的男人穿着深色西装,身形壮实,体重足有两百斤,可眼神里的光却格外亮。那是吴征,上海出生,法国留学归来,在传媒投资领域早已崭露头角,身家过亿。他说话时不看稿子,手势有力,提到亚洲媒体的困境时,眉头皱得很紧,说到未来的可能性时,又笑得像个孩子。 茶歇时,杨澜端着咖啡走过去:“吴先生,您刚才提到的‘文化折扣’理论,我很认同。” 吴征眼睛一亮,像是找到了知音:“杨小姐对这个有研究?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中美媒体对比的项目,正缺你这样懂一线实操的人。” 那天他们聊了三个小时,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聊到央视的改版计划,从纪录片的叙事方式聊到卫星电视的覆盖难题。杨澜发现,这个外界眼里的“百亿富豪”,对传媒的理解比许多业内人士还要深刻,他能准确说出她每档节目的优点与不足,甚至记得她三年前采访基辛格时的一个小细节。 “你知道吗?”吴征突然说,“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见你,就觉得这个姑娘眼里有光。” 杨澜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后来他们一起去逛纽约的跳蚤市场,吴征会蹲在地上帮她挑旧唱片;她熬夜剪纪录片,他会默默送来热可可,说“再忙也得垫垫肚子”。他从不像别人那样只关心她的名气,而是会认真听她讲采访时的困惑,会在她被论文难住时,请来普利策奖得主给她指点。 1995年,杨澜和吴征在纽约结婚。有记者追到婚礼现场,举着话筒问:“你嫁给吴征,是因为钱吗?” 杨澜笑着理了理婚纱的裙摆,阳光透过教堂的彩绘玻璃落在她脸上:“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但买不到有人能听懂你凌晨三点说的梦话,买不到有人能陪你在图书馆泡到天明。” 她想起离开北京那天,张一兵说“去做你想做的事”。或许婚姻的意义从来不是捆绑,而是在某个阶段,有人愿意陪你走向更辽阔的世界。就像此刻,吴征牵起她的手,掌心的温度熨帖而坚定,她知道,这一次,他们要一起去看更远的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