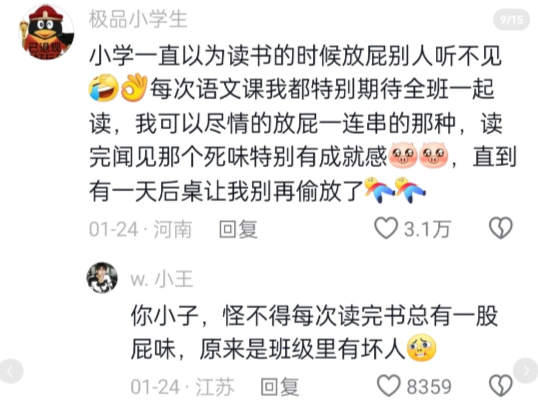每年一到这时候,我脑子里就得有两个小人儿打架。 一个声嘶力竭地喊:灌!必须灌!没那几串红亮亮的香肠挂在窗边,这冬天就算白过了! 另一个凉凉地说:忘了去年你是怎么发誓的了?忘了那满手的油,和最后那柴得能当柴火烧的“杰作”了? 真的,我快被自己这该死的执念给整疯了。 你说用后腿肉吧,瘦是瘦,吃起来干巴巴的,跟嚼木头渣子似的,没灵魂。 换前腿肉试试?好家伙,筋膜多得跟盘丝洞一样,切肉能切到你怀疑人生。 一咬牙一跺脚,上五花肉!结果呢,一口下去,半口是油,腻得我能当场原地去世。 年年灌,年年骂自己。 年年骂自己,开春风干物燥的时候,又开始想念那个味儿。 后来我琢磨明白了。 我折腾的哪是那几斤猪肉啊。 我是在折腾一种感觉,一种“啊,冬天来了,快过年了”的仪式感。 是那种亲手把一年的盼头、日头、念头,一点一点塞进那层薄薄的肠衣里,再挂起来,让风和阳光去给它上色、给它定味儿。 看着它们一天天变红、变干、变得紧实,心里就莫名其妙地踏实了。 所以,今年…… 算了,不说了,我再去趟菜市场。 你们说,这算不算一种甜蜜的“自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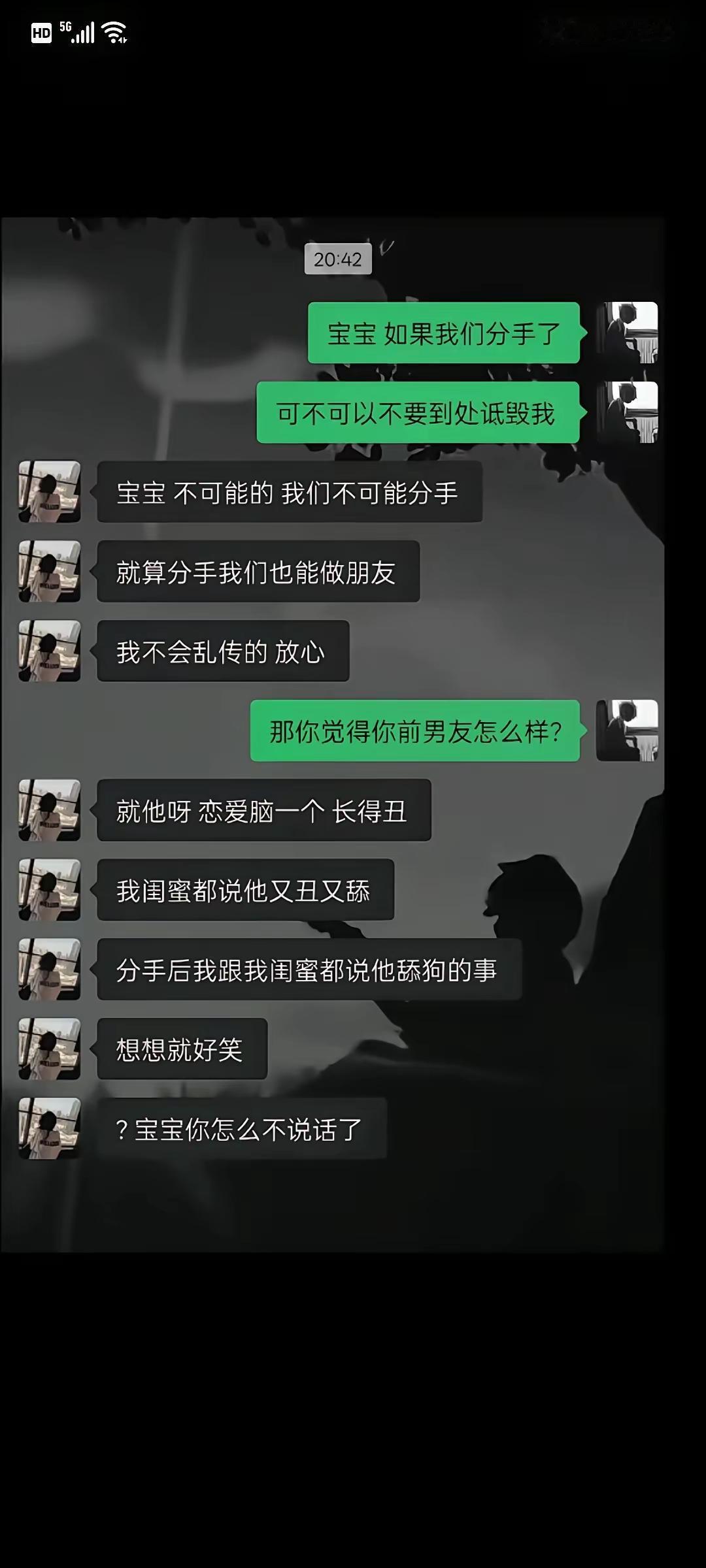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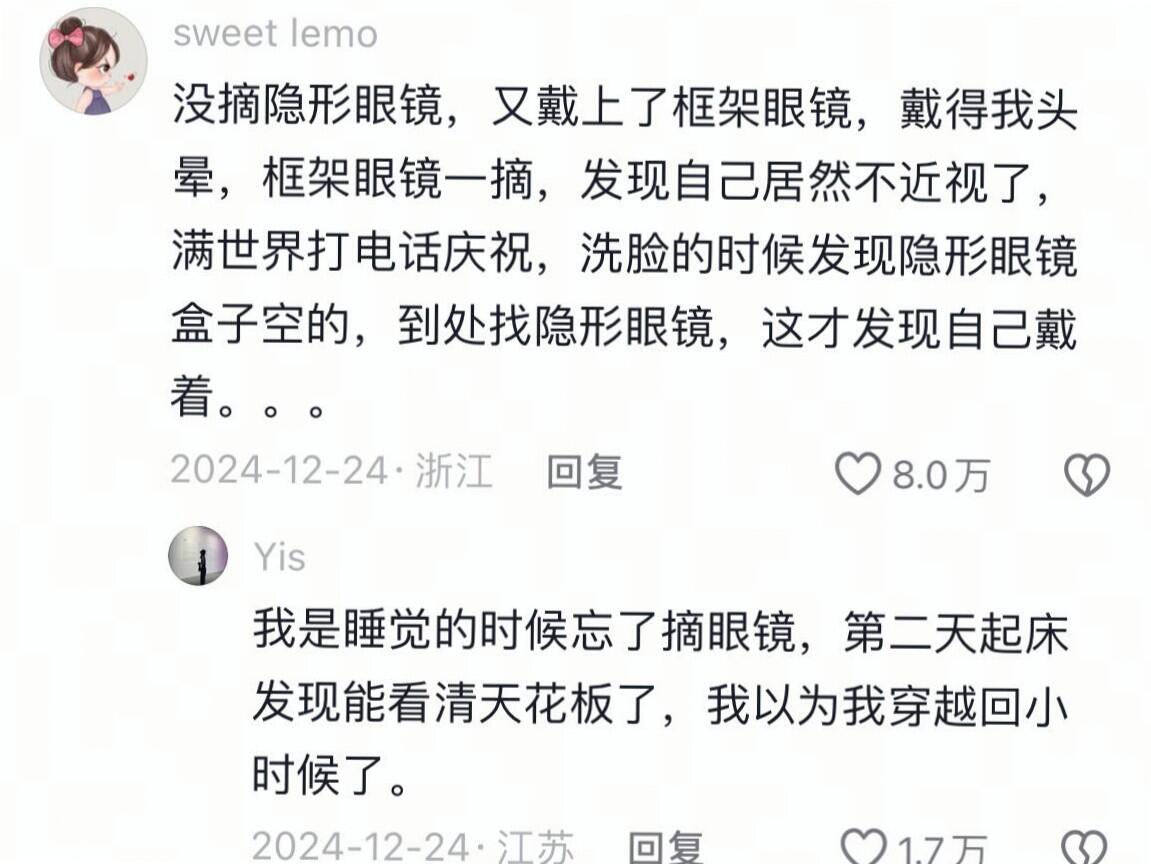

![好家伙,一句话要付邮费了[狗头]](http://image.uczzd.cn/18255230543578045607.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