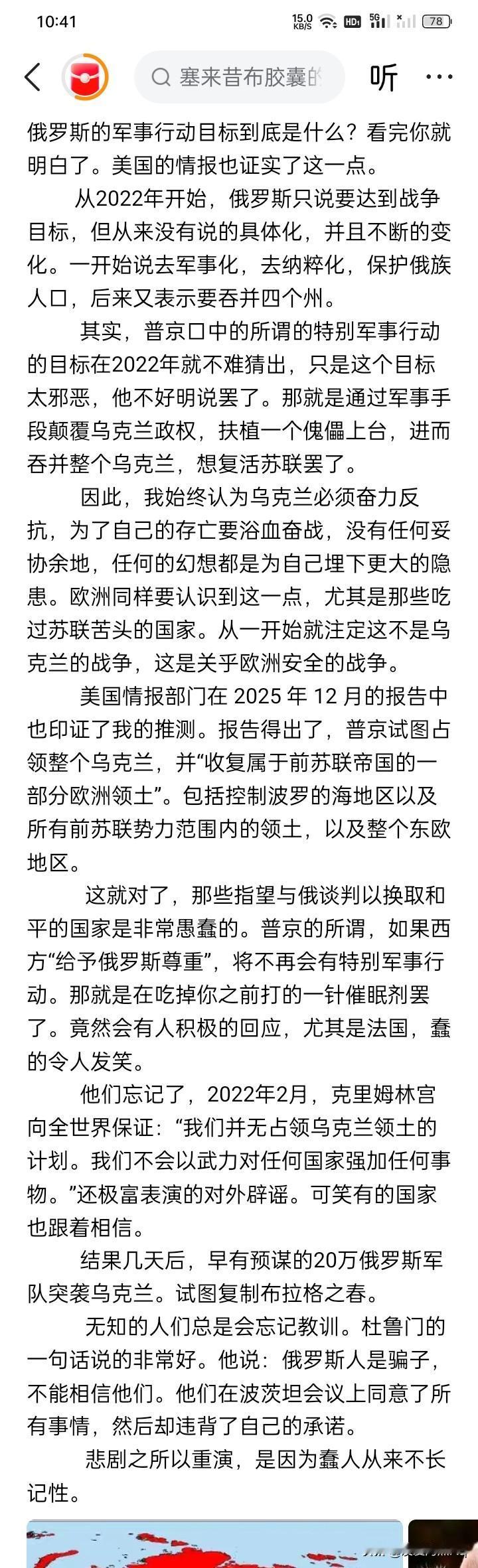1925年,物理天才薛定谔背着老婆,跑到别墅跟情人过圣诞节,可让人震惊的是,约会时他竟连发6篇重要的量子论文,不仅碾压海森堡,还开创了著名的波动力学。 1925年冬天,阿尔卑斯山的雪下得很实在,不是照片里那种好看的薄雪,而是一层一层压下来,把路、屋顶、围栏全盖住。 薛定谔和安妮玛丽住的那栋出租别墅,进出都不太方便,每天得先铲一会儿雪,门才能打开。 从外人看,这应该是一次很正常的度假,两个人,假期,远离城市,屋里有壁炉,有酒,也有足够安静的空间。 但真正住进去之后,安妮玛丽很快意识到,这趟行程恐怕不会按她预想的方式展开。 薛定谔几乎从第一天起,就没把自己当成是在度假,那段时间,他的情绪一直紧绷着。 德国那边,海森堡刚提出了一套新的量子理论,用的全是矩阵、算表和极度抽象的数学表达。 圈子里讨论得很热,但薛定谔越看越不舒服,他不是看不懂,而是觉得这种写法把物理问题变成了纯数学游戏,看不到图像,也抓不住直觉。 他更认可德布罗意提出的“物质波”想法,在他看来,如果电子真的像波一样运动,那就应该能用连续的方式写出来,而不是拆成一堆互相跳跃的数字。 这种念头在脑子里转了很久,到了雪山,反而被彻底点燃了,屋里的桌子很快就乱了,稿纸一张接一张铺开,写完就往旁边一推。 没多久,桌面不够用,他干脆坐到地毯上算,纸用完了,就找能写字的东西:信封背面、旧清单、厨房里那本菜谱的空白页,墨水瓶被他挪来挪去,经常差点被碰翻。 安妮玛丽有时候裹着毯子坐在一旁看书,一抬头,就看见他趴在地上,眉头皱着,嘴里小声念着推导步骤,叫他吃饭,他常常应一声,却要过很久才起身,饭也吃得很快,像是怕思路断掉。 早上更明显,她习惯慢慢煮咖啡,而他往往一边等水开,一边就在厨房的瓷砖边写公式,铅笔在白色瓷砖上划来划去,咖啡有时溢出来,在桌上留下一圈深色痕迹,他也顾不上擦,只是绕开继续算。 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天,几乎没有中断,当时的量子物理,正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老的理论已经解释不了微观现象,新的理论却彼此冲突。 海森堡的方法能算结果,但太难理解;德布罗意的想法直观,却缺少完整的数学支撑,薛定谔做的事,其实很直接:他想给“波”这件事,补上一套能站得住脚的方程。 在那几天里,他一步步推导,把原本模糊的直觉写成了微分方程,这些式子不仅能算出氢原子的能级,还提供了一种连贯的描述方式,让粒子的行为看起来不再那么跳跃、破碎。 有一天晚上,安妮玛丽忍不住抱怨,说圣诞节连教堂都放慢了节奏,他却还在算,薛定谔当时嘴里叼着一块没啃完的鸡肉,头也没抬,只回了一句:“物理不会等节日。” 这场在雪山里的“硬撑”,很快见了分晓,回到学界后,他把论文寄了出去,《物理学纪事》接连刊登了几篇文章,讨论迅速铺开。 很多原本被矩阵搞得头大的物理学家,第一次觉得量子问题“好像能看见了”,即便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也不得不承认,这套写法更容易使用。 后来,人们证明了他的波动力学和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但在实际使用中,更多人选择了前者,薛定谔的名字,也就此固定在量子力学的核心位置。 1933年,他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但他始终没有完全接受量子理论,后来越来越激进的解释方式。 1935年,薛定谔提出了,那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思想实验:把一只猫关在盒子里,让它在理论上同时处于生和死的状态,他的本意并不是宣扬这种荒谬,而是反问——如果理论走到这一步,那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讽刺的是,这个用来质疑的例子,后来却成了量子力学最出名的符号。 他的私生活同样不按常理来,他的妻子安妮,对他和其他女性的关系是知情的,也选择了接受。 陪他在雪山度假的安妮玛丽,并不是例外,外人很难理解,但这种状态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反而让他保持了一种奇怪的稳定。 晚年,因为局势变化,他离开奥地利,在欧洲多地辗转,最后在都柏林定居,那时的他不再冲在物理前沿,却写了一本小书,《生命是什么?》。 书不厚,也不晦涩,从物理的角度讨论生命中的秩序问题,几年后,这本书被沃森和克里克反复提起,成了他们理解DNA结构的重要启发来源。 回头再看那个被大雪包围的圣诞节,它并不浪漫,也不轻松,但很多关键的东西,往往就是在那种不合时宜的环境里被推出来的。 也许科学本来就需要这种状态——不那么体面,不那么舒适,但足够专注,足够执拗。 信源:澎湃新闻---成为文化符号的薛定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