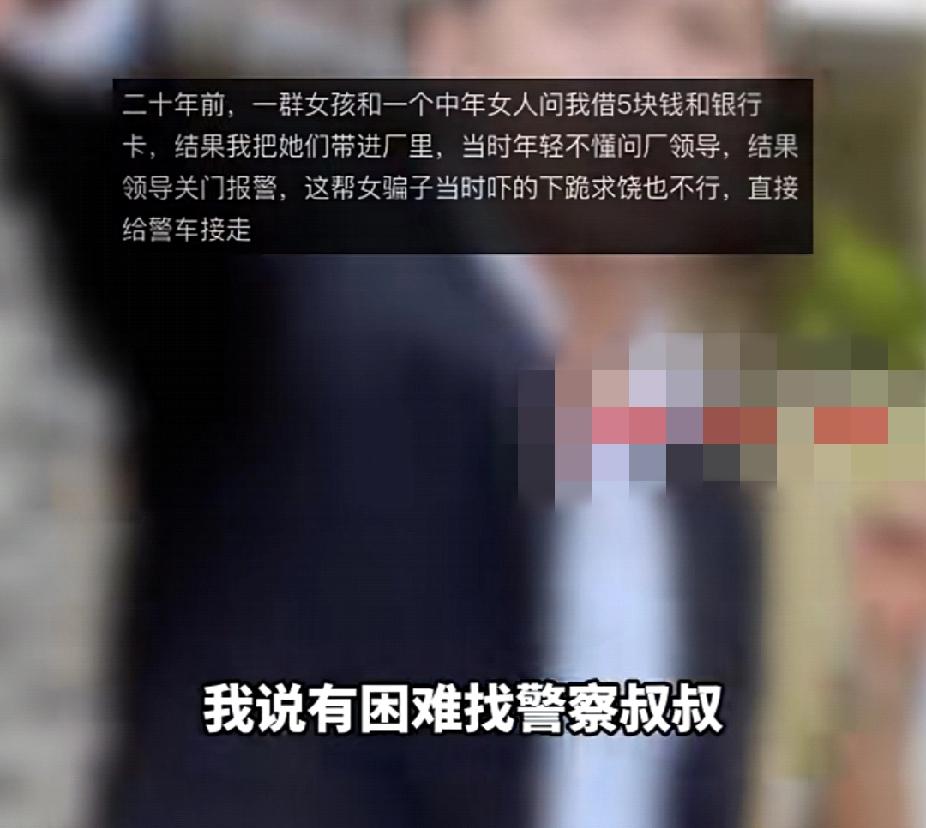渣滓洞监狱中,特务给女共产党员邓惠中上老虎凳时,无意中碰了一下她的脚底板,邓惠中猛地把腿收了一下。这一下,让特务眼前一亮,好像找到了折磨人的新招。 刑讯室的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冷风裹着霉味灌进来,邓惠中身上的单衣根本挡不住寒意,可她脊背挺得笔直,脚镣在青砖地上拖出“哗啦”的响,像在给这死寂的监狱敲警钟。 “邓惠中,别硬撑了。”领头的特务把烟头扔在地上,用皮鞋碾了碾,“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免得受这份罪。” 她抬眼扫过墙上的血痕,嘴角勾起点冷笑:“要我说的,早就说了——想知道游击队的下落?做梦。” 特务们被噎得脸色发青,其中一个瘦高个拽着她的胳膊往老虎凳上按,粗糙的麻绳瞬间勒紧了她的手腕和膝盖,骨头被死死卡在凳沿,动弹不得。她咬着牙,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这疼她熟——当年在山里打游击,摔下陡坡时骨头错位的疼,比这狠多了。 “加砖!”特务吼了一声,一块厚木板垫到她脚腕下。邓惠中闷哼一声,额头渗出细汗,却死死盯着天花板上的蛛网,像没听见似的。 第二块砖垫上去时,她的腿已经开始发抖,肌肉被强行拉伸,像要从骨头上撕下来。特务不耐烦了,伸手去掰她的膝盖,想让她彻底弯下腰,手指却没留意,蹭过了她的脚底板。 就这一下,邓惠中浑身猛地一颤,腿像被烫到似的往里缩了缩——谁能想到,这个在战场上能双枪打落敌机的女人,脚底板竟是天生的怕痒。 那特务眼睛突然亮了,像饿狼瞅见了猎物:“哟,原来‘双枪老太婆’还有这软肋?”他冲旁边的人使个眼色,“来,给她松松筋骨。” 两个特务立刻围上来,粗糙的大手在她脚底板上胡乱挠起来。邓惠中先是猛地绷紧了身子,想忍住,可那痒意顺着骨头缝往心里钻,比竹签钉进指甲缝还难受——疼能咬牙扛,这钻心的痒却让人浑身发软,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 “说不说?”特务一边挠,一边狞笑,“说了就停手。” 她死死咬住嘴唇,血腥味在嘴里散开,硬是把到了喉咙口的呻吟咽回去,换成一句骂:“狗东西……有种就给老娘来真的,玩这些下三滥的招数,算什么本事!” 可痒意越来越烈,她的腿抽搐着,浑身冷汗把衣服浸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有那么一瞬间,她真想大声喊出来,可脑子里突然闪过儿子的脸——她的儿子,也是共产党员,此刻说不定就在隔壁牢房里听着。她要是松了口,不光对不起组织,更对不起儿子眼里那声“娘”。 “停!”她突然喊了一声,特务们以为她要招供,得意地停了手。 邓惠中喘着粗气,头发黏在汗湿的脸上,眼神却亮得吓人:“要打要杀随便,别来这套。你们记着,我邓惠中活一天,就绝不会让你们得逞!” 特务们愣了愣,随即恼羞成怒,抓起旁边的辣椒水就往她嘴里灌。辛辣的液体呛进喉咙,火烧火燎地疼,她却死死瞪着那些狰狞的脸,喉咙里挤出断断续续的骂声,直到意识被剧痛淹没。 不知过了多久,她被拖回牢房时,腿已经肿得像馒头,脚底板还残留着那种诡异的痒意。同牢房的难友想给她擦药,她却摇摇头,扯出个笑:“没事……这点伎俩,困不住我。” 夜里,她疼得睡不着,悄悄摸了摸自己的脚底板,想起年轻时在山里,儿子总爱挠她的脚逗她笑,那时的痒是暖的,现在的痒却裹着毒。可她心里清楚,不管是疼是痒,只要这口气还在,就不能让敌人得意。 黑暗中,她蜷着肿得厉害的腿,轻轻哼起了山里的歌谣,声音轻得像风,却在寂静的监狱里飘得很远——那是给儿子的暗号,也是给所有难友的信:别怕,我还撑着。 (来源:澎拜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