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剧中的后宫,永远是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站在前台的,永远都是那些“花一样”的各宫妃嫔,但鲜有镜头落在那些服侍洒扫的宫女身上,她们最好不过是充当配角,最差则是走来走去的舞台背景,装点着宫廷这座锦绣牢笼的富丽堂皇。
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倒不必责备影视剧故意忽视宫廷底层,把他们当作背景工具人,而是因为她们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本就如此,来去都悄无声息。
只有少数人会在偶然间留下自己只言片语的故事。
当毛奇龄踏足京师时,已经是清朝康熙十七年,这位在明亡时“哭于学宫三日”的前朝遗民,如今已经因为献书得到新朝嘉赞,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的清贵官职,也正是在这座改朝换代门庭一新的京城里,他见到了一位前明宫女,她的故事本来不会留下只言片语,但出于某种历史的冲动,加上撰写碑文的稿酬诱惑,让他在《重修双关庙碑记》中写下了她的故事。
尽管已经垂垂老矣,但她还记得自己当年是怎样入宫的。那是前明万历年间,更确切地说,是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尽管她已经不记得具体年月,但她记得,那天,是万历帝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出藩洛阳的日子。那天,宫中尚寝局掌设女官在道旁看到了还是个小女孩儿的她,一眼便相中了她姣而晳的相貌,于是向她投来一个金罂,趁她低头拾取时,突然把她抱起来——她就以这样粗暴诱拐的方式进了宫,从此,便远离了她的父母,一道朱红色的宫墙禁锢了她的人生。
她侍奉了三代前明皇帝,终于因年老离开宫廷。毛奇龄的碑记记下了她入宫的开始,却没有记下她在宫中的生活,或许是宫中生活的悲苦,让她不忍回忆,毕竟她入宫的万历年间,侍奉的主人万历帝,正是一位虐待宫人的行家里手,在一封奏疏中如此描述道:
“臣义等窃见御前执事宫人、内官,或干圣怒责处发遣,络绎不绝,每致重伤兼患时疾而死亡者,殆无虚日。盖以圣旨钦传,即以本日动刑,而用刑者,因惧罪及于己,辄加数多酷责,而押解者复惧连累,日夜严加墩锁,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无一二。”
而万历帝的正妻王皇后,同样也嗜好虐待宫人,曾经随侍内宫的太监刘若愚,在他的私人笔乘《酌中志》中记述道:“中宫孝端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宫人及小宫人,多罹棰楚,死者不下百余人,其近侍内官亦多墩锁降谪。”
在这种棰楚荼毒之下,能活下来就已不易。也许她衰老的身体上,还残留着昔日虐待的累累伤痕,但这总不便于示人。
也或许她讲了,但稿酬并不足以丰厚到让这位大文人完整地写下她的故事。
总之,坐在那位垂着新朝辫发的朝廷新贵对面的前明宫女,如今已经是一位剃去三千烦恼丝的老尼姑。她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只有她的法号“静元”。
而这位前明宫女尽其衰朽残年栖身守护的那座双关庙,所奉祀的神灵正是千年前忠于大汉却功败垂成的名将关公。
以下内容选自《明宫彤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明宫彤史:明代宫廷女性》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进宫:赏与罚
宫人们伺候着皇帝、后妃们的生活起居,作为宫廷内的服务人员,她们会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除了每月按照规定应该给的月例钱,还会有额外的赏赐。《稗说》中记载:“凡宫中诸女侍……每日给花粉钱,月给鞋料帨帕钱。遇上行幸一宫,例有给赏。上下女侍有金银豆,金银八宝,金银钗、串落索等项,人各若干,设有定数。”可见,宫人们获得赏赐不仅仅因为勤勉任事,能讨得主上欢心,赏赐中也有依循惯例、例行公事的意思。宦官诸衙门中有银作局,便是“专司制造金银豆叶以及金银钱,轻重不等,累朝以供宫娃及内侍赏赐”。除了日常因循惯例的给赏,凡遇到宫中重大的节庆,又会有赏赐。《酌中志》记载:
祖宗旧制,凡万岁圣节、中宫千秋、皇贵妃千秋,则凡内执事、宫人并王体乾等,及山陵等处内官,各有赏例,每银一两以上。”帝后及皇贵妃生辰,相关服侍的宫人、内官都能得到赏赐。这样看来,宫人得到赏赐的机会似乎还是有很多的。但显然这也是有前提的,从以上记载分析,能经常得到赏赐的宫人需服侍宫中地位尊贵者,或者是在皇帝经常行幸的某一宫当差,否则也就只能拿着月例钱度日。

明代山西新绛稷益庙壁画中的明代宫女形象。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有赏自然有罚,宫人们若稍有不慎,行差踏错,惹怒主子,辱骂、受责在所难免,挨打甚至丧命亦不足为奇。史载,明成祖自徐皇后崩逝后“多任性,间或躁怒,宫人多惴惴惧”,全凭王贵妃“辗转调护,徐俟意解,自皇太子、亲王、公主以下皆重赖焉”。然而永乐后期出现了两起因妃嫔而起的宫廷杀戮,后宫妃嫔、宫人被杀者竟达3000人,可谓触目惊心,惨烈异常。明世宗亦是性情偏狭乖戾之人,在后宫中常因暴怒而责罚后妃,棰楚宫人,其中不乏因此殒命者。于是宫人畏惧亦积怨日深,最终导致了宫人对世宗的报复谋刺,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壬寅宫变”。史载:
嘉靖壬寅年,宫婢相结行弑,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腹绞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入解之,立缚诸行弑者赴法。
事后,涉及此案的两位妃嫔和16名宫女皆以极刑处死。
据《胜朝彤史拾遗记》记载,宪宗宠妃皇贵妃万氏晚年体肥,因用“拂子挞宫人,怒甚,中痰死”。万历时,太监田义、陈矩曾密谏神宗曰:
臣义等窃见御前执事宫人、内官,或干圣怒责处发遣,络绎不绝,每致重伤兼患时疾而死亡者,殆无虚日。盖以圣旨钦传,即以本日动刑,而用刑者,因惧罪及于己,辄加数多酷责,而押解者复惧连累,日夜严加墩锁,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无一二。如此致伤天和,岂圣世所宜有哉!……凡宫人病死者,即连累内官,或打一百二十、一百五十,性命难存。一人病死者,尚然可悯,况又波及无辜生命乎?令耳闻目见,哭声载道,怨气冲天,景象如此。若不披沥上奏,则是臣等贪禄恋位,畏死偷生,直犬马之不如也……
此段记载足见万历时对宫人、内官处罚之严苛与不近人情,人命如草芥一般。有罪受罚已不堪其苦,无罪遭责更是无妄之灾。神宗苛待宫人,其皇后亦多有恶行。《酌中志》记载:中“宫孝端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宫人及小宫人多罹棰楚,死者不下百余人,其近侍内官亦多墩锁降谪。”天启时,魏忠贤、客氏横行宫中,“客氏在内,时有勒死、箠死女升出太安门外”。由此可见,明代历朝皆有宫人遭帝后妃主责打甚至死于非命的事情发生。
《酌中志》中具体记载了明代后期惩罚宫人的方法:“凡宫人有罪者,发落责处墩锁,或罚提铃等名色以苦之。提铃者,每日申时正一刻并天晚宫门下锁时,及每夜起更至二更、三更、四更之交,五更则自乾清宫门里提至日精门,回至月华殿门,仍至乾清宫门里,其声方止。提者徐行正步,大风大雨不敢避。而令声若四字一句,天下太平,云云。神庙御居启祥宫时,则自咸和右门提至嘉德门,仍回原处止焉。”另秦徴兰《天启宫词》有注云:“昌、启之际,设扳著名色以苦之。扳著者向北立,屈腰舒两手,自扳两足,不许体屈,屈则夏楚乱施,立再移时许,其人必头晕目眩,僵仆卧地,甚有呕吐成疾至殒命者。正”是有了这些处罚方式,《天启宫词》有诗云:“十五青娥诵孝经,娇羞字句未分明。纤腰不忍教扳著,夜雨街头唱太平。”
除了身体上的折磨,宫女们还要默默承受着深宫中的寂寥、心灵的悲苦,身心不得自由,如同禁锢一般,宫墙之内不知郁积了多少宫女们深重的幽怨。
出宫:家何在?
明代宫人的最终归宿不外乎两种,或出宫归乡,或卒于掖庭,女官自然亦包括其中,只是因为她们有一定的品级、地位,所以晚景应当不会如普通宫女那般凄凉罢了。
洪武二十二年,授六尚局宫官敕时,对女官的去留便有了规定,即:
其外有家者,女子服劳既多或五载六载,归其父母从与婚嫁,妇人受命年高者,许归以终天命,愿留者听。
从这一规定看,女官们的去留确实并非强制的,她们在宫廷中服务数载后,便可以归乡,是去是留听凭自愿。
邱仲麟《明代宫女的采选与放出》一文中认为,明代宫女的放出经历了从主动到被动的过程。就女官放出而言,亦符合这样的过程。从洪武年间的情况看,凡是洪武年间入宫,又能在洪武年间归乡的如范孺人,因年老赐归;如陈二妹、江全,“以勤劳久”而赐归或派内官送归乡;如胡贞良入宫五年后,亦放归,她们在洪武年间服务于宫廷的年限皆不是很长,“服劳既多或五载六载”便能归乡,当不是虚言,且她们皆属赐归,而非乞归,也就是朝廷主动放出。但情况至永乐年间已不同了。成祖登基之初便下令采选女官,且规定“妇人年至五十愿还乡里,女子给事十年以上愿还家及适人者,俱从之”。这一规定实际上已增加了女官服务于宫廷的年限,且是愿意还乡者从之,言下之意,只要不提出还乡便继续在宫中服务,表十六中所列永乐年间及以后,便甚少有赐归回乡者,而多是乞归了。还乡时的年龄亦远高于50岁,如江全,再次被召回宫中又服务了15年,以年老乞归时已63岁;又如黄惟德,乞归时已是75岁高龄,在宫中服务了40多年。虽然年事已高,但至少她们最终荣归故里了。
关于明代中后期女官事迹的记载本就寥寥无几,放归情况仅能以个案进行分析。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的倪氏,当是在天顺三年八月下诏采选女官后,于天顺四年选入宫中,在天顺八年就赐还家了。而同一时期选入宫中的沈琼莲则没有这么幸运,沈琼莲在宫中服务了几十年,从《“女学士”沈琼莲及其宫词考证》一文中对其生平的考证可知,她在弘治十一年时因其家族之事已在宫外,但是后来又不知何故回到了宫中,最后很可能卒于宫中。那么沈琼莲的短暂离宫可能是因家事暂时告假,亦可能是已启请归乡后因其曾经在宫中的贡献而复召回。
明代中后期有大臣多次上疏,以宫中阴气郁结、恐致灾异为由,而行放出宫人之举,宪宗即位后的天顺八年、成化十五年和二十三年都曾放出过宫人,孝宗在位期间,曾于弘治四年议放宫人,但是否施行则不清楚。沈琼莲经历了成化、弘治两朝,成化年间正是其年富力强之时,而且又因有才华而颇受器重,所以不会在放出宫人之列。且选择放出的宫人多是考虑老病及不堪使用者,“留其有职务及不愿出者”,所以即便沈琼莲想出宫也很可能不被准许。弘治年间,沈琼莲尚在中年,且因试《守宫论》而更加得到皇帝的赏识并升官,即使弘治四年放出宫人之令得以施行,有才学且担任重要职务的女官是不会轻易被放出的,结合永乐以后女官乞请归乡的情况,不是因为老病而不堪任事了,恐怕也不能告老还乡,毕竟她们的地位、学识及所掌之事是不同于普通宫人的。而倪氏应该是在天顺八年的这批放出宫人之列,她为何能够在短短数载后便可回乡,不知是不是老病的原因。
归宿:一抔黄土
宫人中未及出宫者,终是离乡背井,卒于深宫。明代普通宫人死后,后事如何处理在明代的一些笔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万历野获编》记载:
内廷宫人,无位号名秩而病故,或以谴责死者,其尸亦传达安乐堂,又转致停尸房,易朱棺再送火葬。
《宛署杂记》中的记载更为详细:
盖专掌内庭物故宫女殡送之役者,名曰土工,疑于土掩,而实不然。静乐堂在都城西,阜城门外五里许,砖甃二井,屋以塔,南通方尺门,谨闭之,井前结石为洞,四方通风,即火所也。安乐堂在北安门内,有屋数楹。令甲,宫人有故,非有名称者,不赐墓,则出之禁城后顺贞门旁右门,承以敛具,舁出玄武门,经北上门、北中门,达安乐堂,授其守者,召本堂土工移北安门外停尸房(在北安门外墙下),易以朱棺,礼送之静乐堂火葬塔井中,莫敢有他者。凡宫人故,必请旨。凡出,必以铜符,合符乃遣……
我朝监古定制,委曲周悉,非有名称,不得赐墓,示有等也;非合铜符,不得出櫘,重宫禁也。
普通宫人亡故后,先送安乐堂,再送至阜成门外静乐堂火化,上述记载中分别提到,宫人亡故,“无位号名秩”或云“非有名称者”,不得赐墓,送出火葬。也就是说,有名称名秩的是有资格赐墓的。女官作为后宫中有品级、官职且身份地位高于普通宫人的女性,应属于“有名称者”,是有资格被赐予墓地的,而不会凄凉地被抬进静乐堂。

明宫廷行乐图中的宫女形象。
从明初女官的事迹看,告老还乡者有内官护送,卒于宫中者,亦有中使护灵归葬,如陈二妹。永乐年间的王司彩亦卒于宫中,虽未记载是否归葬故乡,但其生时为帝后所器重,死后亦当有此哀荣,把几十年的人生甚至生命都奉献给了宫廷,这也算朝廷对她们的礼遇了。沈琼莲亦可能卒于宫中,但是否明中后期依然赐亡故于宫中的女官归葬故里则不甚明了。但即便因路远迢迢而不能魂归故里,在京城附近赐葬亦是有可能的。《宛署杂记》中有如下记载:
宫人孙氏等墓:嘉靖末年,宫内火,孙氏等死之。敕赐墓县南上下庄。
女官孙氏等墓共祠堂。岁春秋二祭,遣内官行礼。祝板云:
皇帝遣□谕祭于女官孙氏等之灵曰:时维某节,特用遣祭,尔等其歆承之。
“宫人孙氏”和“女官孙氏”许是同一人,死后不仅赐葬于宛平县南上下庄,且一年两次遣宦官祭祀。由此可见,女官若亡故于宫中,按制度是要赐墓祭祀的。另外,金山在明代除了作为妃嫔及皇子女墓地外,亦有累朝夫人葬于此地,清明、霜降两节有内官行礼祭祀。《宛署杂记》中记载这些夫人的名封主要有“保圣”“佐圣”“翊圣”“辅圣”“卫圣”“奉圣”以及“勤敬”“恭奉”“崇奉”“敬慎”“忠慎”“勤慎”等。从名封上看,封号中带“圣”者,一般为皇帝的乳母,其他封号或可能属于保育过皇子女的乳母,亦不能排除宫官、宫人因侍奉帝后、太后勤慎有功而特加封号的可能。总之,“矧诸妇有劳于国,生则时赉之,没则厚葬之,荣以殊号,守以坟户,报德报功,极隆且备,不必为堤防之举,而诸妇自兢兢享富贵终其身”。当然,女官亦有品秩地位高下之分,但赐一抔黄土得以入土为安当不是奢侈。
明代亦有放出宫女之令,洪武、正统、成化、正德、嘉靖、隆庆各朝皆有宫女放出之事,人数不等。这些宫女得以出宫回乡,或者嫁人,能够脱离深宫,也是不幸中的幸运了。统治者和文官们将遣放宫人视为无量功德,但随着一批宫女的放出,又会有大量的民间少女被选入宫,继续重复深宫中的悲剧。
那些在深宫中耗尽一生的宫女,晚景更是凄凉。明代有内安乐堂,此处在金鳌玉蝀桥西的羊房夹道。“凡宫人病老或有罪,先发此处,待年久再发外之浣衣局也。”浣衣局不在皇城内,在“德胜门迤西,俗称‘浆家房’者是也。凡宫人年老及有罪退废者,发此局居住,内官监例有供给米盐,待其自毙,以防泄露大内之事”。为了防止泄露宫中的秘密,不知有多少宫女付出了自由与生命的代价,然而统治者却认为“法至善也”。宫女一旦病故,“或以谴责死者”,尸体送至北安门外的安乐堂,再“转致停尸房,易朱棺再送火葬;其有不愿焚者,则痤之地,亦内中贵嫔所舍焚冢也”。“宫制:凡宫人死,殓者必先索其身畔,有长物以闻。”其火葬之地曰“净乐堂”,在西直门外,因其墙阴皆斜,宫人死后又在此火葬,故有“宫人斜”之称堂“有东西二塔,塔有眢井,皆贮骨灰之所。”浓浓的怨怅在熊熊火焰中化作净乐堂下的一捧捧灰烬,这就是宫女一生的终结。
作者/彭勇潘岳
导语/李夏恩
编辑/李永博
校对/张彦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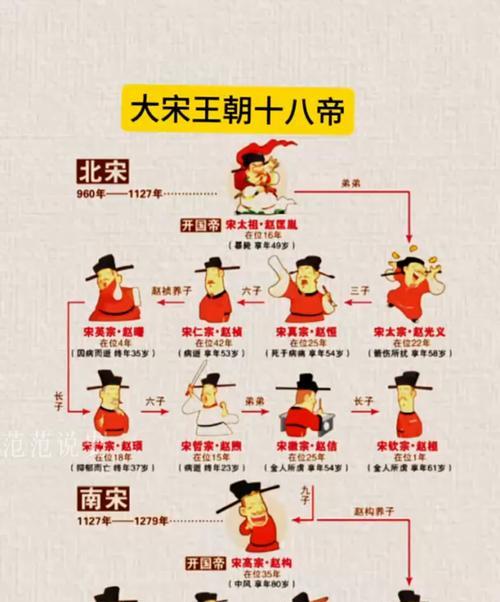


![乾隆可是把雍正的心腹差不多搞了个遍[吃瓜]](http://image.uczzd.cn/52571713781214644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