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举行。近日,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接受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的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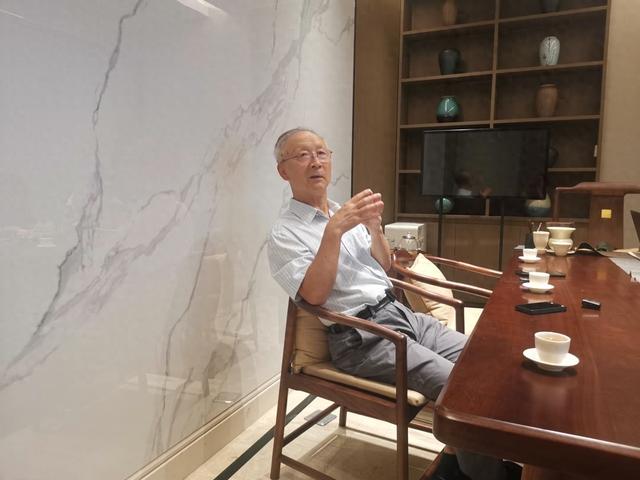
记者:本届世界中国学大会的主题是“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在您看来,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
李伯重:实际上经济史学界回答过这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历史是连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座桥梁”。因为“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是连续的过程,而不是过程的断裂。所以,不能把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割裂开来。现在我们学界越来越多人都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也开始研究历史中国,因为你不了解历史中国,你就无法真正认识当代中国。
到了今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历史和现在是割裂不开的。今天我们都在说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就是我们国家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特点,因为历史给我们奠定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情,因此我们的现代化也必然体现出中国特色。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汉学”“国学”“中国学”有何不同
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的研究被称为“汉学”“国学”,现在提出“中国学”,如何理解这三个概念?
李伯重:因为我在海外工作过,在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伦敦经济学院、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学校都教过书,所以对欧美的中国研究有一些了解。我认为“国学”“汉学”可能都是一些比较陈旧的说法,准确来讲应该是“中国学”。
“Sinology(汉学)”这个名称实际上只是在欧洲比较常见(英国除外),而在美国则很少见到。如果在美国,人家叫你“Sinologist”,就觉得你是一个做先秦文化研究的人。现在在欧美,用得最广泛的是“ChinaStudies(中国学)”。
“汉学”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和制度,集中于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汉学研究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只靠汉学不能全面了解历史中国,特别是难以了解中国重要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
“国学”是一门中国本土的学问,主要是研究中国古典学问。这当然是很必要的,但是要把它视为全面了解历史中国的学问,我觉得不太合适。
“汉学”和“国学”研究难以全面认识历史中国,而要全面和深入研究中国的学问,最恰当的名称应该就是“中国学”。“中国学”这个名称本身已经包含了“汉学”和“国学”的研究。而且历史中国必须是放在世界范围来研究,不然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所以“中国学”到了今天,就已成为“世界中国学”。
为何强调“世界视野下”
记者:近几百年以来,中国研究很多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来定义的。如何把这样的一种视角重新收回来,由中国人自己定义中国学?
李伯重: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因为科学研究没有国界,不管是西方人看中国或者是东方人看中国,中国就是中国。但从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则可以看到中国的不同方面。我的看法是,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方面。把各个视角看到的不同方面融合起来,才是一个全面的中国。
第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中国没有一个从世界的视野出发对自己进行研究的传统。中国古代虽然有长久的治史传统,但基本上是出于中国人自己的视角,不是世界眼光。
在一次会议上,有位学者专门谈“天下”问题。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人没有“世界”观念,而只有“天下”观念。“天下”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如果没有比较,没有和别的对象之间的联系,就看不出自己的特点。
我觉得中国学也是这样,它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全方位来看,每一个视角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如果只是从中国出发去看,那也有缺点,就会变成我们中国是“天下中心”的古代观念,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多视角是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次世界中国学大会的主题强调“世界视野下”,我想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记者:以前一些关于中国学的研究可能会有一些欧洲中心的思想。近年来,像您这样的中国专家加入了之后,这种情况是不是有所改善?
李伯重:每一个时代人类的认识都在进步,不能以某些学者在某个时期的认识为标准来看过去。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世界学术研究,所以今天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可以利用西方200年来发展的社会科学为我们的研究服务。研究中国的时候,不管是用哪一种方法研究中国,只要你是用功的、认真的,做出来的结果对认识中国有帮助,我觉得这就够了。
现在有一些学者谈“中国话语权”,如果是自说自话的话,话语权有用吗?你要让人家听得懂,让人家接受,你必须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这不单是指是否使用英语的问题,而是整个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都得让人听得懂。我研究中国经济史,特别是从明朝到清朝的长三角的经济,西方学者或许不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但能理解我的研究方法。而且我提出的是新观点,他们也觉得观点很重要。我认为这是中国融入且能够得到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方式。
对于学术研究,我们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就像鲁迅先生当年讲的“拿来主义”,是我们自己去拿,不是别人强迫你接受,拿好的东西,不拿坏的东西。
自主知识体系就是我们自己作出的正确结论
记者: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济学界用西方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发现很多问题解答不了。对此,您怎么看?如何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
李伯重:我对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还没有很深的认识。但如果要谈论自主研究的空间,我觉得可以以经济学为例。新剑桥学派的主要创始人琼·罗宾逊夫人说得很清楚,经济学就是一个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拿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换一个工具,如果没有旧的工具,就创造一个新的工具。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创造了世界的经济奇迹,到底为什么会成功?在经济发展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困难?这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尽管西方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真正能够找到符合我们中国国情的答案还得靠我们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主知识体系就是我们自己作出的正确结论。
记者:今天我们遭遇了逆全球化,从过去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可以获得哪些应对现状的智慧呢?
李伯重:我们可以把逆全球化看成一个逆流。历史的进程证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那么,为什么现在会出现“逆流”?因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主要方向是会提高整个世界的经济总量,从而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但是它也会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让原来的优胜者逐渐被拉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得利比较多,有的人得利比较少,就会出现矛盾。怎么解决?历史上没有先例,但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
当然,这股“逆流”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中国必须持续推进产业升级,还有内部消费要提振,对人民的福利更要加强。我们先把自己的内功练好,等到“逆流”逐渐过去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大的爆发力。
为什么要举办世界中国学大会?
记者:对于一般的受众来说,很多人可能对中国学并不了解。为什么要举办世界中国学大会?
李伯重:我觉得世界中国学的核心就是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民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了解。了解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面向大众的媒体,也有学术性的研究。归根结底,这些都需要由学术界提供比较好的知识作为支撑。在我看来,举办世界中国学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提供更好的知识,同时也让中国人民更加了解中国。对于前者,大家比较能理解;对于后者,可能有人会问:中国人还不了解中国吗?
我在国外教书时,部分国外学生对中国的了解比一些中国留学生还要好。我觉得通过世界中国学大会,可以为教育事业提供更好的支持。
记者:现在信息畅通,但是对于中国,外界还是有一些误解和偏见。您认为,他们在理解中国文化的时候到底存在哪些困难?
李伯重:我觉得首先是语言的困难。我最初到海外主要是和汉学家打交道,后来慢慢接触其他西方学者。一个汉学家,要能够阅读中国的古文,需要大量的时间。另外,由于他对中国没有身在其中的直接了解,了解的往往还是书本上的情况。传教士留下的记录关于普通人是极少的,而这个世界主要的生活人群又是普通人,如果你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不了解他们的活动,你怎么研究历史?
现在我接触到英美比较年轻的中国学学者,他们的中文水平基本都不错,特别是口语相当好,阅读现代汉语文献能力也不错,但看古文还是比较费力,当然我们中国自己的大学生现在看古文也费力。有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他到北京来查资料,天天晚上看中国清代的奏折文献,每天晚上看到12点钟,就一直待在宾馆里看,门都不出,兢兢业业,所以他的成就很高。但是现在这样做的年轻学者可能不是很多。
此外,研究中国历史还强调个人的感受。研究唐史,就需要沉浸在唐代的语境中,这样会比较容易理解很多东西。如果找一个做现代史的人来做唐史研究,哪怕文字上都读得出来,可能还是不了解其中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有世界中国学大会这样的机会,让这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到中国来实地体验,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在研究中有很多AI不可取代的地方
记者:本次大会有一个平行分论坛专门讨论“数智时代的世界中国学”。您会用AI工具来做历史研究吗?技术的发展对于史学研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伯重:我在研究中会使用AI作为辅助工具。我使用AI,主要就是帮忙查资料。我的一些学生想要写文章的英文提要,也会叫人工智能帮忙翻译,我觉得翻译得还不错,至少比他们自己翻译的好得多。
我觉得AI技术还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它要能够做到替代一个优秀学者,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在这个过程中,用传统的方法还是有空间的。当然,如果愿意学习AI的技术,再加上用传统的方法,可能会做得更好。在研究中有很多AI不可取代的地方,比方说谈到人的情感、审美,还有一些复杂纠纷,AI想要完全取代还是比较困难的。
还有一点,AI不会发现问题。比如,我现在做16—19世纪中期中国的贸易研究,要同时了解英国、荷兰的外贸以及当时世界的贸易格局。我可以通过AI搜索学界的研究成果,还有重要学者的主要观点,这样可以为我节省大量的时间。但是,选题是我想出来的,研究路径和最终观点也是我想出来的,这个是AI无法取代的。
中国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记者:现在世界中国学研究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李伯重:在过去20年,新的动向已经出现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史在国际史坛上一直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20多年前,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大分流”理论的提出及其引起的世界反响。“大分流”理论由美国加州学派提出,当时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一批在加州各大学任教而且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学者经常会面,探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问题。大家有很多共同的想法,都力图重新看待中国,特别是明清的中国。我们都认为学界流行的“中国停滞论”或者“冲击—回应”模式是有问题的,提出中国有自身发展的动力。后来彭慕兰就写了一本书《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震动了国际学术界。现在“大分流”已变成一个研究的重大课题,也体现出中国在世界史学界的影响。
记者:这次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您会遇见一些老朋友,您最想聊些什么?
李伯重:想多了解他们最近做的工作。因为现在国内看他们的文章,新成果见到的不多。中国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如果只是中国学者关起门来闭门造车的话,那就不可能提出很多对世界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外国学者也一样,如果不到中国来亲自体会,也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所以必须交流。比如说,一个学者如果想研究唐代历史,不去看敦煌,能够真正了解唐代吗?要真正了解唐代中国,就必须到西北去看看。
今天的一些国外青年学者,到中国来的机会比较少,其研究可能也拿不到资金支持,导致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仍然还是主要来自书本。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也不像他们的老师那辈人那样,对中国抱有深厚感情。西方有个传统,就是每一代学者总是要挑战上一代学者。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和上一代学者之间的代沟越来越深,他们和中国学者之间的国际界沟也会加深。这些都是大问题。如果世界中国学将来发展得好,能够逐渐消除这些隔阂,能够让学者之间更加密切合作,这肯定是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