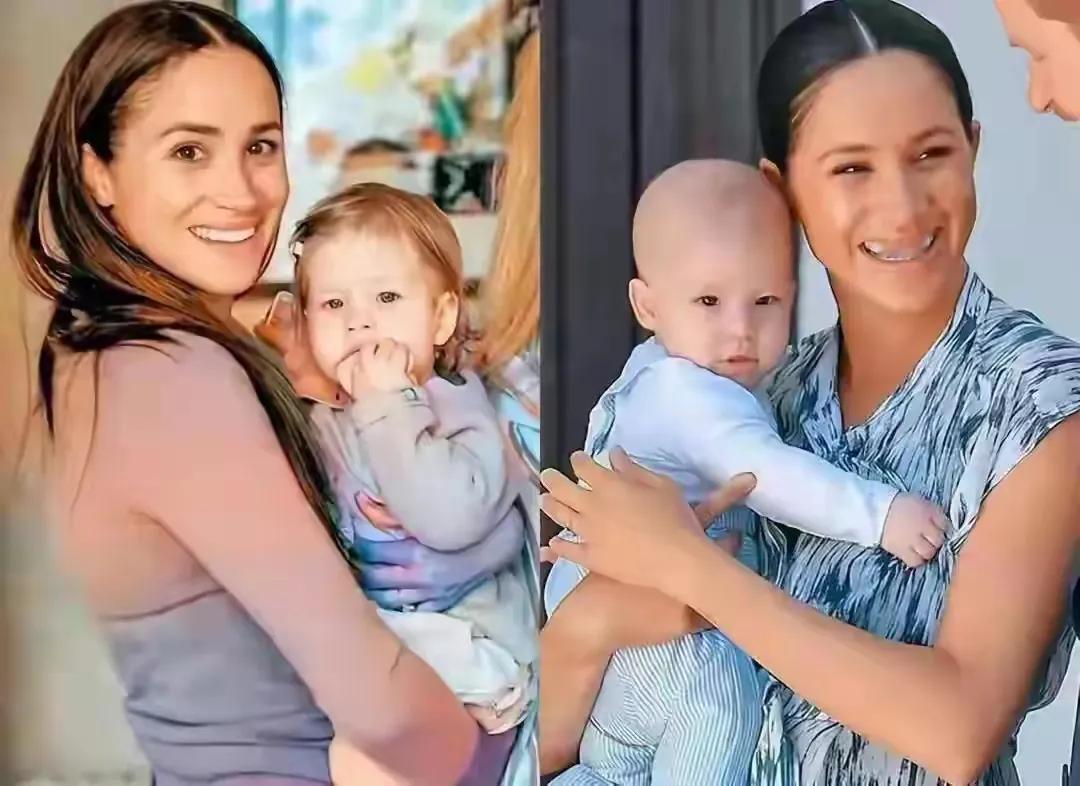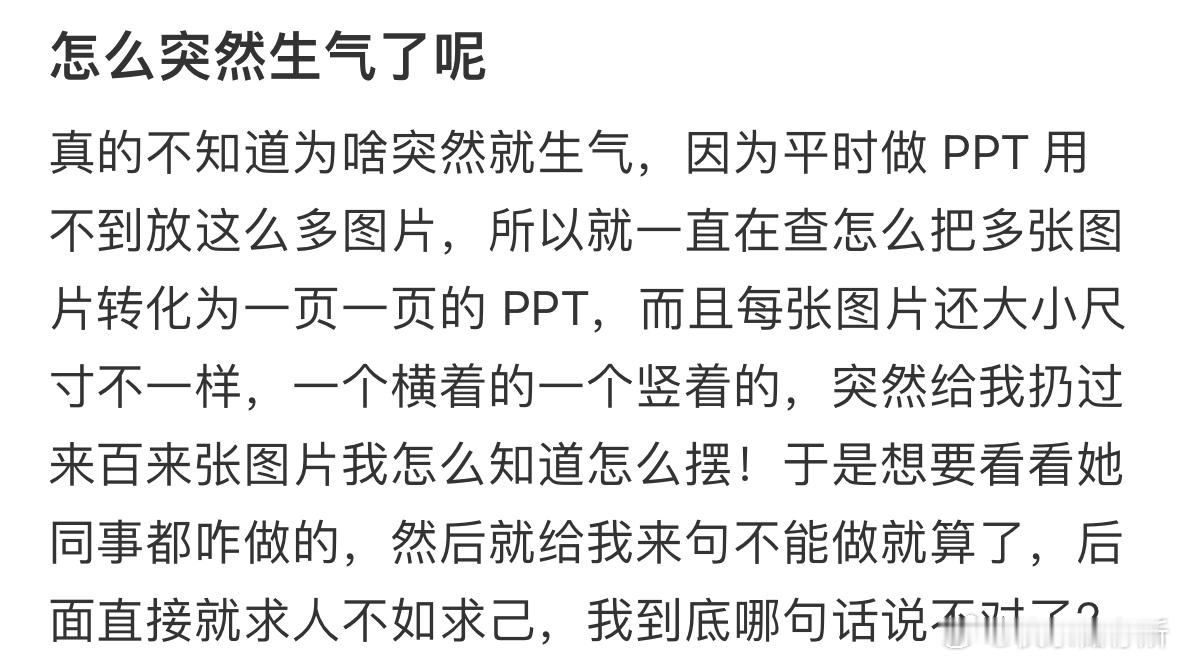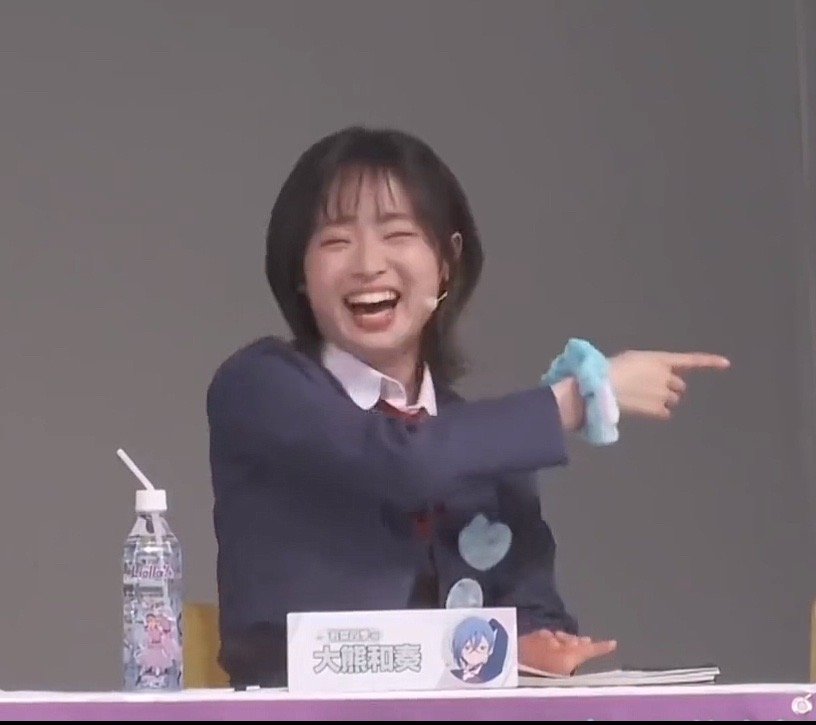古时,有一妇人怀了双胞胎,到了生产这日,老大一下就生出来了,老二却是生了一天一夜。等老二出来,男子还来不及欣喜,产婆却一脸惊恐从房内冲出来,断断续续说了一句话,男子惊骇下扬言赶紧把那孩子扔了。 光绪三年,在胶东某村,农民王老实蹲在自家小院门槛上,抽着旱烟。 屋内,妻子月娥正在生产。 产婆和邻妇进进出出,木盆里的血水换了一茬又一茬。 老大落地时还算顺当,是个虎头虎脑的男婴。 结果,王老实心头刚松口气,屋内月娥的力气马上快用干了,老二却迟迟不见踪影。 突然,一声尖叫传出! 产婆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门:“胎胎、神发怒,是个、是个肉疙瘩!” 邻妇们挤在门口,探头探脑。 很快,“六指娃克死爹娘”的陈年旧事被重新提及,钻进王老实的耳朵。 他猛地起身冲进产房。 在炕角,一个沾满污血和粘液的布包微微颤动。 借着油灯光,王老实看清了,那并非寻常婴孩,而是一个肉团。 他害怕的转身,抄起柴刀:“把那东西给我扔后山喂狼!” 柴刀在他手中不住颤抖,就在这时,炕上的月娥用尽最后力气:“别伤我娃,那也是我的肉啊!” 王老实僵在原地,柴刀高举,却迟迟未能落下。 产婆壮着胆子劝道,“月娥刚生产,经不起刺激,不如先看看清楚?“ 王老实咬着牙,将那怪异的布包揭开。 里面,竟真是一个活生生的婴儿! 只是这婴儿的模样,半边脸颊覆盖着巴掌大的深红胎记,触目惊心。 另半边脸却是青中透蓝,透着不祥。 更诡异的是,那双眼睛一黑一灰蓝。 这哪是孩子?分明是妖孽!是家门不幸的征兆! 然而,月娥挣扎着:“我自己养!他再怪,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你敢扔了他,我就抱着老大跳井!” 两人僵持到后半夜,王老实才默许了孩子留下。 随后,他在院子角落搭了个简陋的柴棚,铺上些干草破絮,将这个取名“来寿”的孩子安置。 不许他踏入正屋半步,更严禁村里的孩子靠近。 从此,“鬼娃”成了来寿的代名词。 老大“来福”被捧在手心,吃细粮,穿绸衣。 王老实赶集时,连碰见带疤的果子都要一脚踢开。 月娥夜夜搂着来福入睡,却总在五更天惊醒,摸着右乳怔忡出神。 一次,来福淘气打碎了碗,月娥竟狠狠抽打他屁股:“糟践东西!你弟弟连碗边都摸不着啊!” 王老实摔了烟杆,从此,“老二”成了这个家的禁忌。 “鬼娃”的传闻,终于传到了三十里外白云观玉清真人的耳中。 真人下山,寻至王家。 见到面覆红蓝胎记、眼神却异常清亮的来寿时,真人非但不惊,反而长笑。 “阴阳脸通天地,此子不凡!随我上山吧,赐名‘长生’。” 王老实夫妇如蒙大赦,很快长生被带上白云观。 在清幽的道观里,他喝着米汤长大。 玉清真人发现他天赋异禀,六岁便能辨识百草。 一次小道士烫伤,长生随手揪了把紫花地丁嚼烂敷上,水泡竟迅速消退。 真人抚掌而笑:“此乃天赐印记,非妖非怪,是济世救人的徽章!” 然而,血缘的羁绊并未断绝。 光绪某年寒冬,来福突染恶疾,高烧不退。 王家倾尽家财,遍请名医神汉,皆束手无策。 王老实最终奔向那白云观,药庐竹帘掀开,一个身着道袍的少年侧身而立。 当他转脸,月娥和王老实才认出这是自己的孩子! 玉清真人将煎好的药递来:“此乃长生。” 长生以奇方救活了来福,却拒收谢礼。 月娥日日往观中送饭,蒸糕总捏成并蒂莲花。 一次下山,月娥崴脚跌入山沟,长生毫不犹豫背起她回村。 村人见状,指指点点“鬼娃背人”。 王老实闻讯,抄起扁担拼命,却被长生拦住。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翌年开春。 胶东遭遇蝗灾,县太爷率众设坛求雨,法事连做七日,烈日依旧炙烤大地。 第七日,几名衙役突染怪疾。 混乱中,长生一眼辨出是热毒攻心。 他抄起香炉灰混入唾沫,涂抹衙役患处暂缓毒性,又急令煮绿豆汤解毒。 县太爷怒斥“妖言惑众,扬言拿办。” 玉清真人挺身而出:“未时三刻无雨,贫道自焚谢罪!” 长生在万众瞩目下,一步步登上祭坛。 他取出三根银针,毫不犹豫刺入自己虎口穴位。 人群屏息,死寂中,东南天际骤然翻涌起墨黑云团! 未时三刻,豆大的雨点精准砸落。 这一刻,胎记不再是诅咒的象征,而是天地感应的印记! 雨幕滂沱,浇熄了旱魃,也浇透了围观村民的心。 当晚,王老实蹲在灶房,打磨一柄小刀。 月娥心惊胆战,王老实却摊开掌心,露出三根精心镶嵌了桃木柄的银针。 他闷声道:“防滑。” 光绪三十六年,胶东爆发大疫。 长生携带药方,奔走于疫病肆虐的村落。 他右脸那鲜明的红蓝印记,不再令人恐惧躲避,反而成了活生生的“济世招牌”。 村民远远望见那抹独特的色彩,便知救星已至,绝望中升起希望。 当年柴棚里的“鬼娃”,已成百姓口中的“活神仙”。 主要信源:(《太平广记·异疾篇》《民俗奇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