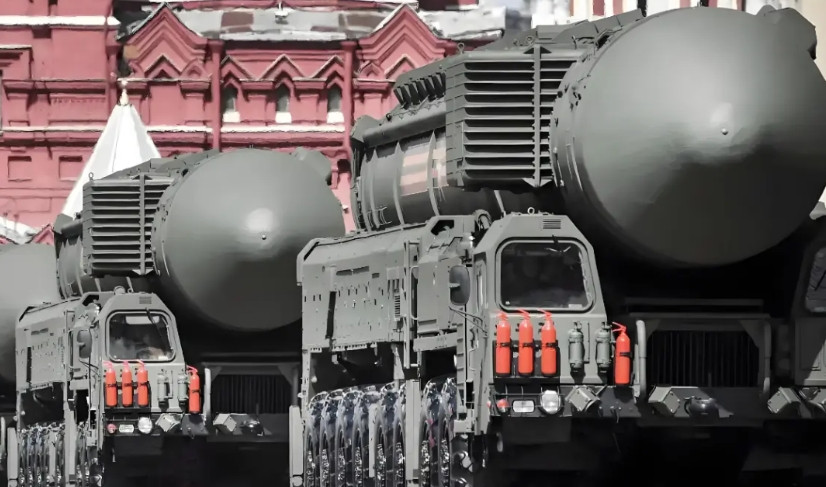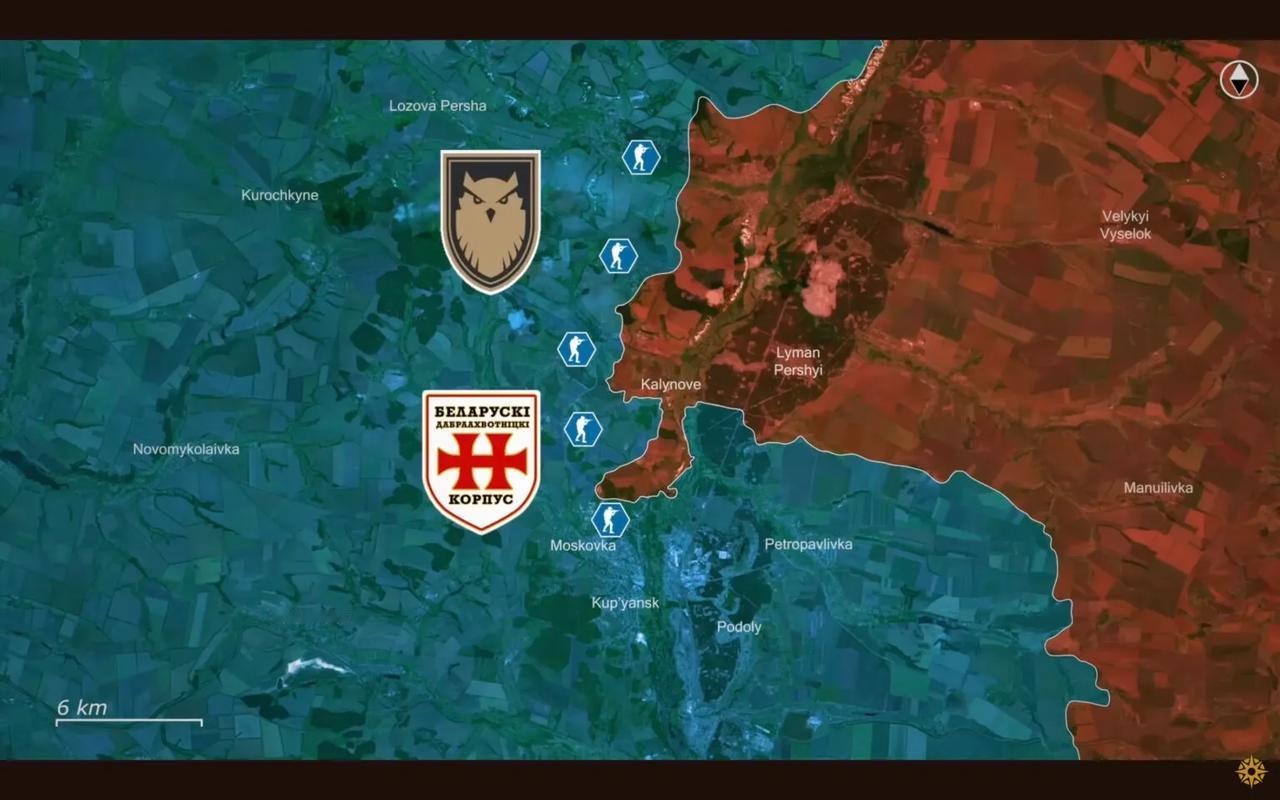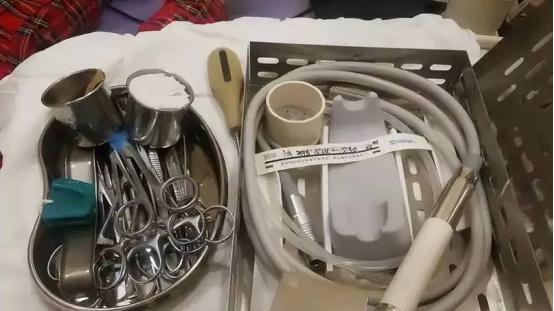1982年8月,第六机床厂供销科职员陈掖贤几天没来上班,也没有请假。同事担心他,去到他家里看望,闻到一股浓重的臭味。打开房门一看,只见“陈掖贤已经上吊多日”,家里一贫如洗。 陈掖贤这人,出生在1929年1月底的湖北宜昌,那时候家里条件一般,他妈赵一曼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宁儿,因为那天正好是列宁逝世纪念日。他爸陈达邦和妈赵一曼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早年去苏联留学,在那儿认识结婚。赵一曼怀孕后回国,生下他就把他交给伯父陈岳云抚养,自己继续干抗日的事。陈掖贤从小跟着伯父长大,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伯父家在四川宜宾乡下,靠种地维生,他小时候帮着干农活,挑水砍柴啥的都干过。1941年,伯父跟他说了实话,他不是亲生的,他爸其实是八叔陈达邦。他起初不信,以为伯父逗他玩。六年后,姐姐告诉他真相,他妈是抗日英雄,早牺牲了。他这才知道自己爸妈的来历,两人都在苏联相识,结婚后妈回国生他,取名纪念革命。爸妈那时忙着革命,没时间带他,他就这么在伯父家待着,长到十几岁。 长大后,陈掖贤通过组织介绍,1950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他学习挺用功,读了四年书,1954年毕业,本来有机会去外交口工作,但分配去了北京工业学校,当政治课老师,教马克思主义原理啥的。工资不高,但起码稳定。他1957年跟爸陈达邦去黑龙江祭拜妈赵一曼,那是他第一次知道妈的具体事迹,赵一曼是东北抗联的女英雄,1936年被日军抓捕杀害,留下一封遗书给他,里面写着希望他代替妈继续奋斗,好好学习啥的。他抄了遗书,回家后用钢针在手臂上刺了“赵一曼”三个字,当作纪念。爸陈达邦也一直在找赵一曼的下落,好不容易确认了身份,两人总算团圆了点,但妈已经没了,爸后来也遭了不少罪。 工作上,陈掖贤一开始干得还行,1958年他和同事去房山县河北乡下放劳动,修水电站引水渠,干农活,挺苦的。1960年又去朝阳区楼梓庄公社锻炼。那时候全国日子都不好过,他看到乡下人饿肚子,家里也穷,就写信给上级反映情况,说些尖锐意见。上级看了信,没追究,说他是个可怜孩子,就这么过去了。但后来信被别人看到,借题发挥,他日子难过了,被调岗。1969年,学校解散,他跟精密机械研究所合并成第六机床厂,去了供销科,当职员。天天处理采购单据,骑自行车上下班,手上老沾墨迹。工资还是那点,够勉强过日子。 到了1982年夏天,北京热得像蒸笼,第六机床厂供销科的同事们发现陈掖贤几天没来上班,也没请假。大家合计着去他家看看。他住的旧平房在胡同里,院门没锁。进去一股臭味直冲鼻子,推开房门,只见他从梁上吊着,身体僵硬了好几天。脸肿了,衣服皱巴巴的,地上几张旧报纸和空碗。屋里家具没几件,墙角堆破布,穷得一清二楚。老婆张友莲前不久病逝了,留下一堆债,他一个人扛着,估计压力太大,走投无路了。同事们赶紧报案,民警来确认是上吊自杀,已多日。厂领导来了,查看现场,摇头。陈掖贤就这样走了,年仅53岁。 事后,民警调查了现场,确认是自杀。厂里开了会,讨论怎么处理后事。邻居说陈掖贤平时不出门,脚步慢,自行车停院里生锈了。他的闺女陈红后来来了,捡起地上的东西。遗体运走,家属收拾残局。陈掖贤一生坎坷,从小没妈,爸也晚年才相认,工作调来调去,家庭负担重,经济一直拮据。他妈赵一曼是英雄,留遗书让他继续奋斗,但他拒绝特权,过普通人日子,结果穷苦到头。爸陈达邦也早逝,1979年才平反。他没辜负妈的期望,努力工作,但命运不济,情绪低落,病痛缠身,最终选择这条路。两个闺女,大女儿陈红在成都工厂上班,二女儿去了国外。陈掖贤死时,身上还刺着妈的名字,家里就剩泛黄笔记本记妈的事迹和破日历停在8月初。 话说回来,陈掖贤这辈子其实挺典型的英雄后代故事。妈赵一曼抗日牺牲,留遗书教育他要自强,他也真这么做了,上大学,当老师,后来干供销,啥苦都吃。爸陈达邦是革命干部,早年忙着工作,没带他,但他长大后父子相认,一起找妈的下落。1957年去东北祭拜,那一刻估计他最有感触,抄遗书时手都在抖吧。但生活不是电影,英雄后代也得面对柴米油盐。老婆病了,孩子要养,工资就那么点,他饿肚子是常事。1974年那次饿晕,同事救他,说明他平时人缘还行,但穷苦是真穷苦。拒绝抚恤金这事,说好听是骨气,说难听是轴劲儿上头,结果苦了自己和家人。1982年老婆走了,他一个人扛不住了,就这么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