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八年,科举考试结束,赵构发现探花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便问道,您多大,有孩子吗?谁料,对方直言,草民73岁,并未娶妻生子。结果,赵构笑道,30岁的宫女,赏给你了!
这白发苍苍的探花老人名叫陈修,说起他的科举路走得那要比比南宋的驿道还坎坷。
他在二十三岁初入考场时,那时候汴梁城的虹桥尚未染血。
直到金兵铁蹄踏碎半壁江山,他背着一布袋发霉的窝头逃到江南,布袋里还塞着抄满批注的《禹贡》残页。
那些个同窗笑他是棺材里伸手要功名,就连客栈小二嘀咕“老童生占着茅坑”。
但是对于这些个流言蜚语他都充耳不闻,只把冻裂的手伸进怀里焐暖半块砚台。
绍兴八年的殿试题“四海想中兴之美”点燃了他枯槁的双眼。
于是提笔写下“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时,墨迹在纸上洇开的裂痕,像极了黄河故道的沟壑。
当赵构见到此句,亲手抄录贴于宫墙,朱笔一圈将他定为探花,直到唱名时才发现,这力透纸背的文辞竟出自颤巍巍的老者之手。
曾有大臣劝他以年纪太高为由想要降一位,只见赵构摆手,说,论才不论龄。
之后就又问他多大,娶媳妇没,有几个孩子,直到对方说草民73岁,并未娶妻生子。
没想到之后赐婚旨意砸懵了整个朝堂。
此时宰相秦桧党羽趁机发难,暗讽礼部舞弊,赵构却将弹劾奏章摔在地上,陈卿策论字字剜心,岂是尔等谄媚文章可比?
之后转头对陈修补了句,朕宫中有施姓女官,三十未嫁,许你为妻,再赐良田百亩安家。
太监憋着笑宣旨,老探花接旨时袖口墨汁未干,那是殿试激动时甩上的。
大爷连忙谢恩,这大年纪不仅考取了功名,就连终身大事也解决了。
新婚夜的龙凤烛爆了三次灯花。
新娘施翠娥攥着鸳鸯被面发抖,盖头下泪水冲花了宫妆。
陈修颤手递过放妻书,老朽七十三,恐误姑娘芳华。
施氏却盯着“恐误芳华”四字怔住,这字迹与宫中珍藏的状元策一模一样。
她忽然撕碎放妻书,大人教我写字,我便留下。
案头《水经注》被风吹开,露出“束水攻沙”的朱批,那是她三年前亲手装订的治水方略。
而六品编修的俸禄养家捉襟见肘。
之后陈修每日从衙门省下半块糕饼揣回家,施氏当了陪嫁银镯换宣纸,在漏雨的屋里支起织机。
暴雨夜屋顶哗哗漏水,陈修举着《策论集注》盖住织机,后背湿透还嘟囔,书皮是牛皮纸的,防水!
然而转机发生在某个雪夜。
陈修因治水策被赵构斥为“书生空谈”,枯坐书房长叹。
此时施氏铺开河防图,簪花小楷点向汴梁故道,此处该筑双闸分洪?
老探花愕然得知,妻子竟是尚功局掌典籍的女官,昔日御览的《治水十策》便经她手装帧。
五更天时,更夫瞧见陈府西窗映出双人影,老头子执笔勾画黄河九曲,少妇挽袖研磨松烟,织机声混着论水声惊飞了梁上雀。
直到七十八岁的陈修挂工部侍郎衔冲上黄河堤坝时,满朝文武还在扯皮治水方案。
之见他抖开珍藏的《禹贡地域图》,带着小伙计连熬七夜核账,骂声震得值房梁灰簌簌掉,这段堤去年就该加固!谁吞了银子?
暴雨突至,施氏策马送来新誊的河防图,牛皮纸袋墨迹未晕。
陈修笑着递给河工,袖口露出她绣的松鹤纹护腕。
堤坝合龙那日,赵构亲题“国之梁栋”匾额。
陈修却盯着落款嘀咕,印泥不如家里那方朱砂。
巡抚送来“老骥伏枥”贺匾,他咂嘴摇头,这字比我媳妇差远了。
之后三个从育婴堂抱来的孤儿趴在膝头习字,施氏在窗下绣“状元及第”锦囊。
老探花逢人便显摆,殿试文章里‘束水攻沙’的批注,是我家老婆子添的!
待到九十三岁的陈修弥留之际,孩童诵读《河防要略》的声音飘进卧房。
他攥住施氏的手,气若游丝地念叨,下辈子我早点考功名让你当状元娘子。
此刻窗外桃花扑簌簌落进屋里,盖住当年那身旧官袍。
后来施氏遣散仆从,只带一箱书稿回到福建,开绣坊授女红,门前木牌只写“陈家未亡人”。
七年后金兵破临安,南宋宫阙燃起大火。
有人看见白发老妪在火光中焚烧一卷河图,灰烬里依稀可辨“葱岭金堤”字样,那是陈修殿试策论的残稿。
五十载寒窗换一夕探花,七十三岁遇三十知音,他们用墨迹与针线,在飘摇乱世绣出了最暖的归途。
陈修用实际经历告诉我们73岁正是闯的年纪,而我们年纪轻轻的却每天都在抱怨生活。
人一定要有梦想,并且朝着梦想奋力向前,即使没有实现,但我们曾经努力过,不留遗憾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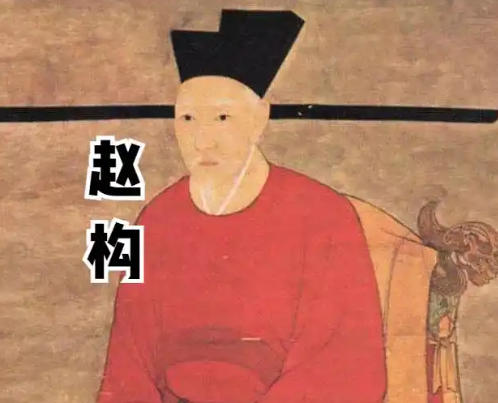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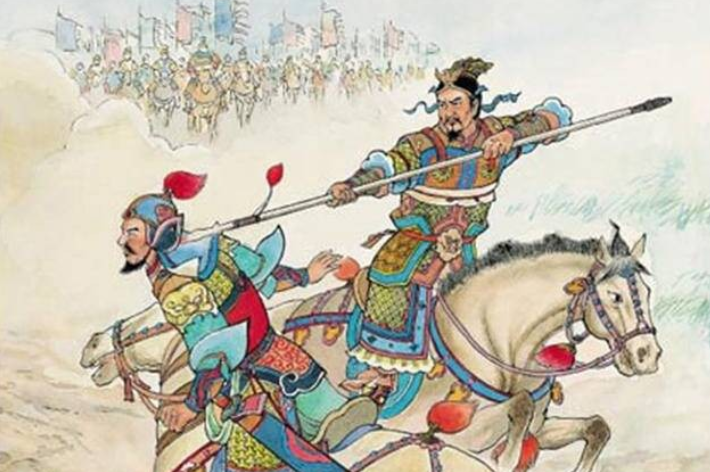

雾海云山
赵氏江山不灭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