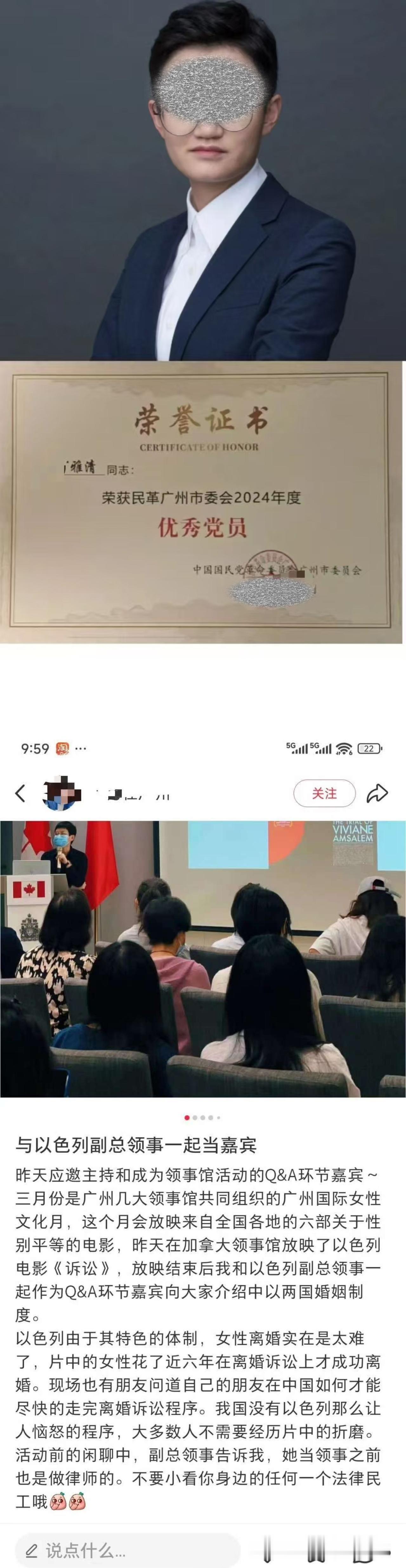1948年,狱医刘石人到女牢诊病,刚到门口,一女犯突然趔趄摔倒在他身上,并迅速塞给他一个纸团,刘石人正要扶她时,狱警走过来了,刘石人只能假装怒骂女犯。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8年的重庆渣滓洞,狱医刘石人照例去女牢巡诊,谁知一个女犯突然踉跄着向他扑来,他本能地伸手想扶,可看守的脚步声就在耳边,吓得刘石人收回了手,换上一副嫌恶的表情,厉声喝道:“找死啊,差点撞到老子!” 这一声怒骂,像一道幕布,利落地遮住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接触,女犯倒地的瞬间,手精准地顶在他右胸的口袋上,一张小纸条滑了进去。 这看上去是监狱里再寻常不过的一场冲突,可骂声背后,却是另一个世界的暗号,这位身穿国民党中校医官制服的医生,究竟是谁。 在这堵高墙内,有两条泾渭分明的战线,一条是国民党特务建立的“明线”,用暴力和铁律维持着统治。 而特务头子徐远举拍着刘石人肩膀时的话,就是这条线的纲领:“这里关的都是共党死硬分子,治死了算他们命短,治好了算你功劳。” 在这套逻辑里,生命本身没有价值,囚犯不过是一串等待处理的编号,看守长李磊是这套规则最忠实的执行者,他把刘石人的行动限制到极致,看病只能隔着牢门的小窗问话发药。 并且医疗资源更是被压缩到可怜的地步:二十来种常用药,两支体温计,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所有人,这里是剥夺生命的地方,不是拯救。 而且刘石人亲眼见过这条“明线”的成果:江竹筠的手指被竹签钉得血肉模糊,而怀有七个月身孕的周泉香因严重营养不良,蜷在草席上,瘦得能看清一根根肋骨。 然而,在高压统治之下,还潜藏着另一条坚韧不拔的“暗线”,这条线由一群被剥夺了自由,却从未放弃信仰的人们维系,他们不是特务口中的“死硬分子”,而是教授、记者、银行经理,是一群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 即使身陷囹圄,他们也依然关注着墙外的战局,用智慧和勇气编织着秘密的抵抗网络,他们的任务清晰而危险:传递情报,保护同志,策划越狱,并向外界揭露此地的暴行。 并且每一次计划好的晕倒或装病,都经过了反复的观察和预演,只为创造一个与外界联络的瞬间,胡其芬,正是这个网络里负责下达指令的关键节点,而那位开篇撞向刘石人的女犯,咳得撕心裂肺的李玉钿,既是需要被拯救的病人,也是承载着秘密的希望载体。 刘石人,这个最初的“局外人”,正是在这两条线的交汇点上,被意外激活了,他初到监狱时,眼前的惨状与徐远举的冷血训示形成了剧烈冲突,在他心里搅起了巨浪,他的第一次“越界”,无关什么宏大理想,仅仅出自一名医生的基本良知。 在那天晚上,刘石人把配给自己的牛肉罐头悄悄塞进药箱底层,送给了极度虚弱的孕妇周泉香,这个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举动,是他内心天平第一次偏离“明线”的规则,为人性投下的砝码。 但也正是这次小小的越界,让他进入了“暗线”的视野,不久,为给一位疑似阑尾炎的病人检查,刘石人不惜与看守长李磊当面撕破脸,甚至以“调职回城”相要挟,最终吵赢了“必要时可进牢房看病”的特权。 但让他自己都没想到,这次为救人命发起的抗争,不仅是突破了监狱的死规定,更是为自己日后成为那条“暗线”的关键通道,凿开了一道至关重要的裂口。 从此,刘石人便开始在明暗两条线上惊险地行走,胡其芬塞来的第一张纸条,指令明确:“三号牢房急需磺胺”。 这对于“明线”来说,根本不可能——磺胺是严控药品,钥匙在看守长手里,可刘石人却想出了办法:他先在医务室“不小心”摔碎三支宝贵的体温计,趁着一片混乱,迅速偷走半瓶磺胺粉。 到了牢房,刘石人借着给李玉钿检查疥疮作掩护,指尖一弹,就将药粉精准地撒进了她的漱口杯,紧接着,他立刻切换角色,对着看守大声嚷嚷:“这病得隔离,再拖下去整个牢房都要传染!” 而他的表演天衣无缝,不仅成功送达了救命药,还为三天后李玉钿被抬出监狱就医创造了合乎逻辑的理由。 并且藏在李玉钿棉袄夹层里的,正是写给党组织的密信,任务的难度不断升级,当胡其芬将一份三百人的名单交给他时,刘石人已然像个经验老到的情报员。 时间来到1949年11月26日,渣滓洞的空气紧张到凝固,看守们口中“要转移犯人”的风声,预示着一场屠杀即将到来,刘石人溜进女牢,接过了胡其芬递来的最后一张纸条,上面没有指令,只有一句诀别般的嘱托:“如果明天有枪声,请记住我们曾活过。” 这句话,是“暗线”的同志们对他这位战友最后的信任,在那样一个非黑即白、生死一线的环境里,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一个普通人做出如此不凡的选择,是最初那点不忍心,还是对另一种信念的向往? 【信源】重庆日报——渣滓洞狱医刘石人多次为狱友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