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 年,皇后阿鲁特氏被慈禧软禁,四天内没有吃水米,快要死的时候,她收到了父亲崇琦偷偷送来的一个食盒,结果食盒里竟然一点东西都没有。阿鲁特氏苦笑着,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食盒的木纹里还沾着宫外的尘土,她用指甲抠了抠,土粒簌簌落在掌心,像极了当年父亲送她入宫时,跪在承乾门外沾的灰。 那天崇琦的朝珠晃得厉害,他说 “皇家规矩大,女儿要忍”,可他没说,忍到最后,连口饱饭都成了奢望。 她摩挲着盒盖,上面的铜锁早就生了锈,想来是父亲从库房里翻出的旧物,怕新物件太扎眼,惹来祸端。 储秀宫的窗纸被风捅出个洞,寒风卷着雪籽灌进来,落在她手背上,冰得像慈禧的眼神。三天前被关进来时,地上还留着前殿的炭火味,现在只剩墙角的霉气。 她想起同治帝在时,他总爱往钟粹宫跑,带些御膳房的杏仁酥,说 “皇后的字比御笔还俊”。 那时她坐在他对面研墨,看他把 “福” 字写得歪歪扭扭,笑得前仰后合,根本没察觉窗外慈禧的眼线,正把这一幕记在小本子上。 食盒是空的,可她摸出了盒底的凹凸。指尖划过那两个字时,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女儿”。崇琦的笔锋她认得,当年教她写 “阿鲁特” 三个字,也是这样,横平竖直里藏着不舍。 他是翰林出身,一生信奉 “君君臣臣”,可女儿成了皇后,反倒成了他的软肋。 她仿佛看见父亲在书房里踱步,手里攥着这只食盒,想放块糕点,又怕被搜出是 “私相授受”;想写张字条,又怕字迹连累全族,最后只能空着送来,让她自己悟这无声的告别。 墙皮上的字被风吹得发淡,是她前两天用发簪刻的 “天可怜我”。刻到 “怜” 字时,簪子断了,半截尖儿扎进掌心,血珠滴在砖上,像朵没开的花。 那时她还抱着点盼头,想着慈安太后或许会来救她 —— 毕竟是慈安点头选的皇后,可宫人才传话,说慈安近来 “偶感风寒”,连朝会都免了。 她就懂了,这深宫里,没人能拗过慈禧的铁腕,连先帝的遗孀都不行。 胃里的绞痛让她蜷起身子,四天没进水米,视线已经发花。恍惚间看见同治帝的脸,他弥留时拉着她的手,说 “等我好了,带你去圆明园看荷花”。 可他没好起来,而她连他的葬礼都没能好好守着。慈禧说 “皇后年轻,恐伤风化”,就把她打发回了钟粹宫,转头就立了光绪帝,把 “太后” 的尊号牢牢攥在手里。她这个皇后,成了多余的影子。 食盒被她抱在怀里,像抱着唯一的念想。她想起刚嫁入皇家时,父亲给她讲 “妇德”,说 “忍一时风平浪静”。 她忍了慈禧的冷言冷语,忍了宫人的阳奉阴违,忍了同治帝病重时不能近身的规矩,可到头来,连忍的资格都被剥夺了。空食盒像是父亲给她的最后答案:忍不下去了,也不必忍了。 她起身时,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扶着墙走到妆台前。铜镜里的人颧骨高耸,嘴唇干裂,哪还有半分 “皇后” 的样子。 她摘下头上的凤钗,那是同治帝送的,钗头的珍珠早就失了光泽。放在食盒里时,珍珠磕到盒底,发出细碎的响,像在跟过去告别。 内室的小炉还有点火星,她慢慢添了些炭,架起小锅烧水。药包里的鹤顶红是早就备下的,不是为了寻死,是怕有朝一日被人暗害,至少能死得有尊严。 水开时冒出的白汽模糊了她的眼,她想起小时候在父亲书房,看他写 “清白” 二字,墨汁浓得化不开。 服下药时,她靠在墙角,手里还攥着那只空食盒。疼痛袭来时,她反而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原来父亲早就懂了,这宫里,清白比活着金贵,体面比苟活重要。盒底的 “女儿” 二字,是他给她最后的体面。 宫女发现她时,雪已经停了。食盒掉在地上,凤钗滚了出来,钗头的珍珠沾了点血。 有人拾起食盒,才发现盒底的刻字,吓得赶紧捂住嘴 —— 谁都知道崇琦是个硬骨头,竟也会在暗处,对女儿说这两个字。 慈禧听了奏报,正用银簪挑着燕窝,只淡淡说了句 “她聪明”。聪明就该知道,新帝登基,旧人留不得;聪明就该知道,反抗的下场比死更难堪。 可没人知道,阿鲁特氏吞下毒药时,想的不是谁的聪明,是父亲刻字时,该有多疼。 三天后,讣告贴在午门外,“嘉顺皇后薨” 五个字写得干巴巴的。送葬的队伍连白幡都没挂满,崇琦远远站在街角,朝灵柩的方向拱了拱手,袖口遮住了发红的眼。 后来有人说,他那晚回府就烧了所有女儿的字稿,火光里,仿佛能看见当年那个在书房练字的小姑娘,说 “爹爹,我要写遍天下的好字”。 储秀宫翻修时,那只空食盒被扔在柴房,被个老太监捡了去。他擦干净木盒,总在夜里摩挲盒底的 “女儿”,想起那个总爱站在廊下看雪的皇后,说 “雪化了,就该暖了”。可那年的雪,直到她死,都没化。 多年后,惠陵的荒草长到了墓碑那么高,碑上连她的名字都模糊了。 只有那只食盒,被老太监的后人收着,木纹里的尘土早已干透,可轻轻一敲,仿佛还能听见当年那个年轻皇后的苦笑,在空旷的宫里,一声一声,撞得人心头发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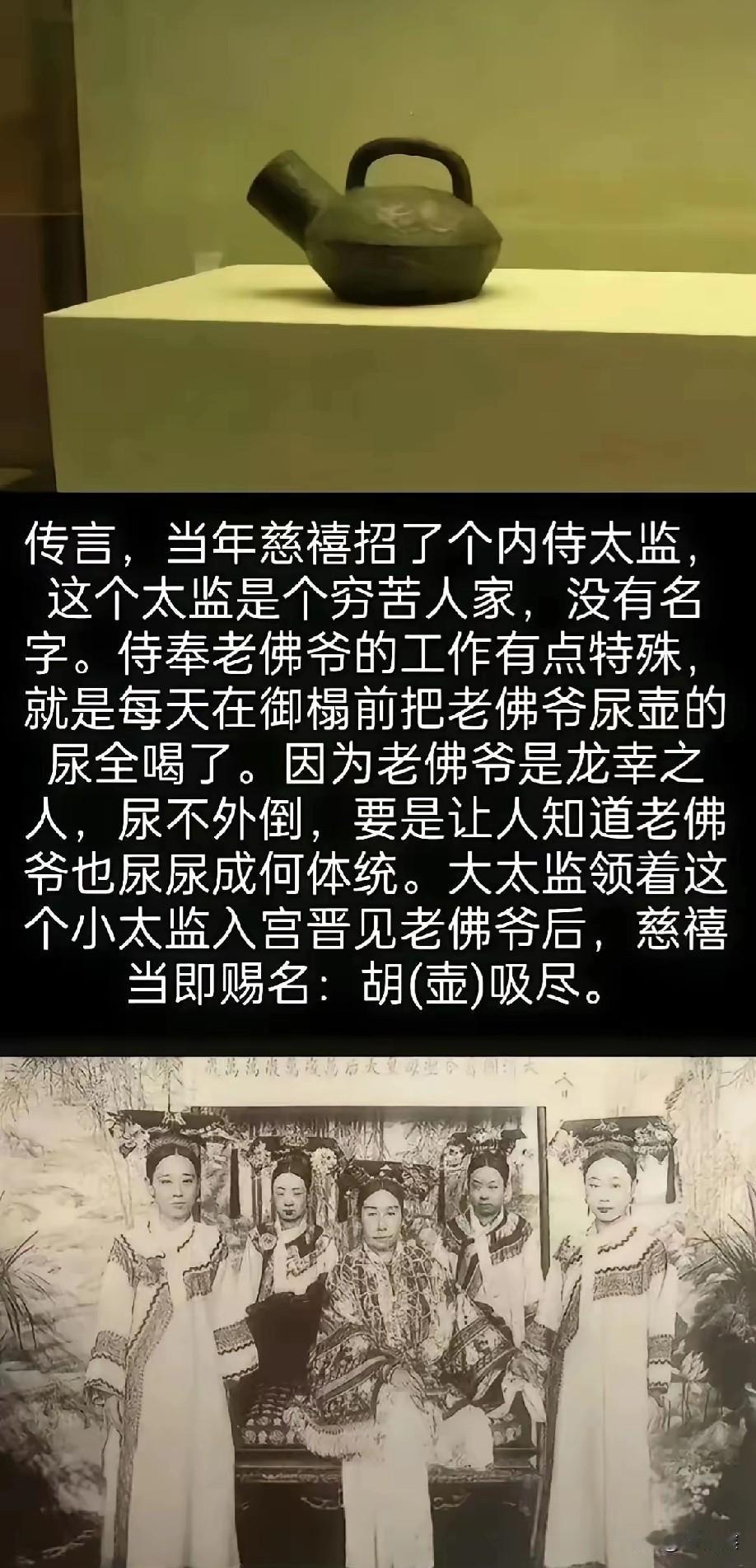


DEATHMASK
“放肆,我是从大清门抬进的中宫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