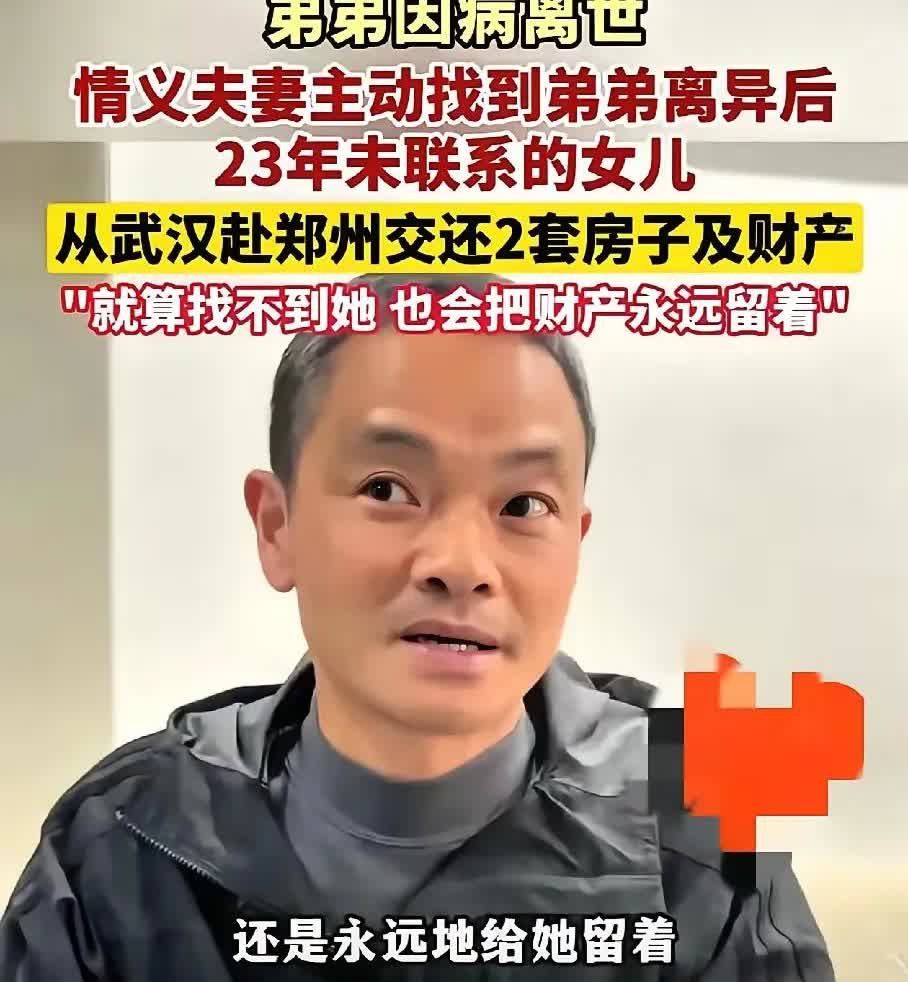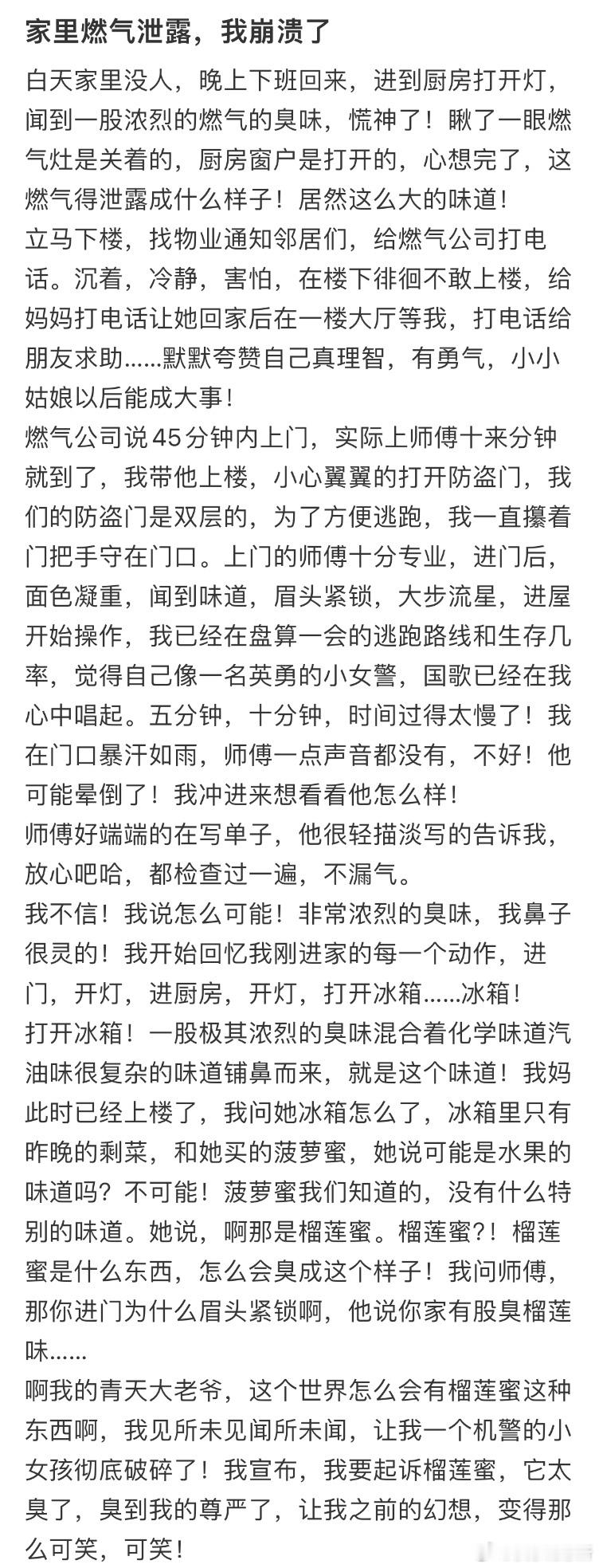1888年,山东一乞丐(武七)讨饭28年,攒下230亩良田、3800吊钱,盖了一豪华宅子。 那宅子盖在堂邑县的土坡上,青砖黛瓦在一片土坯房里扎眼得很。当地乡绅来看热闹,摸着雕花的门廊啧啧称奇,说这叫花子怕不是中了邪,讨饭攒下的钱不买地娶媳妇,倒盖这么气派的房子。武七穿着打满补丁的破棉袄,蹲在门槛上啃窝头,听着这些话只是嘿嘿笑,露出两排黄牙,眼里的光却亮得很——他们哪知道,这宅子根本不是给他自己盖的。 武七小时候叫武训,爹娘死得早,他跟着叔伯过活。十二岁那年,叔伯让他去地主家当长工,说好年底给两石粮食,到了年关却被地主指着鼻子骂:“你个睁眼瞎,账本上早记着给过了,还敢来要?”他攥着拳头想争辩,可那些弯弯曲曲的字像天书,怎么也说不过人家。最后被地主家的狗追着跑出二里地,冻得缩在草垛里,眼泪冻成了冰碴子,那时他就发誓:“将来我要盖个学堂,让穷人家的孩子都能认字,再也不受这欺负!” 讨饭的日子苦得像黄连。他背着个破麻袋,白天在集市上捡别人扔的烂菜叶子,晚上就睡在城隍庙的供桌底下。有回遇上大雪,他冻得浑身发紫,路过的货郎扔给他半个窝头,他揣在怀里没舍得吃,跑了三里地送给更饿的小乞丐。有人笑他傻,说乞丐还学菩萨行善,他只是咧着嘴笑:“我一个人吃饱没用,得让更多人能吃饱饭、认得数。” 他把讨来的铜钱串成串,藏在破庙里的墙洞里。有回被小偷扒走半串,他追着小偷跑了十里地,最后累得瘫在地上,抱着小偷的腿哭:“那是给娃们盖学堂的钱啊,你不能拿!”小偷被他哭得发怵,把钱扔给他就跑,他趴在地上数着铜钱,数着数着笑了,眼泪却掉在钱串上,溅起小小的水花。 28年的光景,足够让青丝变成白发。武七的背早就驼了,走路一瘸一拐,那是年轻时被地主家的棍子打坏的。可他藏钱的墙洞越来越满,最后换成了沉甸甸的地契——230亩良田,租出去的粮食够养一村子人。乡绅们又来找他,说愿意出高价买他的地,他梗着脖子摆手:“这地是学堂的,谁也不卖!” 盖学堂那天,武七请了最好的瓦匠木匠。他亲自搬砖和泥,虽然瘸着腿,却比谁都卖力。有瓦匠偷偷问他:“武大哥,盖这么好的房子,咋不给自己留间正房?”他指着图纸上最大的那间屋子:“那是教室,得宽敞,娃们念书才亮堂。我嘛,有间柴房就行。” 学堂落成时,门口挂了块匾,写着“崇贤义塾”四个大字,是当地举人亲笔题的。开学那天,武七站在门口,看着几十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孩子背着书包往里跑,个个眼睛亮晶晶的。先生开始讲课,朗朗的读书声飘出来,武七蹲在墙根下,背靠着冰凉的砖墙,听着“人之初,性本善”,忽然咧开嘴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眼泪混着脸上的泥垢,淌出两道黑印子。 他还是天天讨饭,只是不再往墙洞里藏钱了。他把讨来的东西分给学堂里的穷学生,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比自己吃山珍海味还香。有学生给他鞠一躬,叫他“武先生”,他慌忙摆手:“我不是先生,我就是个讨饭的,你们好好念书,将来做个能认字、不欺负人的好人,就行。” 后来光绪皇帝听说了他的事,赏了他个“义学正”的名号,还赐了块“乐善好施”的匾额。乡绅们见了他,再也不敢叫“叫花子”,都恭恭敬敬地喊“武公”。可他还是那身破棉袄,背着破麻袋,走在集市上讨饭,只是腰杆好像比以前直了些。 有人说他傻,忙活一辈子,自己没享过一天福。武七听了还是嘿嘿笑,他心里清楚,那些朗朗的读书声,就是他最好的福气。就像他常念叨的那句顺口溜:“我积钱,我买田,修个学堂教贫寒。”这朴素的愿望,比任何金银珠宝都金贵。 参考书籍:《清史稿·武训传》《武训先生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