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年间,宋理宗赵昀一觉醒来,发现搂着自己的女子又黑又瘦,气得他要处置女子。没想到女子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宋理宗顿时没了脾气。 龙涎香的烟气还在帐顶缭绕,宋理宗猛地推开身边的人,锦被滑到腰间时,他看清了那女子的模样——脸颊上有层薄晒斑,手腕细得像能被风折断,粗布内衣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这哪是宫里的人?他昨夜喝了些酒,明明记得拉进帐的是新晋的淑妃,那姑娘生得粉白,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来人!”宋理宗的声音带着宿醉后的沙哑,龙床的帷幔被他扯得哗哗响,“把这刁民拖出去,杖……” “陛下可知,江淮的百姓连粗布都穿不上?”女子突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像块石子砸进水里。她没跪,只是直挺挺地坐着,晨光从窗棂漏进来,照见她眼底的红血丝,“臣妾昨夜在御膳房见了剩下的羊肉,光是扔掉的骨头,就够村里五户人吃三天。” 宋理宗的话卡在喉咙里。他盯着女子手上的薄茧——那不是宫女该有的手,倒像是常年做针线活的妇人。去年冬天,丞相曾递过奏折,说江淮遭了雪灾,百姓“易子而食”,他当时正忙着给景灵宫画壁画,随手批了句“令地方官赈灾”,转头就忘了。 女子见他没再喊人,又说:“臣妾是寿安宫的绣女,昨夜淑妃娘娘说身子不适,让臣妾替她来守夜。奴婢不敢欺瞒,只是想着,陛下或许该看看,寻常人家的女儿长什么样。”她从怀里摸出个布包,打开来是半块干硬的麦饼,“这是奴婢今早从家里带的,陛下尝尝?” 麦饼的碎屑落在明黄色的龙袍上,像撒了把细沙。宋理宗想起自己的早膳——燕窝粥要炖三个时辰,点心得用桃花汁染色,连盛粥的碗都是定窑白瓷。他突然没了力气,挥挥手让闻讯赶来的内侍退下。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奴婢姓陈,娘家在濠州。”陈氏拿起麦饼,自己先咬了一口,嚼得很慢,“去年冬天,奴婢弟弟就是饿极了,去地主家偷了块饼,被打断了腿。后来朝廷发了赈灾粮,可到我们手里时,只剩些发霉的谷子。” 宋理宗沉默着掀开被子。他走到窗边,看见宫墙外的柳树抽出了新芽,想起前几日去西湖泛舟,岸边的花船排了十里长,歌女们的裙摆上绣着金线。那些银子,若是省下来,能救多少像陈氏弟弟这样的人? 那天上午,宋理宗没上早朝。他让陈氏坐在身边,听她说濠州的事——说黄河决堤时,百姓抱着门板在水里漂;说税吏来收粮,连种子都要抢走;说村里的孩子,大多像她一样黑瘦,因为常年吃不饱饭。 “陛下,”陈氏说到最后,声音有些抖,“奴婢知道冲撞了圣驾,该受罚。可奴婢不怕死,就怕陛下永远不知道,宫外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宋理宗叫人取来纸笔,亲自写了道圣旨,让江淮的官员“即刻开仓放粮,不得克扣”。写完又觉得不够,索性带着陈氏去了御膳房,看着厨子把当天剩下的食材全装上车,送去城外的流民收容所。 淑妃后来被降了位分,不是因为失宠,是宋理宗发现她为了争宠,故意让陈氏替班,本想等陛下发怒时再出来“解围”。他没处置陈氏,让她回了绣房,只是常叫人去问濠州的消息。 有人说宋理宗是被陈氏唬住了,有人说他不过是一时兴起。可那年江淮的赈灾粮,确实比往年多了三成,流民收容所里,也真的有了能填饱肚子的粥。陈氏后来嫁给了一个禁军小校,离开皇宫那天,她没要赏赐,只带走了宋理宗没吃完的半块麦饼。 这件事听起来像个传奇,细想却满是无奈。一个皇帝要靠宫女“骂醒”才想起百姓疾苦,本身就是件荒唐事。南宋到了理宗时期,朝堂早被权臣和外戚把持,有人忙着斗党争,有人忙着修园林,谁还记得淮河边上还有人在挨饿?
陈氏的一句话能让皇帝低头,不是因为她多有胆识,是因为那句“百姓连粗布都穿不上”,戳中了王朝最痛的地方——当统治者看不见民间疾苦时,再华丽的宫殿,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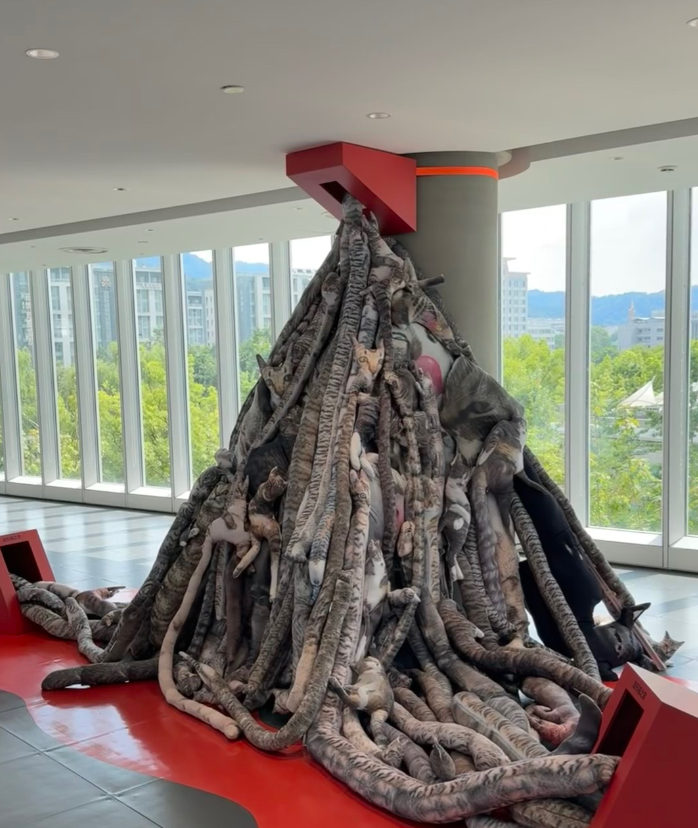
![一个群里四个人,还有一个没发言,是女婿害羞吗?[doge]](http://image.uczzd.cn/8560876989529805352.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