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马寅初没有提出人口论,没有实施计划生育,如今我国会怎样? “1963年盛夏的夜里,北京大学老图书馆外灯光昏黄——‘马校长,这账我翻了三遍,如果人口按目前势头往上冲,三十年后可就真吃不消了吧?’”那名年轻助教的话音刚落,就被夜色吞没。马寅初只是摆摆手,低声回了句:“数字不会说谎,问题在于我们信不信。”那一年,他已不再是校长,却仍在琢磨人口曲线与粮食曲线的交叉点。假设当时他的那套公式没有被搬上会议桌,中国的今天会是什么画面?很多朋友喜欢用一句“历史没有如果”来打住话头,可对人口这件事,多算一次并不吃亏。 先看基数。1949 年,中华大地约有5.4 亿人;如果继续沿着传统“多子多福”的惯性,按照当时接近 3.5 的总和生育率往前推,1970 年人口就可能触碰 9 亿大关。这并不是危言耸听——邻国印度在同一阶段的增长曲线就能提供参照。再把目光放到耕地,人均耕地面积原本就不足四亩,人口翻番后只剩两亩出头,人均粮食产量极有可能跌回三十年代的水平。一边是吃饭,一边是工业化要钢要煤要电,二者一挤,钢轨搁哪儿还真是个难题。 不少朋友可能会说,市场经济自身有调节功能,生得多不代表就一定会饿肚子。话虽不错,但在七十年代初,中国的轻工业仍停留在“布票肥皂票”的时代,城市化率刚破 20%,哪来那么多岗位接纳每年两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如果劳动力汹涌而来却没有机器可上、车间可进,结局只有两条:第一条,隐藏失业,统称“靠地吃地”;第二条,更直接——向外迁移。想想当年东南沿海偷渡出国的浪潮,如果全国性的就业缺口进一步扩大,这股流水线上的劳动力会不会更早、更大规模地奔赴海外?八十年代初广东、福建沿海渔船的引擎声,大概率要提前十年响彻夜幕。 再看城市。没有计划生育,六七十年代的城市常住人口会快速膨胀,城市住房与基础设施无论如何追都追不上。按当时投资强度测算,水、电、燃气的扩容速度顶多支撑年均 2% 的人口增长,而不是 3% 甚至更高。挤在筒子楼里的三代同堂,本来是一种过渡状态,可若人口压力迟迟不减,过渡就会变成常态。人们对居住品质的不满叠加对消费品短缺的焦虑,社会情绪难免发酵。别忘了,七十年代末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如果那时城市频现“米袋子”“菜篮子”危机,决策层会不会有足够底气把重心从“保供给”转到“抓效率”?这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人会把目光放到教育,“孩子多,人才多,创新不就多了吗?”理论上说得通,落到当年条件就犯难了。1975 年之前,全国每年高校招生不到 30 万人,如果考生多出一倍,可供应的教室、实验室并不会自动翻倍。大量青少年留在乡村,中等教育跟不上,高等教育更是“僧多粥少”,结果就是整体受教育年限提升缓慢。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制造业升级恐怕要再等几年,产业链也未必能顺利向上攀爬。试想,一台 286 电脑出厂价刚压到可接受区间,结果工人技能跟不上,返修率蹿到 20%,谁还敢放心把订单往中国丢? 当然,也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人口。如果没有计划生育,随着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推进,生育率仍会自然下行,这是全世界普遍趋势。可问题在于“下得慢”,峰值会更高,压力持续时间会更长。更高的人口峰值不仅意味着更多口粮,更意味着养老金缺口要更早暴露。一个简单的算式:若 2035 年人口达到 18 亿,而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 13%,老年人口就是 2.3 亿;而与之对应的依赖抚养比将远超当前。年轻人肩上的养老包袱提前加码,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经济增速下滑恐怕无法避免。 环境代价同样显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水泥、钢铁、化肥、农药产量节节攀升,即便在计划生育背景下,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已经拉响警报。如果人口继续快速增长,用水需求更大,南水北调或许不得不提前动工,整个工程体系再加一层急就章色彩。能源方面亦然,煤炭占到一次能源消费的七成左右,多一个亿人口就多消费若干亿吨标准煤,酸雨带和雾霾带的扩散速度只能用“飞奔”形容。彼时中国刚起步的环保机制,面对这种体量,几乎难以招架。 那么,也有人问:没有计划生育,我们会不会像印度一样拥有更澎湃的“人口红利”?答案并非完全否定,关键在“红利”能否转化为“能力”。如果工业与服务业无法提供足够岗位,教育与培训不到位,大量适龄劳动力可能沦为廉价体力,红利就会被稀释成低工资、低储蓄、低消费的恶性循环。此消彼长,孕育高端制造业和科技研发的土壤反而变薄。用一句更通俗的话来说:人再多,芯片厂里也只能站得下那么多工艺工程师。 放到国际博弈的大棋盘上,更庞大却就业不足的人口,有时还是一把双刃剑。谈判桌上,市场规模是一张好牌;可如果内部供需矛盾尖锐,竞争对手只需轻轻一捅,社会矛盾就会外溢。对于想冲击全球产业链高端的中国而言,外部压力与内部掣肘若同时发酵,腾挪空间随即变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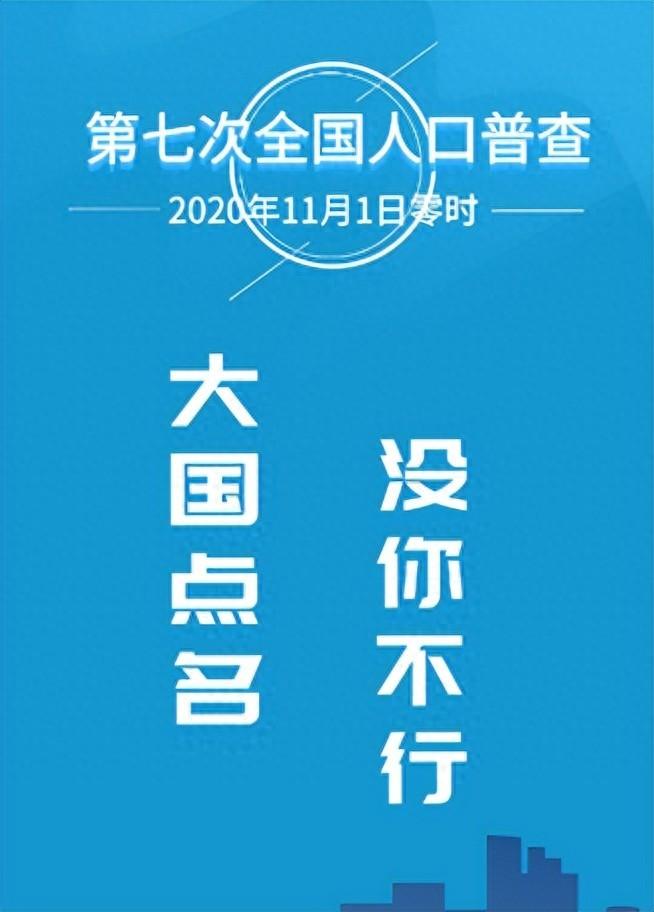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