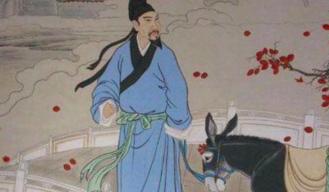宋朝有个官员,出身于苦寒农家,在他少年时,家里人曾和当地的平民定了婚约。后来他立志要出人头地改变命运,遂外出求学,科考数度不中,就慢慢和老家这边疏于联系了。 1027年,新科进士的琼林宴上一位身着崭新绿袍的年轻官员,却已收拾行囊,告假南归。 此刻,他策马扬鞭,激荡难平。 十年寒窗,一朝金榜题名,光耀门楣,本是人生至乐。 然而,他心中所想的却是那个约定。 他生于淮西贫瘠乡野,父母皆为佃农,勉强度日。 家中唯一的“资产”,或许就是父母为他与邻村农家女定下的娃娃亲。 那女子姓甚名谁,他只记得幼时随父母串门,曾隔着篱笆见过一个瘦小的身影、 生活的重压早早教会他现实的残酷。 他不甘于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胸中燃烧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渴望。 家中无力供其读书,他便白日帮工,夜晚借着月光,偷读借来的残破书卷。 那份婚约,是他童年里一个模糊却真实的存在。 后来,他得遇乡塾先生怜惜,收为弟子,得以正式开蒙。 再后来,他辞别双亲,踏上游学之路。 科场蹭蹬,屡试不第,尝尽世态炎凉。 十年间,他与家乡的联系,只剩下偶尔托人捎回的只言片语。 那份婚约,在求取功名的压力和对未来的渺茫中,渐渐蒙上了厚厚的尘埃。 然而,它从未消失。 所以,当李君风尘仆仆踏入阔别十年的家门,迎接他的,是父母喜极而泣的泪水、 双亲老泪纵横,拉着儿子的手,摩挲着他崭新的官袍,“出息了,我儿出息了。” 然而,当李君环郑重提出要践行婚约,迎娶那位邻村女子时,父母的喜悦瞬间凝固。 良久,父亲才艰难开口:“儿啊,那户人家。她爹娘接连病故,就剩那闺女一人,一场大病,又瞎了双眼。” 话音未落,母亲已忍不住啜泣起来。 李君脸上的笑容僵住,父母双亡,孤苦无依,更兼双目失明! 十年苦读,金榜题名,本可另攀高枝,结一门对仕途有益的姻亲,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青云梯。 然而,仅仅一瞬的震惊之后,他斩钉截铁地对父母说:“爹,娘!既有婚约在先,便是天地为证!岂能背信弃义?” 父母望着儿子眼中不容动摇的光芒,既感欣慰,又为儿子未来忧心忡忡。 翌日,李君换上干净的布衣,备了简单的礼物,亲自登门。 推开大门,一股浓重的药味混合着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 低矮的土屋内,一个女子蜷缩在角落的草席上,听到声响,她茫然地抬起头,空洞的眼神望向门口。 李君说明来意,女子听清后,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她猛地摇头:“不,不!大人如今是官身。我,我一个瞎眼的孤女,残废之人,怎敢高攀?” 而李君没有退缩,他蹲下身,目光直视着那双无光的眼睛:“姑娘此言差矣!婚约既定,岂因贫贱疾病而改?” 女子浑身一震,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汹涌而出。 她颤抖着伸出手,最终,冰凉的手指触到了李君温热而坚定的手掌。 她紧紧握住,泣不成声。 婚事简朴而庄重。 没有凤冠霞帔,没有八抬大轿。 李君用微薄的积蓄,为妻子置办了一身干净的新衣。 他牵着她,一步一步,走过田埂,在乡邻或敬佩、或不解、或惋惜的目光中,将她迎进了家门。 婚后的生活,清贫而艰辛。 李君的俸禄微薄,既要奉养年迈双亲,又要支撑起这个特殊的家。 妻子双目失明,生活起居处处需要照料。 李君毫无怨言。 不久,他们有了孩子。 新生命的降临,为这个清贫之家带来了无尽的欢笑与希望。 李君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意。 俸禄虽薄,他却从不贪墨一文,亦无半分愠色。 他一手抱着啼哭的婴孩,一手扶着妻子,在生活的泥泞中,走得安稳而踏实。 这份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的情义,温暖着彼此,也悄然在乡里传开。 然而,宦海风波难测。 数年后,李君在任上因秉公处理一桩豪强侵占民田案,得罪权贵,遭人构陷。 年轻的皇帝翻阅案卷,目光停留在吏部附议的“流三千里”的处置意见上。 学士躬身称是,并将李君婚后清贫自守、勤勉为官、夫妇和睦、乡里称贤的事迹简要禀明。 皇帝闻言,动容良久。 他在那份公文上,批下八字:“其行可悯,留任以观。” 李君得以留任,他感念皇恩,更加勤勉克己,清廉自守。 此后十余年,他虽无惊天伟业,却始终秉持初心,造福一方。 然而,就在他即将携家眷赴任州府之时,妻子却因多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李君悲痛欲绝,抚棺长恸。 他拒绝了所有续弦的提议,余生未再娶。 多年后,苏轼谪居黄州,偶闻此事。 彼时他历经宦海沉浮,看尽世态炎凉,更能体会这份在权势与浮华面前,对一诺一盲女坚守一生的纯粹与不易。 他心潮澎湃,挥毫写下《李君行状》,盛赞其“重然诺,轻富贵,守贫贱,笃伉俪,虽古之义士,何以加焉!” 文章流传开来,李君之名,虽未显于庙堂勋册,但在士林与民间口耳相传,化作一曲关于信义与深情的绝唱。 主要信源:(文献——《梦溪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