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的弟弟叫宋子良,宋子良在上海结识一舞女,致其怀孕,宋子良给其银元2000,嘱其打胎,并哀求地说:“这个孩子名不正言不顺,还是打掉的好。 夜风挟着潮气掠过外滩,灯火落在黄浦江面,亮得像一长串碎银。 铜管乐在霞飞路的舞厅里拖着尾音,腻腻的香粉味与雪茄烟丝缠在一起,混进空气,叫人头脑发晕。 有人推门进包厢,只听见银元撞击大理石台面的清脆声响——两千块现洋,分量不轻,摆在那里却像几颗被随手掷出的骰子。 宋子良的脸在灯罩下半明半暗,嘴角撇出一点笑意,随口丢下一句“名不正言不顺”,似乎把一条尚未成形的生命当成烟灰抖落。 旁侧的张小姐捏着烟嘴,指甲掐得粉底微裂,红唇轻抿,没改口。 她要十万元,一个不算低的数字,据老会计暗算,足够买下法租界一小段街角的石库门。 舞女群里议论声顿起,纸扇遮住窃笑,有人嫌她心太大,有人悄悄称她有胆量。 名门少爷抛弃私生子,这样的料放到报摊总能卖光。 张小姐看准的便是这点,只消纸墨一铺,宋家的脸面就被拽进泥里。她赌得凶,可也明白,凡是赌局,座位从来不平。 宋子良不愿和家里长辈扯脸,也懒得同官方多生枝节。 转了个弯,他去了杜月笙的公馆。 那幢法式洋房常年亮着壁灯,朱门背后传说聚着半座上海的影子。 主人剪着油头,西服纽扣扣得齐整,说起话来温吞低柔,偏生袖口常挂腥风血雨。 青帮在上海不是台面上的衙门,却能让衙门自觉绕道。 一个眼色,一块印章,江面便能卷起谁也不敢多问的浪。 两人密谈不到一炷香,杜月笙抬手合扇,随口应了句“包在身上”。 答应得轻,仿佛吐掉一口烟。 市井里混迹多年的师爷暗暗摇头:这话翻译出来,就是张小姐没有退路。 夜色跟着降温,法租界的梧桐叶哗啦啦一阵,像有人悄悄翻书。 没过几天,一道信儿送到张小姐手里,中汇银行有款项待领。 她挑了件月白旗袍,银色盘扣攀到锁骨,指尖点了同色指甲油,鞋跟踏在石板上,节奏明快。 门口执事客气领人,走廊深处灯光昏黄。 房门关的瞬间,四道黑影扑来,木棒闷声砸下,空气震得发颤。 毛巾堵住嘴,呛着一股含血的香粉味。 麻袋系紧,粗麻绳勒得皮肉生疼,耳边只剩“嗡嗡”耳鸣。 夜半的小火轮贴着江岸滑行,船桁嘎吱几声,那只麻袋被一脚踢进水里。 浪尖闪着黯光,旋涡卷走紊乱的泡沫,一切又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 翌日晨雾笼江,报纸照例堆满街角。 头版全是股市曲线与舞台剧彩照,只字未提有人失踪。 舞厅灯罩擦得锃亮,新来的姑娘吊着眼线,踩着旧木地板,笑得一如往日。 经理查点名单,红笔一划,把“张小姐”三个字删得干脆。有人问起,她去香港的说法就此流传,像一粒轻灰飘散。 青帮同宋家各得其所,杜月笙照常出入洋行,捐米济贫的牌匾挂得更高;宋子良在私人俱乐部抿掉陈酿,举杯应酬,袖口钻扣依旧闪亮。 世道学会闭口,街边茶摊偶尔飘来只言片语,旋即被风吹散。 底层巷口的留声机唱片翻面,嘶哑的旋律换首再跳,谁也不敢提旧日曲名。 张小姐的故事并非孤例,赣南有女子为显赫人家诞下双胞胎,深夜一针哑然;北平巷口的学生妹死在巷尾,却只换来报纸角落一句“意外”。这些名字像断掉的灯丝,遥远又寂静。 舞女们懂得规矩更苛刻,青春换酒资,皱纹换冷眼,若想另谋活路,往往拿肚子去赌。 可对手若握着权力与帮派,筹码再大,也难过那些暗潮涌动的掌心。 民国的光影被后世镜头拍得璀璨,西装革履、旗袍曳地、爵士乐曲曲入耳。 可只要夜路拐进弄堂深处,臭水沟的腥,棚屋里的湿冷,随处可见。外滩霓虹照不进码头棚户,机器轰鸣盖不住乞儿咳嗽。 社会秩序像一张绷紧的鼓皮,上层轻轻一敲,底层便跟着颤。 张小姐赌输了,骨血沉在江底,不留碑、不留名;青帮维持了所谓“体面”,宋家少爷保住了声誉,上海照样自称“东方巴黎”。 江水东流,从不回头,拍岸声日夜不息。 码头工在晨光里背麻袋,舞小姐在夜灯下补口红,报馆学徒抱着新排铅字奔跑。谁都晓得风月里暗股汹涌,却各自闭口,生怕下一个浪头卷走自己。 偶有人站在外滩长栏,望见黑水泛光,低声念一阵旧事,旁人听完只叹一句“世道如此”,然后快步离开。 档案夹深处,那页失踪记录被更厚的文件压住,角落卷起灰,像给历史留了不易察觉的缺口。 翻到缺口,能看到微弱字迹:权力一旦与冷漠结盟,真相就会沉底;底层若只剩沉默,结局往往无声。 铜管乐又起,街灯再亮,旧时代的暗纹仍旧埋在灰里,等着下一双眼去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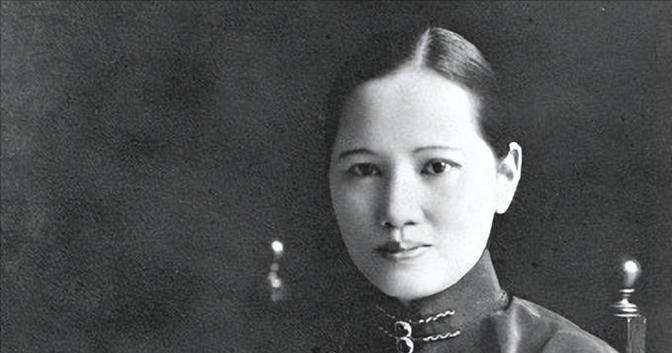



![杜月笙如果来了,能站在哪里?[思考]](http://image.uczzd.cn/2132587354235060390.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