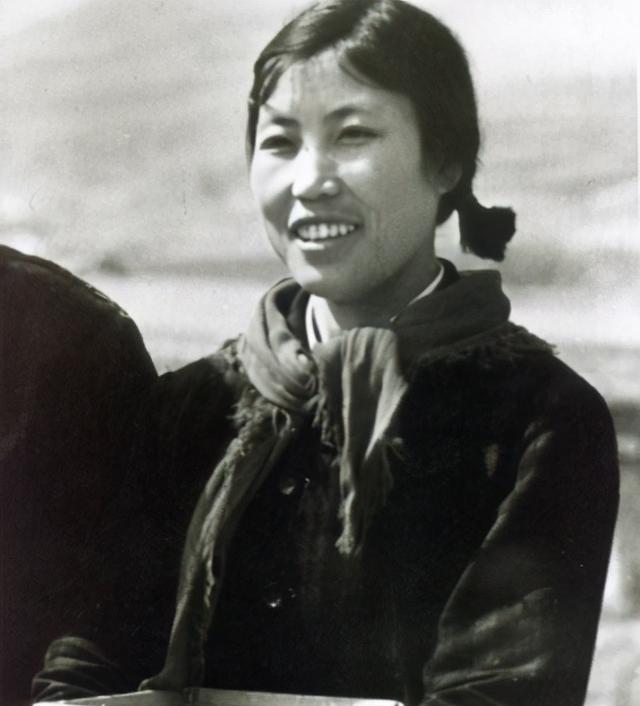陈永贵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他本来可以享受“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 陈永贵的烟瘾大得吓人,大寨时抽自种的旱烟,呛得人眼泪直流,进了北京改抽3毛钱的廉价香烟,硬是不要“特供”。他本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却偏偏守着粗茶淡饭,一碗小米粥、几口馒头就打发了。他是谁?一个从黄土高坡走出来的农民,爬到副总理高位,却从没丢下那股土气。 陈永贵这人,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大寨村,家里穷得叮当响。爹早没了,他跟着妈苦熬,靠给人当长工混口饭。1948年,他入了共产党,赶上土地改革那拨儿,干得热火朝天。1952年,他当上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带着村民把山沟沟改成梯田,粮食产量蹭蹭往上涨。1964年,《人民日报》发了篇《大寨之路》,全国都喊着学大寨,陈永贵一下成了农业战线上的大红人。 他的烟瘾真不是盖的。在大寨时,他抽的是自家种的旱烟,那味儿又冲又辣,抽一口能呛半宿,可他抽得美滋滋。后来到了北京,他改抽香烟,但眼光忒“抠门”,专挑每包3毛钱左右的便宜货。有人给他递“特供”烟,好烟嘛,谁不想要?他偏不,摆摆手就拒绝了,说自己抽惯了这个,换贵的反而不舒坦。 吃的方面,他也一点没变城里人的样。每天早上,一大碗小米粥,热乎乎地端上来,配着老咸菜或者苦瓜,稀里呼噜几口就下肚了。中午可能换成馒头或者面疙瘩,还是那几样咸菜打底,简单得不行。要是有客人来,他也不讲究排场,亲自下厨煮一锅面条,招呼大家一块儿吃,吃完还咂咂嘴,说这味道才正宗。 你说他当了副总理,咋还过得跟村里老农似的?其实,他压根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不拿副总理的工资,靠的是大寨村记的工分,外加一点补贴过日子。粮食呢?也是大寨分给他的口粮,带到北京接着吃。他常说,自己是农民出身,吃这些就够了,多了反倒糟蹋。 穿得更别提了,一身对襟棉袄,脚上蹬着布鞋,从大寨穿到北京,没换过样。刚到北京时,他住京西宾馆,人家给他配警卫员,他死活不要,自己叠被子、扫地,干得有模有样。宾馆走廊的灯老开着,他看不下去,一趟一趟跑去关,说浪费电不行。他这习惯,跟城里那些讲究排场的人一比,简直格格不入。 陈永贵这性子,离不开大寨那段日子。大寨村条件差,山高地薄,粮食全靠人抠出来。他当书记时,天天带头干活,扛锄头、挖梯田,硬是把穷村子搞出了名堂。那时候讲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把这套信条刻在了骨子里。到了北京当副总理,他还是这副德行,觉得吃好的、穿好的,跟自己没啥关系。他常挂嘴边的话是:“咱是干活的,不是享福的。” 再说那烟瘾,旱烟也好,3毛钱的香烟也罢,对他来说不是啥嗜好,就是提神儿的工具。干活累了,点上一根,眯着眼抽几口,整个人就缓过来了。他不抽贵烟,不是装清高,是真觉得没必要。那些“特供”烟,搁他眼里,跟身份挂钩,他最烦这个。 1980年,农村改革来了,大寨模式不吃香了,陈永贵也辞了副总理的职。他没赖在高位上,主动搬出官邸,住进北京一个普通四合院。出门不坐公车,挤公交,拎个布袋子,跟普通老头没两样。刚退休那会儿,他闲不下来,老盯着天发呆,后来工作人员陪着他,才慢慢适应。 1983年,他跑去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每周去地里转转,指点农活。那些年轻员工挺佩服他,觉得这老头接地气,说话直白,干活还带劲。可惜,他抽了一辈子烟,肺早扛不住了。1985年查出肺癌,1986年就走了,72岁。临终前,他没啥特别要求,就说把骨灰埋回大寨虎头山,守着那片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