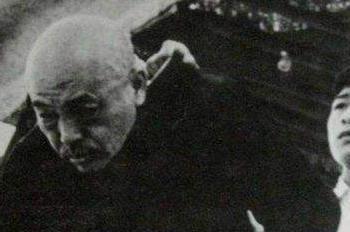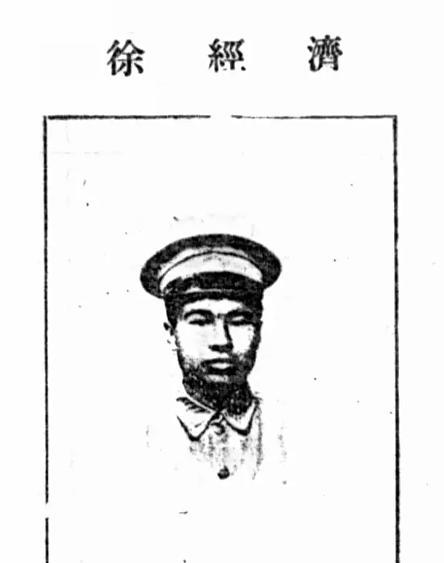1934年,新婚后不久,才女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约会,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你也是知识分子,干嘛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那一记耳光落下的时候,苏青没有退让也没有流泪,她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攥着两角皱巴巴的钱,米缸已经空了,她只是想向丈夫要点钱买米。 丈夫却扬手就扇了她一巴掌,冷冷丢下一句:“你也是读书人,想要钱自己去赚。”这句话毫不迟疑地砸进苏青的心里,把她所有的隐忍和幻想击得粉碎。 苏青出生于宁波一个典型的书香世家,父亲冯子履是留美归来的银行家,极重视教育,也极为开明,苏青自幼聪慧伶俐,擅长写作,读书极快,几乎将家中藏书读了个遍。 她是长女,一直被视为家族未来的希望,凭借优异的成绩,她考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中央大学外文系,原本被认为将来会在学界或文坛开创一番事业。 命运并没有按着她应得的轨道继续向前,父亲投资失误,银行破产,欠下巨债,不久后抑郁而终,这个曾经受人敬重的家庭,一夜之间陷入风雨飘摇。 苏青正在大学读书,学费无着,生活捉襟见肘,为了不辍学,也为了让母亲免于流离失所,她接受了母亲安排的婚事与同学订婚,用对方的聘金续了学业。 当时的苏青并不热衷婚姻,对丈夫谈不上爱意,只是抱着希望能共度困境的想法,她以为只要持家勤恳、尽责尽力,总能得到理解与平和的生活。 然而婚后不久,一切开始偏离了她的设想,丈夫的家庭保守封闭,婆婆对苏青出身的优越感耿耿于怀,始终看她不顺眼,动辄责难她“不像个媳妇”。 苏青继续坚持写作,却被丈夫冷眼看待,说她那是“没事找事”,丈夫不支持她读书,更不愿她参与写作与社交,认为女人的天职就是持家、生子。 苏青怀孕、生子,接连生下四个女儿,丈夫家中从上到下都面色难看,婆婆态度愈发冷淡,丈夫日渐疏远,不再与苏青沟通,甚至很少回家。 她一面操持家务,一面照顾年幼的孩子,日复一日重复着被无视的生活,她曾试图与丈夫重建连接,却发现对方根本无意经营婚姻,只关心外面的应酬与新鲜。 直到那一天,苏青带着孩子回娘家探望母亲,归途中偶然路过茶楼,无意中看见丈夫与表嫂坐在靠窗的位置,两人神态亲密、言笑甚欢。 苏青停下脚步,在门外站了很久,内心一阵发麻,但最终转身离开,她没有质问丈夫,也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直到那天家中断了米,她鼓起勇气去找丈夫要钱,当她站在厨房门口说出口那句话时,丈夫毫不犹豫地打了她一巴掌,并甩下那句“你也是读书人,想要钱自己去赚”的讽刺。 那一刻,苏青彻底明白忍让不会换来尊重,沉默只会换来更深的轻贱,当晚,苏青没有再向丈夫低头,她在孩子们入睡后翻出多年前写作用的稿纸。 她不再顾忌礼教,也不再压抑情绪,而是用笔记录下自己十年婚姻中的每一份委屈、羞辱与痛苦,她写生育时的孤立无援,写婆媳间的隔阂与鄙夷,写丈夫的冷漠背叛,写这个家如何将她一步步逼入绝境。 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学创作,是她对现实生活的清算,她把成稿寄到杂志社,不久后便收到回复,文章将被连载,并支付稿费。 这是苏青人生第一次用自己的文字换来收入,她没有兴奋,也没有欢呼,只是静静地将钱放进抽屉,心中悄然下定决心:她会靠写字活下去。 作品刊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在女性读者中间激起巨大共鸣,杂志社主动找上门,希望苏青继续写长篇,她没有停笔,很快完成了一部长篇记录自身婚姻经历的作品。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迅速售罄,接连重印数十次,许多女性读者在书信中表达感谢,说她写出了她们自己说不出口的真实。 靠这部作品,苏青一举成名,稿酬也让她彻底脱离了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她不再犹豫,带着孩子搬出那个家,住进了租来的小屋。 虽然空间狭小,生活拮据,但她终于能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她继续写作,创办杂志,参与出版工作,在文坛站稳了脚跟,她变得干练而果断,不再让任何人主宰自己的命运。 离婚之后,苏青依旧承担着照顾孩子的重任,在战乱与权力更替的时代背景下,苏青也并非一帆风顺,为了维持杂志运转,她曾不得不向一些当权者示好,也因此背上骂名。 可她从未停止写作,从未停下为生活而奔波的脚步,她曾与胡兰成短暂交往,最终看清对方的本质,也毫不犹豫地抽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