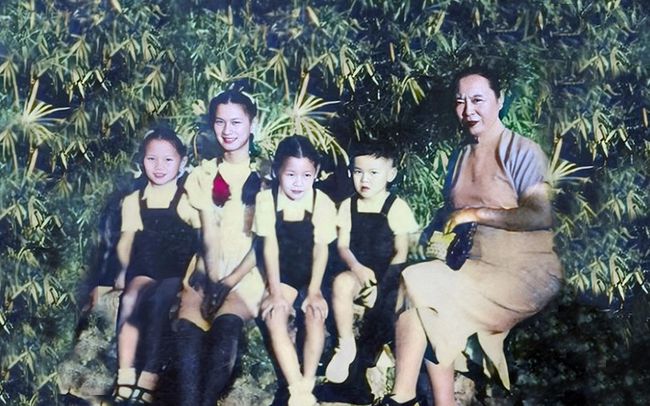1917年,江冬秀等了13年,终于如愿嫁给胡适。新婚夜,江冬秀却让胡适睡地上,胡适问:“难道不用圆房吗?”江冬秀说:“您不当我是妻子,我何必让你做夫君呢?” 信源:百度百科——江冬秀 1917年冬,胡适回到了久别的祖国。 那一年,他已是留美归来的博士,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而在安徽绩溪老家的江冬秀,却只是一个没有太多文化的小脚女人,默默地守着一纸早在十三年前定下的婚约。 十三岁那年,胡适和江冬秀订下婚事,两人还只是懵懂孩童。这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江家在当地虽算不得显赫,但祖上勤勉持家,讲究门第相当。 江冬秀从小便被告知:你将来是胡家的媳妇,是胡适的妻子。她信了,等了,也认了。 胡适远赴重洋求学,见识广阔世界,结交西方女性,吸纳新思想。他越走越远,逐渐不再属于那个围着灶台转、脚裹三寸金莲的旧时女人。 可在江冬秀的心里,他始终是她的丈夫——她等了十三年的夫君。 江冬秀没有读过多少书,却也不是全然不明事理的妇人。她识得自己与胡适之间,隔着的不仅是洋洋万里海峡,更有文化、思想与心灵的鸿沟。 可她始终守着那封婚书,日日在心头摩挲,像盼着一场春雨,等来他回家。 1917年,他终于回来了。 胡适回国不久,便在亲友催促下,举行了婚礼。他虽心有不甘,但也不愿拂逆母命。婚礼朴素,来宾络绎。他是新文化的旗手,却依然无法挣脱旧礼教的枷锁。 洞房花烛夜,屋里挂着红灯笼,屋外鞭炮犹响。新娘江冬秀静静坐在床沿,头上盖着红盖头。 一动不动。胡适走进来,心中一阵复杂。他走到床前,轻声说了句:“你先歇息,我去外间看看。” 江冬秀没有动,直到他返回屋内,才揭开盖头,缓缓开口:“你今夜便睡在地上吧。” 胡适一愣:“这是为何?难道……不用圆房?” 江冬秀神情平静,语调里却透着一股倔强:“您不当我是妻子,我又何必让你做夫君?” 她不是傻子。这些年她虽不识多少字,但胡适在美国的一些事,她不是没听说过。 有人悄悄提起,他在美国结识了一位洋女子,两人一度甚是亲密。还有人说,他早就心属他人,只是身不由己才回国成婚。 江冬秀知道胡适不爱她。甚至可以说,从未爱过。她心里苦,却苦得有骨气,不肯卑微求爱。 她从来都知道,自己不是胡适心中的理想女子,但她是胡适名正言顺的妻子,是等了十三年才换来的这份名分。 胡适沉默了。他看着这个小脚女子,忽然生出几分复杂的情绪:怜惜?歉意?还是内疚? 他本以为,江冬秀是个没文化的传统女人,应当顺从、柔弱。但此刻她站在床前,瘦小的身影竟有几分决绝的力量。胡适叹了一口气,终究什么也没说,铺了褥子在地上睡了。 从这天起,他们名为夫妻,却更像两条平行线,客客气气,却始终无法真正走近。 胡适在外讲学、撰文、参与新文化运动,是民国风云人物;江冬秀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孩子,是典型贤妇良母。 他们偶尔也会交流,江冬秀甚至开始学习识字,希望能看懂胡适写的文章——哪怕只是能多了解他一点。 有一年,胡适在外地讲学归来,带回一堆新书。江冬秀翻了翻,不解其意,只淡淡地问:“你这次见了谁?” 胡适怔了一下,没回答。江冬秀也没追问,只是转身去厨房煮了汤,说:“你舟车劳顿,喝点热的。” 这句话,没有怨,也没有责,只剩下深埋心底的隐忍。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位。他是新派知识分子,倡导自由恋爱;她是旧式传统妇女,相信媒妁之言。 他追求思想的独立与个性;她守的是祖训与婚姻的忠贞。他们没有爱情,却有一份难以割舍的责任和家庭的纽带。 江冬秀这一生,或许过得并不幸福。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尊严。她用一种朴素又坚定的方式,站在了那个风云时代里一个独立的角落。 许多年后,胡适晚年在日记中写道:“冬秀贤慧,性格坚强,虽不识字,却极明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