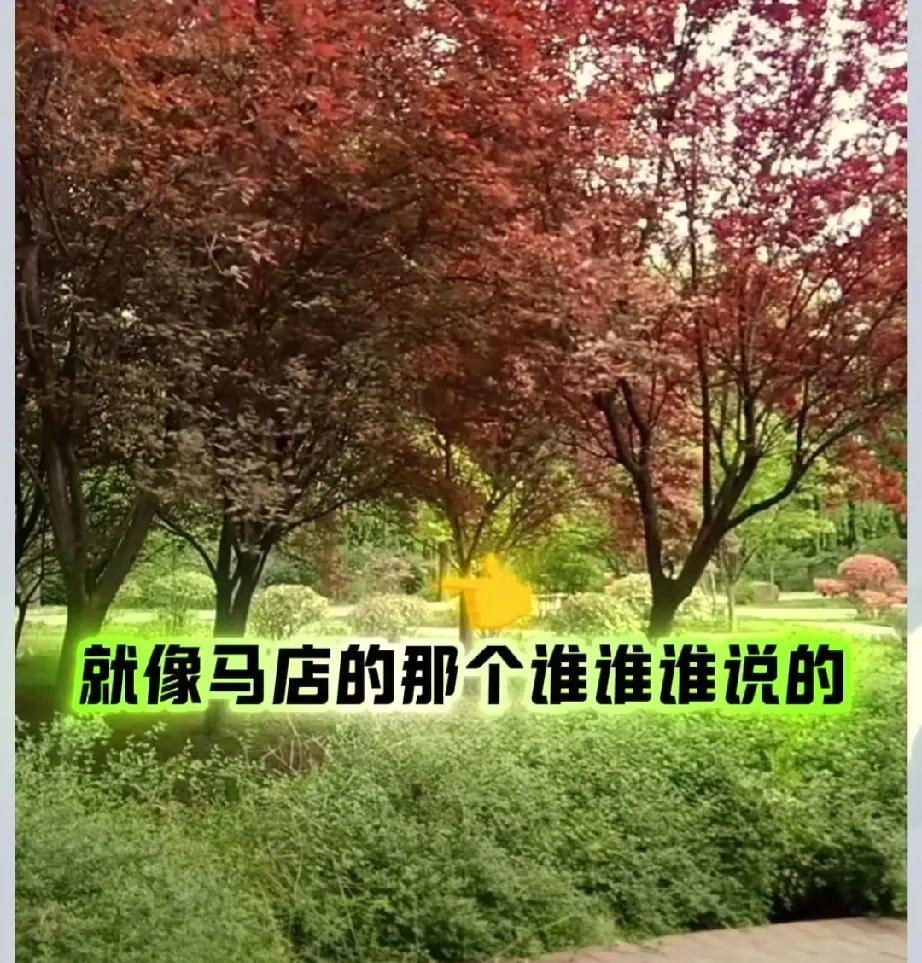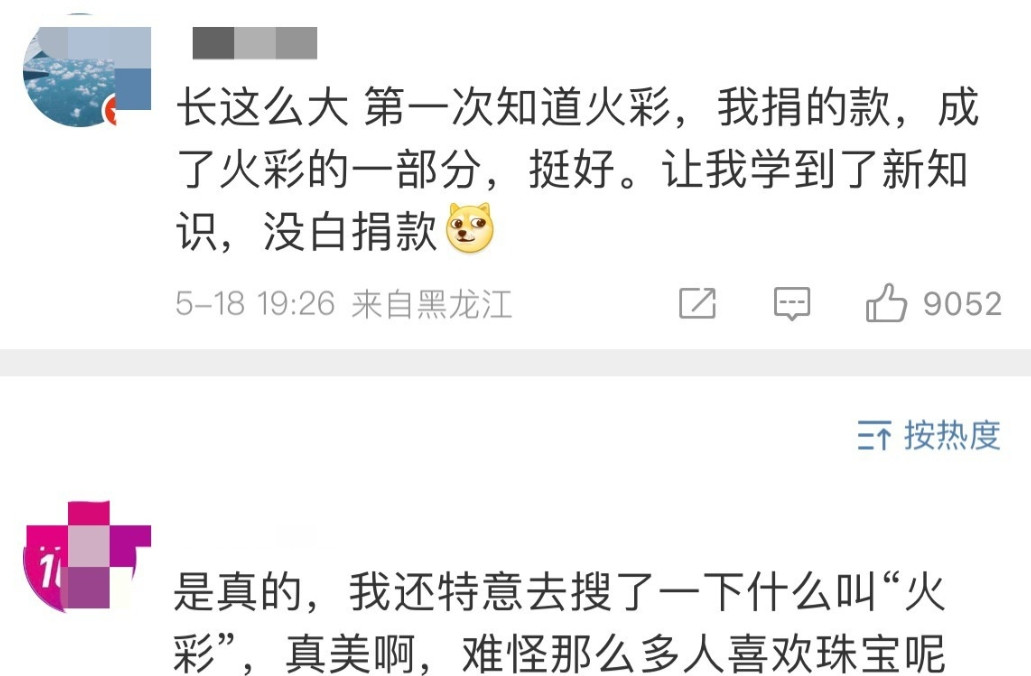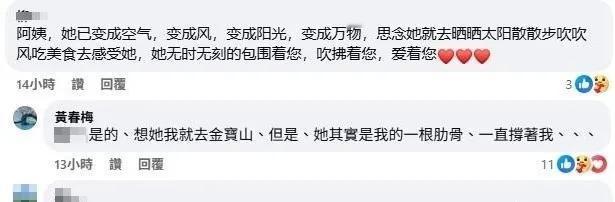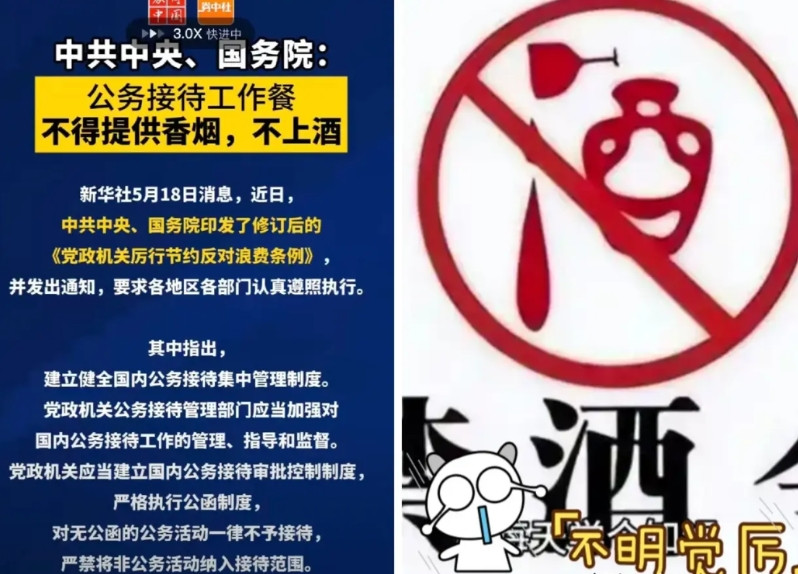1995年,东莞一家殡仪馆的何师傅,准备将一具女尸送进焚化炉,突然一阵风将她身上的白布掀开,未等何师傅做出反应,女尸竟动了起来。 一阵微风,看似平常的拂动,却在1995年7月27日的东莞市东湾殡仪馆内,吹开了生与死的界限。 何亚胜是殡仪馆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这天他如往常一样对即将火化的遗体进行入殓检查。当他走到那具被标记为"无名女尸"的遗体旁时,一阵风突然吹过,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掀开了一角。何亚胜弯腰准备重新盖好白布,却在这个瞬间,看到了令他毛骨悚然的一幕——那具"尸体"的腹部似乎在微微起伏,喉咙和手指也有着细微的颤动。 "这人还活着!"何亚胜大惊失色,立刻呼叫同事前来确认。经过检查,确实如此!殡仪馆迅速拨打了120,将这个奄奄一息的女孩送往医院。 医生们接诊后发现,女孩状况危急,全身瘦骨嶙峋,面容模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最危险的是,她随时可能离开人世。这时医院院长果断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将人救活。" 在这个鬼门关外被救回的女孩,名叫陈翠菊,1977年出生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一个贫困的小山村。在她17岁那年,为了补贴家用,她提出了外出打工的想法。家人为了她的这个梦想,卖掉了准备用来盖房子的木材,凑了200块钱作为路费。 带着家人的期望,陈翠菊来到东莞,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然而,现实远非想象中美好。初次远行的她很快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持续高烧不退。食堂的饭菜不合胃口,她常常只吃一两口就放下碗筷。饥饿、发烧加上高强度的工作,让陈翠菊的身体每况愈下。 那天下班后,头晕目眩的陈翠菊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到河边,看到一艘倒扣的小船,便坐在上面休息,不知何时昏倒在小船下,无人发现。工厂曾多次派人寻找她,但都未果,以为她受不了苦逃回家了,所以也没有报警。而远在贵州的家人也多次托人打听,同样一无所获。 几天后,一位老船工翻转小船时,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陈翠菊。由于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物品,她被当作"无名女尸"送往殡仪馆,后被法医鉴定为死亡。这才有了殡仪馆中那一幕"起死回生"的奇迹。 经过三个月的昏迷,陈翠菊终于睁开了眼睛。而此时,在浙江金华的美术教师陈仲濂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她的故事,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他思考了整整一晚上,决定去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给她提供学习绘画的机会。 陈仲濂在给陈翠菊的信中写道:"你的经历让我很心痛,我想这是因为你文化不高的原因,我愿意供你读书,教你学画画,让你将有一技之长,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如果你愿意,可以带上弟弟一起来,我会承担你们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 1996年6月10日,金华火车站人来人往。陈仲濂手举写有"陈翠菊"的牌子,焦急地张望着。当他看到拖着行李、瘦得像竹竿般的陈翠菊时,一股酸楚涌上心头。眼前的女孩走路摇晃,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她吹倒。陈仲濂强忍泪水,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女孩培养成才。 初到金华的陈翠菊身体虚弱,经常生病,很多人都摇头说她不可能学好绘画。但陈仲濂没有放弃,他鼓励陈翠菊每天清晨5点起床锻炼身体,而他的母亲则精心为陈翠菊准备营养餐,帮助她恢复健康。 身体的恢复只是第一步,陈翠菊心理上的自卑与胆怯同样令人担忧。她不愿与人交流,总是低着头独自走路。当同学们从报道中认出她并议论纷纷时,她变得更加封闭自己。陈仲濂耐心地对她进行心理疏导:"同学们并没有恶意,只是好奇你过往的经历,你将自己封闭起来,友谊也会被拒之门外。"在陈仲濂的引导下,陈翠菊慢慢敞开心扉,开始主动与同学交流。 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陈翠菊来说,学习绘画绝非易事。美术课上老师讲解的绘画技巧,她常常听不懂,落后于同学。挫败感让她有一次竟然把画纸撕毁,扔掉画笔离开了画室。她开始怀疑自己:"我真的适合学绘画吗?我这样会不会拖累了陈老师?" 这种挣扎让她萌生了放弃的念头,曾经的打工姐妹也劝她:"学习那么辛苦还费钱,来打工吧,打工能挣到钱,这样你就不会拖累陈老师了。"陈翠菊差点就此离开,不想让陈仲濂的辛苦付诸东流。 得知这一消息,陈仲濂第一次对陈翠菊发了火:"你现在的生命是那些好心人给的,你当初说好的要去报恩,现在不想了?"这番话如当头棒喝,让陈翠菊想起住院时对好心人的承诺:"我以后一定回来报答你们。"她重新拾起画笔,坚持了下来。 看到陈翠菊的决心,陈仲濂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引导她朝着山水写意绘画的方向发展。每当陈翠菊在绘画上有突破,陈仲濂就把她的作品拿到讲台上表扬,增强她的自信心。 1999年,学习绘画三年后的陈翠菊,在陈仲濂的鼓励下参加了当地的绘画比赛。当宣布她获奖的那一刻,陈翠菊喜极而泣:"原来,我真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