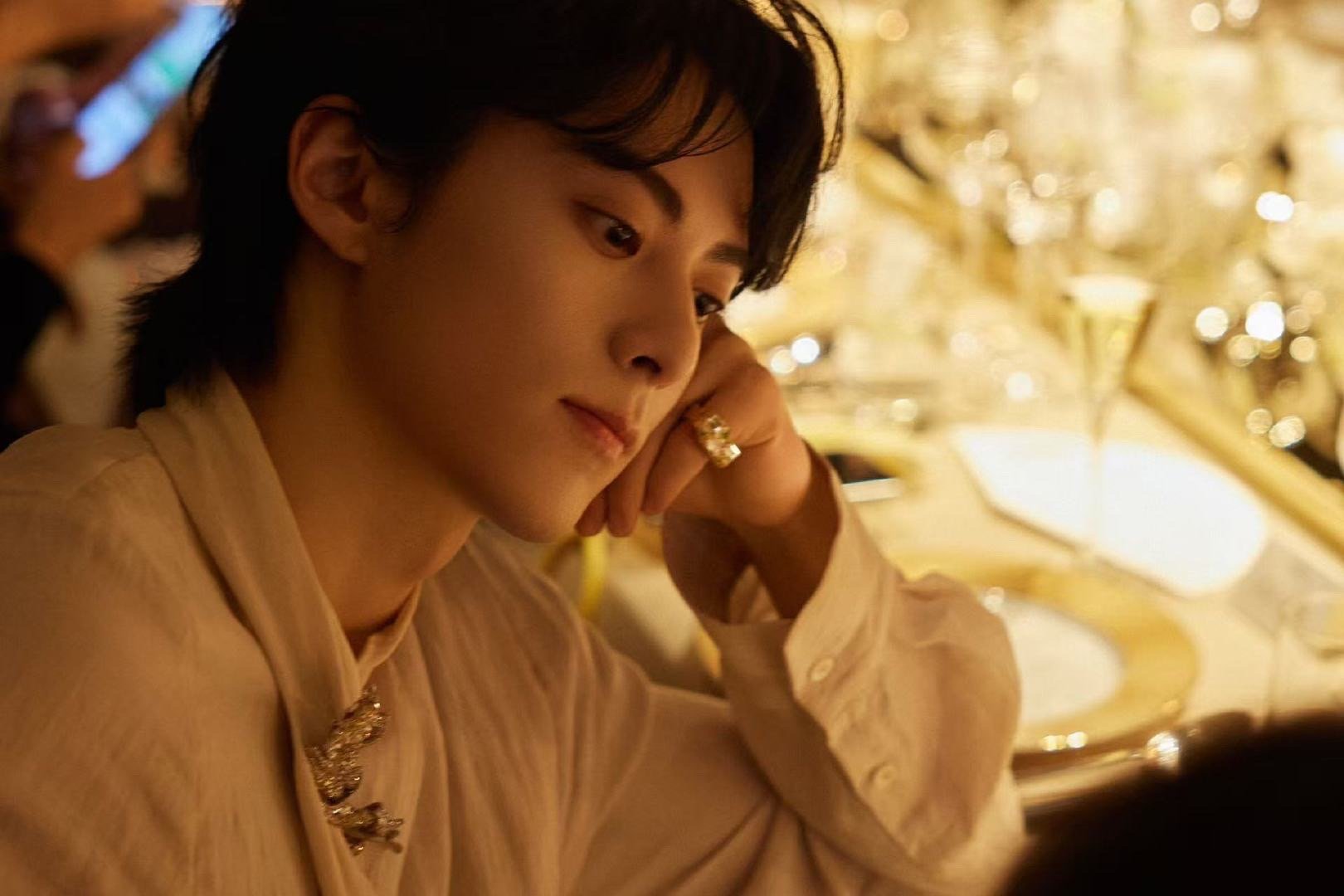1300年前,1名唐代贵妇,将一个小纸条偷偷藏入手腕上的银镯里。看似不起眼,但却在1944年的偶然发掘后颠覆想象,成为蜀地印刷术的一大“领头羊”。 1944年春天,四川成都的四川大学正忙着修新校舍,工人们挥着铁锹挖地基的时候,突然听见铁家伙碰着硬物的声响。 刨开土层一看,底下露出来几块青砖的边角,在场的老工头一拍大腿:“这土里怕不是埋着古坟?” 消息传到学校,校方赶忙请来了考古专家,那时候国家正逢战乱,文物保护的意识还不强,好在川大自家就有顶厉害的考古学者——冯汉骥教授带着学生赶到现场,围着土坑忙活开了。 果不其然,四座古墓在泥巴里现了身,三座是南宋的,独有一座唐代的墓穴保存得最完整。 这唐墓也就两米长、一米宽,棺材木头早烂没了,就剩下几颗生锈的铁钉。墓主人仰面躺着,嘴里含着两枚开元通宝,手腕上套着个黑乎乎的银镯子。 要说这镯子起初真不起眼,表面锈得跟铁片似的,要不是冯教授的学生用刷子慢慢清理,根本看不出接口处有道头发丝细的缝。 几个年轻人拿着镊子捣鼓半天,突然从镯子夹层里抽出一卷泛黄的纸。 这纸薄得能透光,摊开来足有脸盆大,上头密密麻麻印着古怪文字,角落里还印着“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十五个字。现场的老学究们激动得手直哆嗦——这可是唐朝人用雕版印刷的《陀罗尼经咒》! 要说这经咒来头可不小,佛教在唐朝香火旺,老百姓都信随身带着经书能保平安。可谁也不能成天揣着本厚经书,手艺人就想出个巧法子:把经咒印在轻薄的茧纸上,塞进贴身首饰里。 墓主人手腕上这只银镯子,正是千年前成都龙池坊卞家作坊出品的“护身符”。 最让专家们拍案叫绝的是那个“成都府”的地名,史书上写得明白,成都打从公元757年才改叫“成都府”,这经咒少说也得是安史之乱后印的。 要知道以前公认最早的印刷品是868年的《金刚经》,这回的发现直接把中国雕版印刷的历史往前推了百来年。 更绝的是经咒上的图案线条流畅、文字清晰,说明那时候的印刷技术早就成熟得很,保不齐还有更早的印刷品等着出土呢。 要说这卞家作坊可不简单,当年唐玄宗逃难到成都,带去了长安城的大批工匠,保不准里头就有雕版印刷的好手。 成都平原物产丰饶,造纸张、刻木板的条件样样齐全,这才催生出专门印经咒的私家作坊。 从这经咒的做工看,卞家的雕版师傅手艺了得,字迹比后来敦煌出土的《金刚经》还要工整三分。 如今这张千年经咒躺在四川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薄如蝉翼的茧纸泛着淡黄,上头菩萨像的衣纹还清晰可辨。 来看展的老百姓总爱趴在柜子上找那行“卞家印卖”的小字,都说要沾沾古人的巧劲儿。博物馆的讲解员逢人就念叨:“别小看这张纸,它可是改写了四大发明的历史!” 要说这古墓发现也是赶了巧,当年川大刚从峨眉山搬回成都,新校址选在望江楼附近的荒地上,谁想得到稻田底下埋着唐代的宝贝?冯教授后来在笔记里写,墓主人就是个普通百姓,陪葬的碗罐都是粗陶做的,唯独这经咒藏得精心。 可见在战火连天的年月里,老百姓把平安的念想都寄托在这方寸之间的经文上了。 打从这经咒出土,考古界就盯着蜀地不放,果不其然,后来成都又挖出好些唐代印刷品,有印着佛像的绢布,也有带商家标记的历书。 这些物件凑在一块儿,拼出了盛唐时期成都作为西南印刷中心的繁华图景。那些在历史书上轻飘飘的“雕版印刷”四个字,借着这张泛黄的经咒,总算在世人眼前活了过来。 主要信源:(成都日报——手镯里的《陀罗尼经咒》:探秘唐宋成都印刷巅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