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因洗衣服被邻居打了一耳光,他62岁的妻子杨绛立即冲上去还手,被邻居夫妇抓住肩膀按在地上,提起来,又摔下,最后狠狠扔到一堆木架上。钱钟书听到动静,拿着一块厚木板,对着男邻居劈头就打。
当年杨绛怀孕的时候,钱钟书就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要将关爱全部给到阿圆(钱瑗的乳名),她就是我毕生的杰作。”
杨绛曾在《我们仨》中说到到“阿圆”的优秀:在爷爷钱基博眼里,她是“读书种子”,在外公杨荫杭眼里,她是“过目不忘”。
而钱钟书给女儿的评价则是: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但钱瑗和爸爸最“哥们”,自然最像他。
钱钟书疼爱女儿,每晚在钱瑗临睡前,就会给她的被窝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具。每当这时,钱瑗又会像“扫地雷”一样,把父亲布下的“陷阱”清理干净。
然而这个长在蜜罐,备受宠爱又优秀的钱瑗在婚姻方面却没有那么顺遂。
钱瑗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认识了王德一的男同学,两个人都是学校美工队社团的成员,两人经常一起负责学校的黑板板和海报。
相处的时间久久了,钱瑗喜欢上了王德一,病大胆向它表白,并最终在相识13年 后,两人走进婚姻的殿堂。
杨绛对这个女婿也非常满意,常说他是一个和善忠厚的人。
一次,王德一送钱钟书上火车时,见到旁边有人行李太多,王德一便主动去帮忙。
婚后,两人生活得非常幸福,可这幸福只维持了半年的时间,那是一段特殊的时间,王德一被牵扯其中,他不堪其辱,最终在宿舍楼自杀身亡。
那时候钱瑗和父母在北京干面胡同15号的社科院宿舍住。
后来经历了特殊时期以后,钱钟书的同事濮良沛,赵翔凤夫妇,成了他们的邻居,其实他们的到来说白了就是为了“监督”钱钟书一家。
由于濮良沛夫妇家三代同堂,所以钱钟书必须让出两间房来给他们,同时厨房和卫生间也两家共用。
但是公用的毕竟不方便,不过钱钟书夫妻觉得“远亲不如近邻”,所以他们经常忍让与帮助赵翔凤夫妇,比如帮他们把他家孩子的摇篮搬家里去,帮他们生煤炉子的火。
但是赵翔凤夫妇从来没有说过感谢的话。
1973年一个周末,杨绛请了一个钟点工来洗衣服,可赵翔凤非要钟点工免费给他们先洗。
钱瑗不愿意,因为钟点工是自己家花钱请的,就算帮忙洗,凡事也有先来后到…没想到邻居一气之下直接一巴掌打在钱瑗脸上,还说她不是好人。
杨绛看到女儿被打,便和赵翔凤打了起来,这时候钱瑗跑出去找居委会主任报告。
正在屋里写作的钱钟书听到动静,出门一看见妻子被打,抓起一块厚木板向濮良沛头部打去,他一躲闪,却被击中了胳膊。
这时杨绛怕钱钟书吃亏,急忙拉着丈夫跑回屋里。这时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来了,经过调解,大家都散开了。
或许洗衣服这件事只是两家人打架的导火索,因为他们夫妻表面对钱钟书一家和气,实则背地里常常说杨绛一家的坏话。
那时钱媛的丈夫去世,一家人对这件事都避开不谈,杨绛为了不让女儿伤心,于是挨个去拜托邻居,请求他们不要在女儿面前提及此事。
这对夫妻听完后,敷衍地答应着杨绛,转头就跑去问钱媛:“怎么没见你丈夫啊,你来这这么久他都不来看看你吗?”
钱媛只低声说道:“他去世了,麻烦你们不要说这件事了。”谁知这两人听后,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们给钱媛取了一个恶毒的外号:“臭寡妇”。
关于打架这件事,杨绛后来还专门为此事写了一篇《从“掺沙子”和“流亡”》,发在《南方周末》上,可见此事绝非空穴来风。
1997年,钱瑗因为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罹患脊柱癌,在最后的弥留之际,年过八旬的母亲杨绛对她说:“安心睡吧,我的女儿,我和你爸爸都祝你睡好。”
在钱瑗去世后的第八天,处于昏迷中的钱钟书突然大喊:阿媛,我们转去自己家里。
当杨绛先生赶来时,他又再度陷入了昏迷之中。
在某一天钱钟书书在清醒的时候提及“阿媛”,杨绛贴在他的耳边轻声地对他说道:阿媛走得很好,我已经祝福过她了。
没过多久,钱钟书的身体也不好了。弥留之际,他给杨绛留下了一句话:“绛,你要好好过。”
自此,钱家三人组算是彻底地散了。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先生写下了《我们仨》,追忆了一家三口的逝水流年,有欢乐,有痛苦,有相聚,有别离。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携手走完了人生的时光。
书中曾说到:“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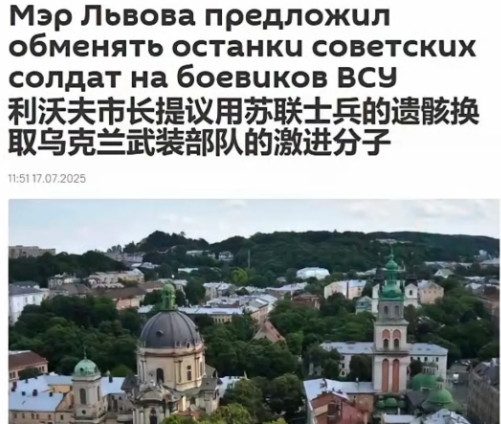






齐齐主人816
钱瑗是个好老师,非常敬业。
dream 回复 05-10 02:07
愿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