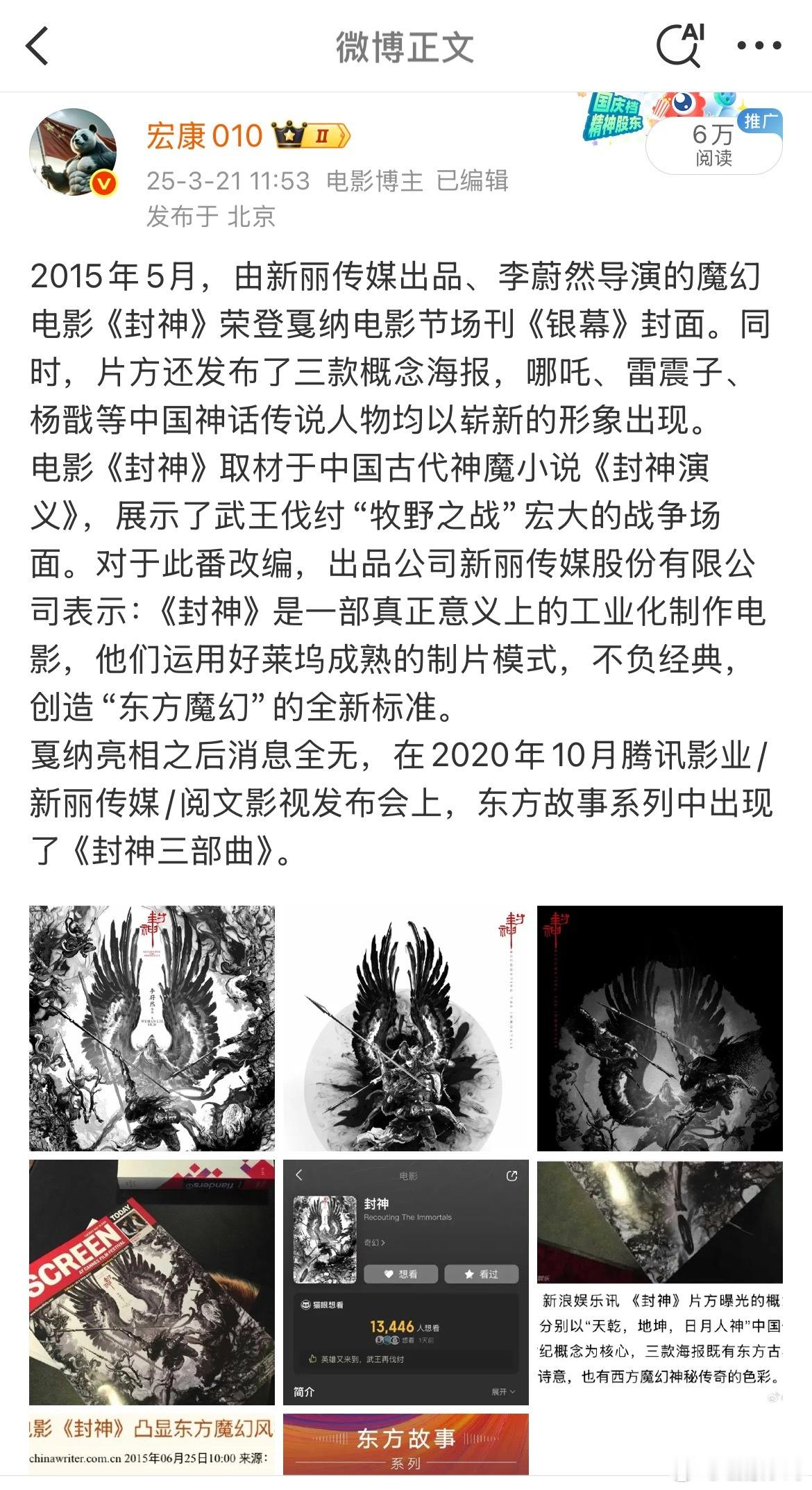池塘边,毛泽东13岁,正跟他爹吵得不可开交,毛顺生气急败坏地骂他是“逆子”,而毛泽东倔得很,干脆跑去池塘边上站着,扬言要跳水。 他不是装样子,是真敢跳,围观的亲戚邻里都吓傻了,毛顺生被逼得没辙,只能低头,让他象征性下跪了事。 从这件事起,毛泽东再也不是那个任打任骂的农村少年了,他学会了用硬碰硬的法子捍卫自己。 毛家在韶山冲算不上穷,但也不富,毛顺生靠种田、放高利贷起家,规矩死板,干活讲究效率,不讲情面。 他把赚钱当头等事,指望毛泽东接班当个精明账房,可毛泽东偏偏不爱这些,他爱看书,尤其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种“闲书”,越禁越看。 他不服老子摆出的架子,经常跟他吵嘴,家里请的私塾老师也被他顶撞过。 十岁那年,有一次先生讲《论语》,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毛泽东质疑这有啥用,还说这不是讲废话?结果被先生当场打了三天。 打完之后,他干脆一走了之,闹罢课,他父亲见他宁肯离家出走也不低头,只能把他喊回来,这事才算了,毛泽东就是那时候开始觉得,硬气一点,别人就不敢欺负你。 这股劲儿没散,越长越重,村里有人穷得快揭不开锅,他爹却趁机买了自家亲戚的田地,价格压得很低。 毛泽东私下里骂老子太绝,把亲戚当肥羊宰,这些事让他对旧社会那一套人吃人的规矩越来越看不惯。 他读到《盛世危言》,书上讲富强、改制、打破旧礼教,跟他心里想的有点像。 读书越多,他的“逆子”名声越坐实,可在他眼里,那不是忤逆,而是活得像个人。 到了1911年,他去长沙参军,没靠家里人帮忙,结果被拒了,理由是没人担保,他没放弃,四处找人。 最后靠彭友胜这个老乡帮他担保,彭是个铁匠出身,在部队当副目,还有个叫朱其升的,也是铁匠,仨人聊得来,就结拜做了兄弟。 彭友胜看毛泽东一穷二白,还经常分饭给他吃,毛泽东这辈子吃过不少苦,但这顿饭他记得清楚。 他后来常讲,铁匠、农民这些人最实在,心里没弯弯绕绕,他说“卑贱者最聪明”,不是喊口号,是亲眼见过、亲身体会过。 毛泽东这人一旦认准谁,就特别敬重,彭友胜退伍后回村当铁匠,手艺不错,但也辛苦。 别人笑他“粗人”,毛泽东却说:“他脑袋灵得很,打个锄头都能琢磨一天怎么省力。”晚年他还念着彭,觉得铁匠这活是技术活,是智慧的象征。 他写《农村调查》时说,农民能写好文章,能当诗人,他真心觉得这些看起来“没文化”的人,比那群只会掉书袋的“先生”强多了。 1950年,土改搞到韶山,按政策,像毛家这种以前雇人干活、收租吃利的,要被划成富农。 村里干部一开始有点犹豫,怕给毛主席家贴这标签不好看,结果毛泽东一封信回过去,说得特别干脆:“我父亲的土地和钱,是剥削来的,该怎么划就怎么划。”还主动退了300块钱给政府,算是“退押金”。 有人说这是“立规矩”,毛泽东压根不解释,他觉得革命不是给自家谋好处的,也从来不觉得“我是主席我就能例外”。 其实,这种态度早在他小时候就有苗头,他看不惯父亲欺负弱亲戚,也从来不巴结村里当官的。 村里谁挨欺负了,他有时候还会站出来吵一架,别人说他“生来就是个造反种”,他不否认。 他就是讨厌那种人压人、事靠关系走的风气,他愿意跟铁匠、农夫一起吃饭,不愿意跟老爷太太坐一桌。 有人说毛泽东是从“逆子”一路走上革命路的,这话不全错,但说白了,他就是从小不吃那一套。 他不信祖宗规矩,也不怕权威,看得不顺眼的事,他要么不理,要么干脆推翻。 小时候对父亲顶嘴、罢课、站池塘;长大了要改社会、打旧制度,他心里头有杆秤,不管是毛家人还是别人家,只要不公平,他都想掀桌子。 当然,他的性子也不是没有代价,小时候常挨打,读书也走了不少弯路,他读了几个学校,都没老老实实待到毕业。 但他从不觉得后悔,他常说,“书不在多,在精”,有用的学问不一定得从课堂来,他喜欢一个人去乡间走,跟农民聊庄稼、看他们怎么灌溉、怎么养猪。 后来搞革命,他说政策要“眼睛向下”,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别光看报表,要去村里看看猪圈有没有修好,老百姓米缸里有没有米。 他走的这条路,确实带着很多个人的印记,没有跟父亲对峙那次,也许他不会那么早明白什么是反抗;没有彭铁匠和朱其升的那顿饭,也许他不会那么信任“下层人民”;没有1950年那封信,也许韶山土改不会那么利落。 有人说他是天生的领导者,其实更像一个一路顶着压力硬闯出来的倔强孩子。 他这一生,跟权威的较劲从没停过,从家里到国家,他从不信“命”,也不吃“规矩”。要说他为啥后来能成大事,归根到底,就是小时候那股子“你要打我,我就跳塘”的犟劲。 参考资料: 《毛泽东传(1893-19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