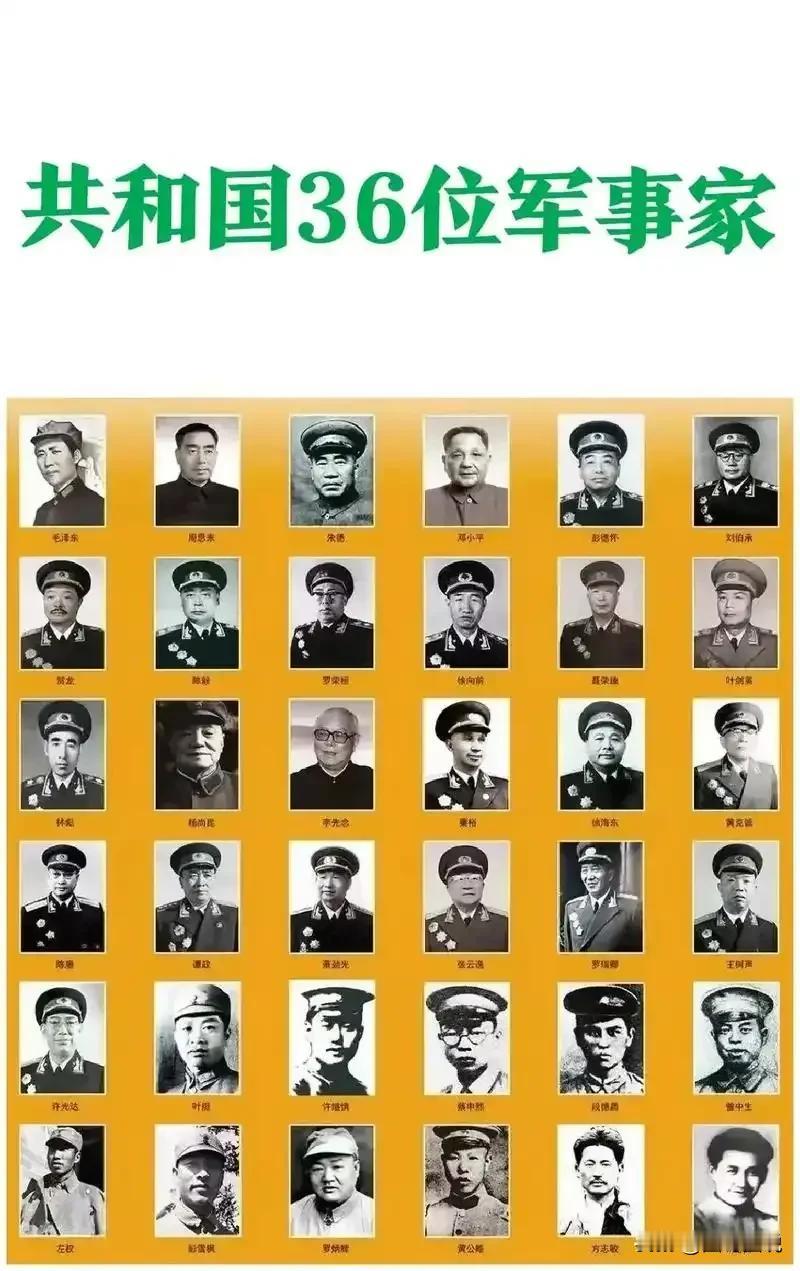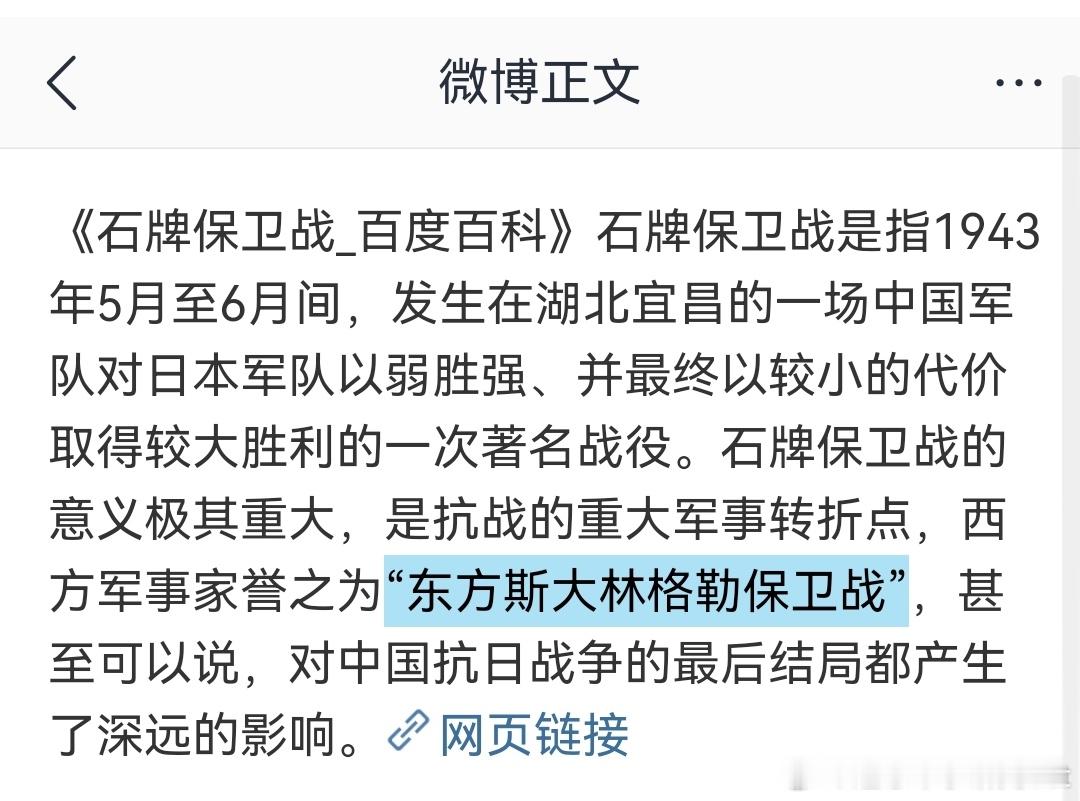1922年的新婚之夜,闻一多为了不与新娘同房,不洗头、不洗澡、不刮胡子。让人没想到的是,新娘的花轿到了家门口,他却溜之大吉。然而,家人不肯放过他,硬是将他抬进洞房。不过后来,闻一多对妻子的态度却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在那个年迈,包办婚姻是常态,很多青年男女或迫于压力,或是因为孝顺,都不敢反抗父母的意愿,但是也有不少有新思想的青年敢于尝试违背父母的意愿。闻一多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最终他却成了离不开包办婚姻妻子的那个男人。
到底怎么回事?还要从闻一多的经历说起。
闻一多出生于1899年,原名闻家骅。五岁他就被父亲送到了私塾。13岁那年,闻一多以鄂籍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看着如此优秀的闻一多,除了家人替他高兴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那就是他的姨夫高承烈。因为他非常喜欢闻一多,他希望自己的女儿高孝贞能嫁给闻一多。于是他就主提出与堂姐(闻一多的母亲)结为亲家。
闻一多的母亲觉得两家门当户对,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就这样,闻一多在出国之前,家里人就把他的婚事定了下来。
按照当时的规定,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子们要在清华学习十年,然后再到美国学习五年。1921年,当闻一多即将从清华毕业前往美国,家人却一直写信催他回家成亲。
闻一多非常苦恼,在他的心里,他向往的是自由恋爱,他对包办婚姻厌恶至极。尽管家人写信催促,他依然无动于衷。
但是家里人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怕闻一多去美国后会变心,甚至让闻一多的堂兄特意到清华去说服他。最终,闻一多只好被“押”回家成亲。
对于闻一多来说,结婚就像是上刑场一样痛苦。婚礼那天,为了表达内心的不满,他不洗脸不理发不刮胡子。眼看新娘的花轿到了门口,他却跑了出去。
那天晚上,闻一多被家人抬着进了洞房,但是他却不理新娘子,让新娘子一个人干坐着,连她的盖头都不掀。
其实新娘子高孝贞并不是闻一多想象的那么不堪。她比闻一多小四岁,温婉淑德,长相大方端庄,是个读过书的女子,而且还没有缠足。
在新婚之夜受到如此冷落,作为新式女子的高孝贞着实心里不好受,但她第二天依然会为丈夫对自己的冷落向公婆解释说“他喝多了,怕影响自己休息,才去书房睡的”。
之后,在父母的强压下,闻一多才在家里多待了一段时间。但是期间,他和高孝贞就像是陌生人,各干各的事,贤惠的高孝贞理解闻一多的想法,她能做的就是不去打扰他,给他时间让他改变。
不久,闻一多就去了清华。而且还收到了女同学的表白信。虽然向往自由恋爱,但是毕竟自己是已婚人士,尽管对妻子没有感情,但是他还是拒绝了女同学的表白。
在清华期间,闻一多给家人写信让高孝贞去读书。闻一多这样的做法,说明他他对妻子还是有所期待的。
高孝贞心中明白,丈夫是当代新青年,自己也必须跟得上他才行,所以她去读了书。
闻一多知道妻子去读书后,就经常给她写信。在那个见字如面的年代,文字是表达内心与情感的最佳方式。
在来往信件的交流中,闻一多发现高孝贞是一个有才情有思想的女子,通过一段时间的沟通交流后,两人的感情逐渐加深,在异国他乡的闻一多越来越依恋妻子,每天都盼望着她的信。
此时的高孝贞的心是甜的,她知道,丈夫终于接受了自己。
1925年,闻一多回国,在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安顿好后他立即把妻子和女儿接来北平,开始了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1930年,闻一多去青岛大学任教。高孝贞带着孩子在老家。期间闻一多遇到了心仪的女子,但是就在流言四起时,他把妻儿接到了身边,他用实际行动斩断了不该有的感情。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高孝贞带着孩子和闻一多住到了一起。
期间,闻一多专心工作。高孝贞全心全意支持丈夫工作,照顾好家庭和孩子。闻一多每周六晚上都会带着一家人去看电影,去逛颐和园等。
抗战爆发后,闻一多一家人冒着炮火搬到了昆明居住。在这里,一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为了改善生活,高孝贞带着孩子去小河里抓点鱼虾,她自己开垦了荒地种菜。看着妻子持家很是辛苦,闻一多瞒着她把自己的狐皮大衣换成了钱来补贴家用。
就这样,这对当初深受包办婚姻折磨的夫妻,在昆明艰苦无比的生活中相濡以沫,互相扶持,互相照顾,度过艰难的时期。
1946年,闻一多被暗杀。高孝贞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改名为高真,将自己的家作为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后来,她冒着生命危险带孩子投身解放区,替闻一多完成了他未完成的事业。
那个年代,很多人成为包办婚姻下的牺牲品。不过闻一多与高孝贞,则是包办婚姻下的幸运儿。从陌生人到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他们经历了很多。
闻一多和高孝贞的婚姻故事也说明,比起一见钟情的刹那心动,日久生情的相濡以沫更让人动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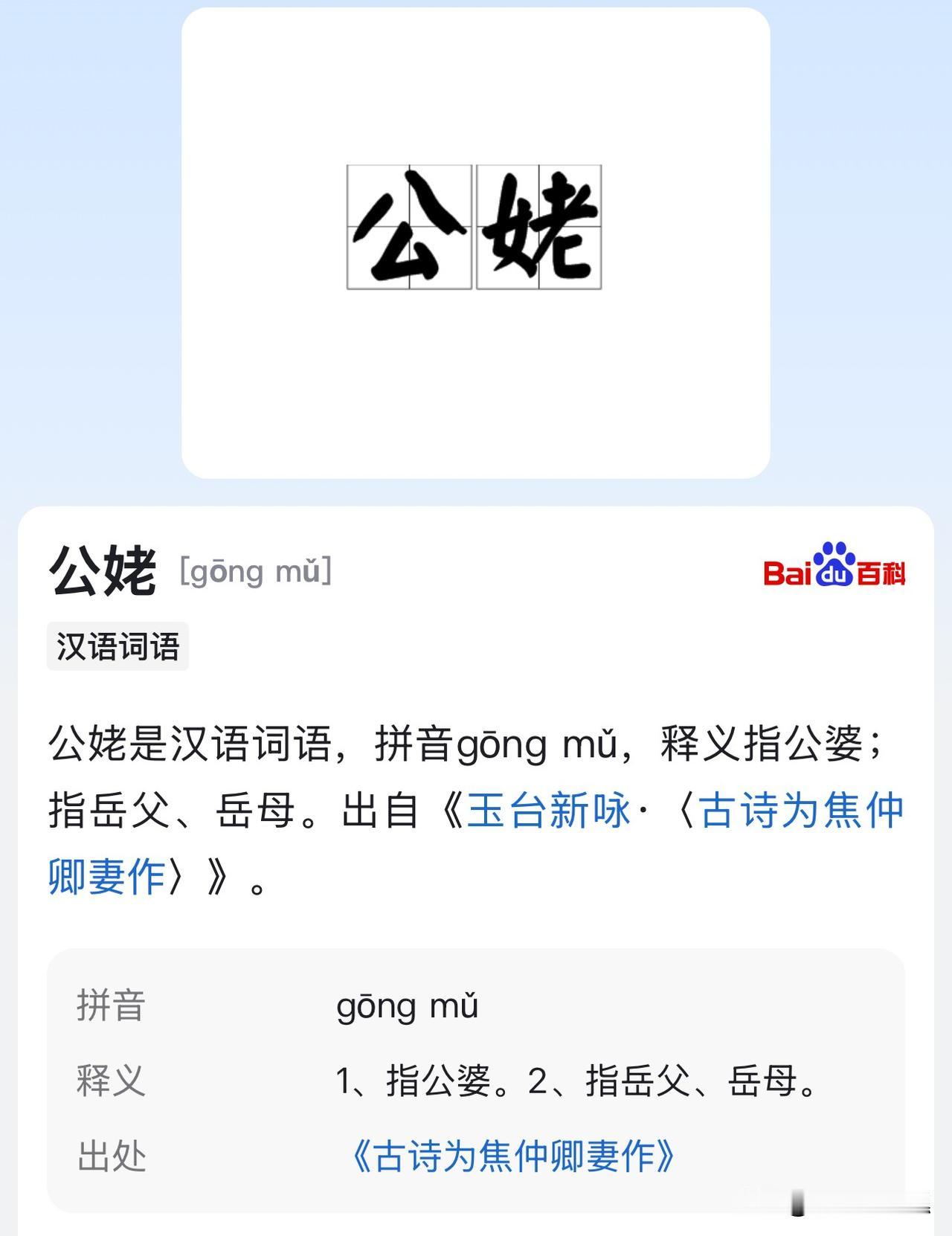
![搞了半天,备受尊敬的大国,原来是大阴帝国[无奈吐舌]](http://image.uczzd.cn/9048281834001629884.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