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明锦化身“玄学达人”说起,孙玉良:折射当代社会对未知焦虑】
采访李明锦,深为她的传奇经历所惊讶。从中山大学的传奇“校花”成长开始,到成长为中国唯一进入埃及国家舞团的优秀东方舞者;从环球游学51国79城的旅游达人,到最后成为玄学研究者,预测领域涵盖时政、经济、金融、A股热点涨跌等且屡有命中,其旺盛的学习及钻研能力令人折服。现在的李明锦已化身为一名“玄学达人”,或者称作“易学达人”、“环球堪舆风水师”,也有人赞许她为“玄学天后”或通俗地叫她“美女算命先生”,其铁粉甚至说她的预言“比天气预报还准”。但我观察李明锦也常发现,她也会时不时处于焦虑之中。这种现象的背后,折射出当代社会对未知的焦虑与对确定性的渴望,而没有信仰的年轻人如果再遭遇生活的打击,比如事业失败、失恋离婚、亲人离世等等,对未知的焦虑感更会增强。
我是把诸葛亮、刘伯温式的“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视作神话传说的,对于“推背图”也半信半疑。玄学与科学究竟能否兼容?未卜先知是否真的存在科学依据?易经是科学还是伪科学?这些问题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不只我半信半疑,许多人都与我持相同的态度,大多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因为玄学常被赋予神秘色彩,所以吸引许多人进入这一领域乐此不疲孜孜以求,当然也包括传奇人物李明锦。
当代玄学易学家陈烯尧提出了一种“原文化”理论,认为玄学本质是“旋转之学”,宇宙中的能量通过旋转产生四季更替、生老病死等规律,并形成“因果循环”的法则。这种解释试图将玄学与物理规律结合,例如将牛顿第三定律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视为能量旋转的体现。但“原文化”理论缺乏实证支持,更多是哲学层面的隐喻,和中国的老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使用的方法差不多。而在现代科学视角下,玄学中的“未卜先知”更像一种心理机制。例如,网络占卜师通过模棱两可的话术,如“桃园三结义,独出梅一枝”,引导受众自我代入,利用“巴纳姆效应”和“幸存者偏差”强化可信度。心理学研究表明,压力越大的人群越倾向于相信玄学预测,以此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这都是命啊”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现代人则将命运视为电脑程序,甚至认为宇宙也是虚似的,冥冥之中也有造物主操控。我认为李明锦的预言之所以被追捧,正是因为她为焦虑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情绪出口,如此而已。
历史中的“预言”真相,实际上是偶然性与规律性相互交织的结果。看似精准的预言案例,例如《史记》记载的“弧箕服,实亡周国”,最终通过褒姒入宫、烽火戏诸侯等事件应验,实则是后人将偶然事件与预言强行关联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某些预言确实包含对规律的洞察。《周易》提出“变易、不易、易简”三原则,试图通过观察自然与社会规律预测变化。例如古代王朝更迭中的权力失衡问题,本质上与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困境相通,我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科学”,并非相信命运的玄学。这种预测更多是利用经验归纳指导未来的社会实践,而非玄学中的“预知未来”。比如伟人写出《论持久战》预言日本必然失败并且被历史所证明,我们称他为洞察未来的大战略家而非玄学家。
科学的核心在于可验证性。暗物质、暗能量等概念虽未被直接观测,但其存在通过引力效应等间接证据支撑,并能在数学模型中被推导。相比之下,玄学的“五行能量”、“因果报应”等理论缺乏可证伪性,主观附会的情况比较多,无法通过实验复现,这是最大的问题。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曾让部分人联想玄学的合理性,但科学界普遍认为微观粒子的随机性无法推导出宏观命运的确定性。混沌理论更表明,长期预测在复杂系统中几乎不可能。真正的科学预测比如天气预报是依赖数据建模与误差修正而达成的,与玄学中的“天命论”有本质区别。
当代年轻人对玄学的热衷,本质是“疗愈经济”的体现,更多反映的是群体对精神慰藉的需求。玄学更多体现的是“情绪价值”而非科学价值,如果不注意就会陷入“欺诈陷阱”,到寺庙或道观烧香,花费大量的香火钱,或者轻信某些人“破财免灾”的说法如此这般这般,往往花了大钱也办不了大事,解决不了他自身的问题。科学早已证明,真正的未来无法被“剧透”。我认为:玄学的价值不在于预知命运,而在于提供心理缓冲,更多的是具有文化符号与精神寄托意义。用科学的态度生活,以玄学的智慧自省,才是应对未知的最佳方式。对未来产生焦虑是杞人忧天,活好当下才是人生智慧,悟透“为”与“无为”的真谛,用“上善若水”的态度保持顺其自然的心态,才不会自寻烦恼,快乐度过每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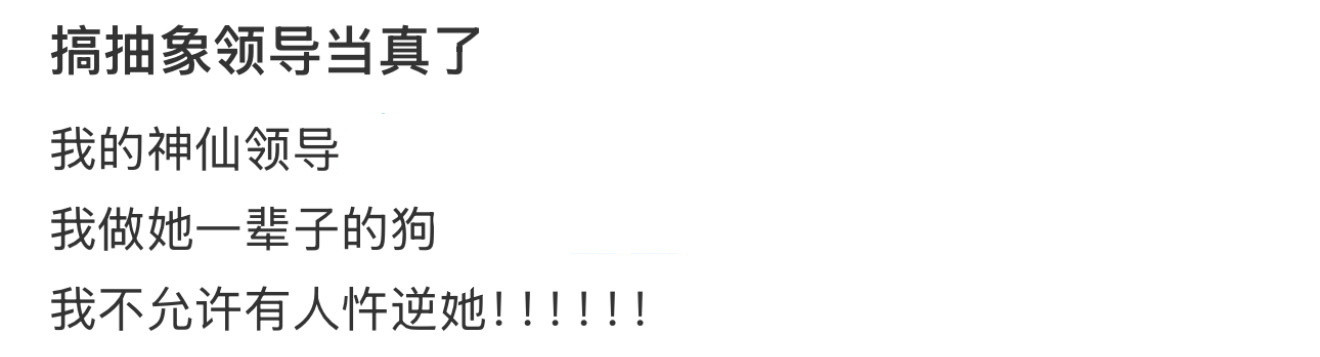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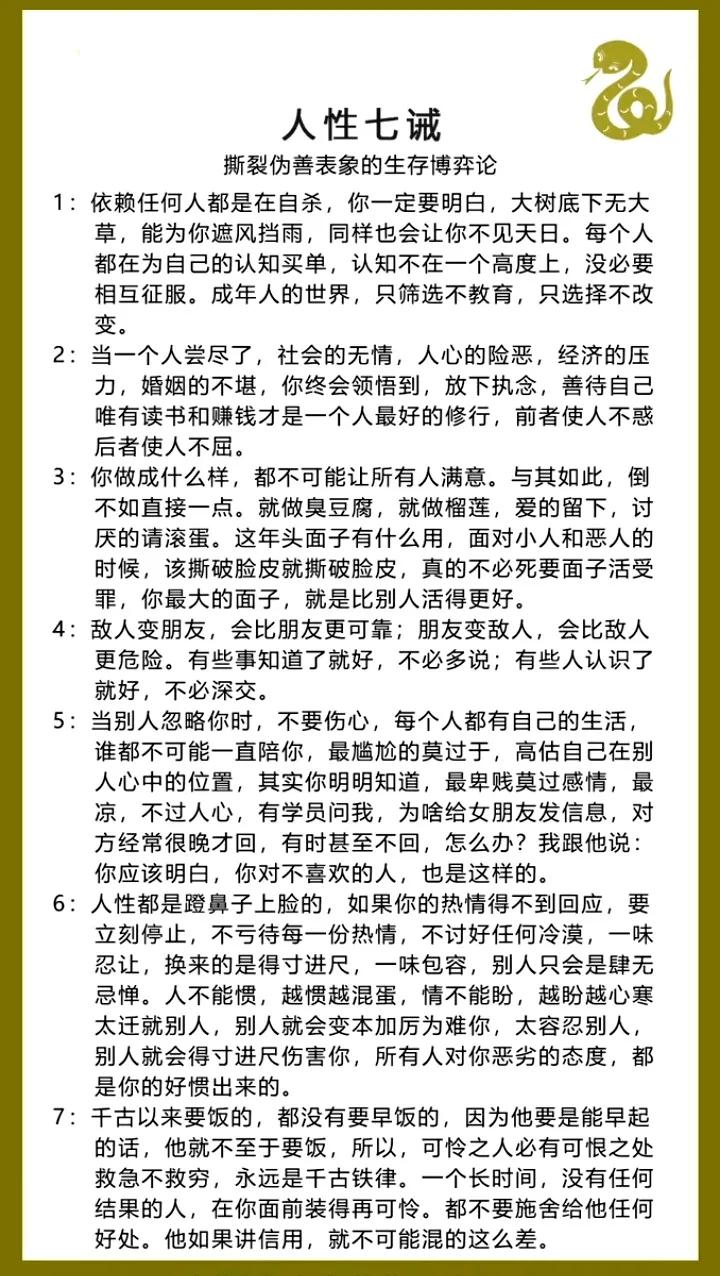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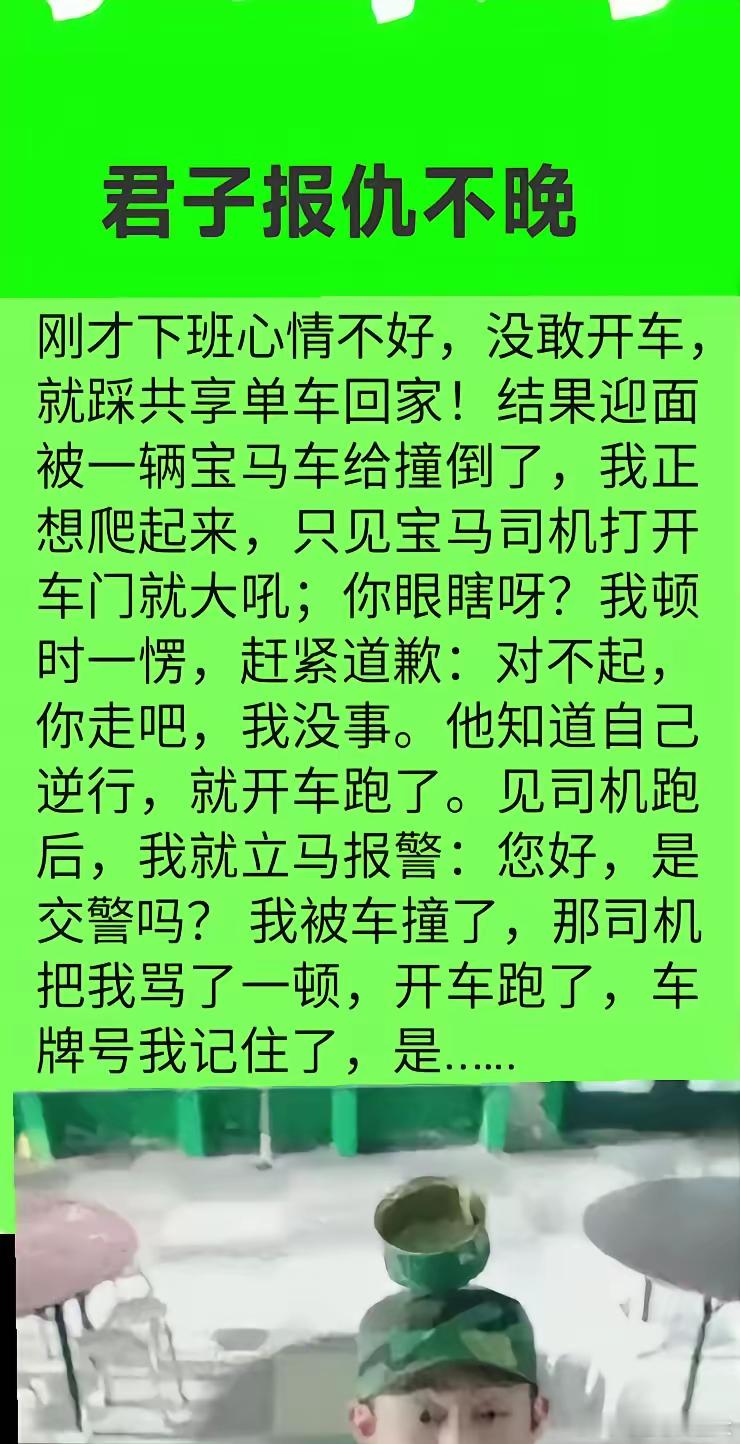

![以前的刊物内容这么愚昧吗[汗]](http://image.uczzd.cn/4112553647127433377.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