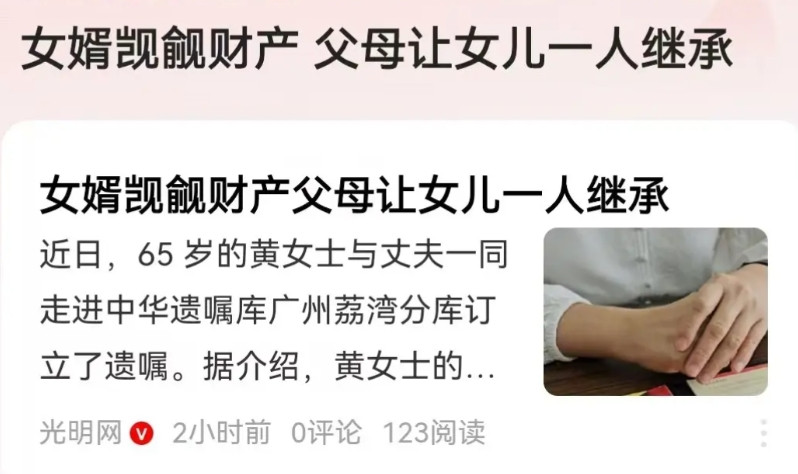吉林,2024年除夕夜,一场朋友聚会演变成生死悲剧。宋某与友人相约观看烟花,却擅自燃放钱某婚礼剩余的A级专业礼花弹。监控显示,宋某未使用发射筒、弯腰近距点火,第二发礼花弹炸裂致其身亡。家属索赔128万,指控代购者楚某及在场友人失责。庭审中,楚某作为婚礼代购是否有过错?宋某冒险操作是否自担风险?各方争论不休。经过审理,法院判决亮了。这场血染除夕夜的惨剧,给违规燃放者敲响警钟——安全红线,跨过即是深渊。
(案例来源:中国法院网)
2024年除夕夜,某居民小区内,一场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意外事故,让五个家庭的团圆时刻蒙上阴影。
案件的源头可追溯至2023年10月。钱某(化名)为筹备儿子的婚礼,委托好友楚某(化名)联系购买烟花爆竹。
楚某通过私人渠道购得包括"大地红""加特林"及礼花弹在内的多种烟花,其中礼花弹属专业燃放类产品。
婚礼当天,部分礼花弹未完全使用,剩余部分被另一好友周某(化名)带回家中存放。正是这些被遗忘的礼花弹,成为四个月后除夕夜悲剧的导火索。
2024年2月9日(除夕)晚,宋某通过微信群发起聚会,邀请赵某、钱某前往周某家中观看烟花。
23时许,宋某驾车将妻子和赵某送至周某家后,又折返接钱某同行。当宋某与钱某返回时,周某与赵某已在庭院内燃放烟花爆竹。
监控录像显示,众人先后燃放"大地红""加特林"等烟花后,宋某主动从周某车库中取出剩余礼花弹。
据在场人员陈述,宋某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将礼花弹置于水泥地面直接点燃,未使用专用发射筒,且未保持安全距离。
第一发礼花弹成功升空后,宋某在点燃第二发时发生意外——礼花弹未正常升空,在近距离爆炸致其头部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宋某家属起诉认为:楚某作为烟花爆竹的实际购买人,未通过合法渠道采购且未确保产品质量;赵某、钱某、周某作为共同燃放者及场地提供者,未尽到安全提醒义务,四人应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128万元。
被告方则提出抗辩:
楚某强调其仅为代购中间人;周某称礼花弹系钱某婚礼剩余物品,自己仅为临时保管;
赵某、钱某主张未参与礼花弹燃放;所有被告均指宋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自担风险。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1、楚某的代购行为是否构成销售者责任?
根据《民法典》第161-162条,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代理人仅需在代理权限内行事。
本案中,楚某接受钱某委托联系购买烟花爆竹,其核心行为是作为“信息中介”促成交易,而非实际参与买卖关系的主体。
从《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19条看,合法销售者需取得经营许可证,但该规定规制的是经营行为,非民事代理行为。
若楚某未收取差价或佣金,其代购行为更符合“无偿帮工”性质。此时,若要求代购者对产品质量负责,相当于将普通民事代理等同于销售行为,突破了法律对“销售者”的界定。
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烟花存在质量问题,更无证据显示楚某知晓产品缺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原告的举证不能直接导致其主张不成立。
故,本案楚某没有过错。
2、赵某、钱某、周某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安全保障义务主体主要为公共场所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组织者。
本案中,周某虽提供自家场地,但聚会属朋友间自发行为,非营利性活动,其身份不同于经营场所的管理者。
监控证据显示三个关键细节:其一,赵某、钱某在宋某燃放礼花弹时身处室内,物理上无法实时干预;其二,周某在车库整理物品,未在场参与燃放;其三,礼花弹系宋某自行从车库取出,未经他人协助。
这些事实排除了“作为义务”(如主动提供危险物品)与“不作为过错”(如未制止危险行为)的成立。
本案明确“风险自担”原则在非组织性活动中的适用边界,强调法律不应苛求普通人预见他人自发实施的危险行为,这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价值。
3、宋某是否属于应自甘风险的情形?
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自甘风险适用于文体活动,但本案通过过失相抵规则(第1173条)实现责任分配,展现了司法裁判的灵活性。
礼花弹属于《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规定的专业燃放类产品(A级),依条例第28条必须由专业人员使用专用器具燃放。
宋某的三大违规行为构成过失递进链:使用非专业燃放方式(未安装发射筒);未保持安全距离(监控显示其弯腰近距离点火);连续燃放时未检查前次燃放结果(第一发升空后未排除哑弹即点燃第二发)。
最终,法院认定宋某应当自甘风险,驳回了其家属的全部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