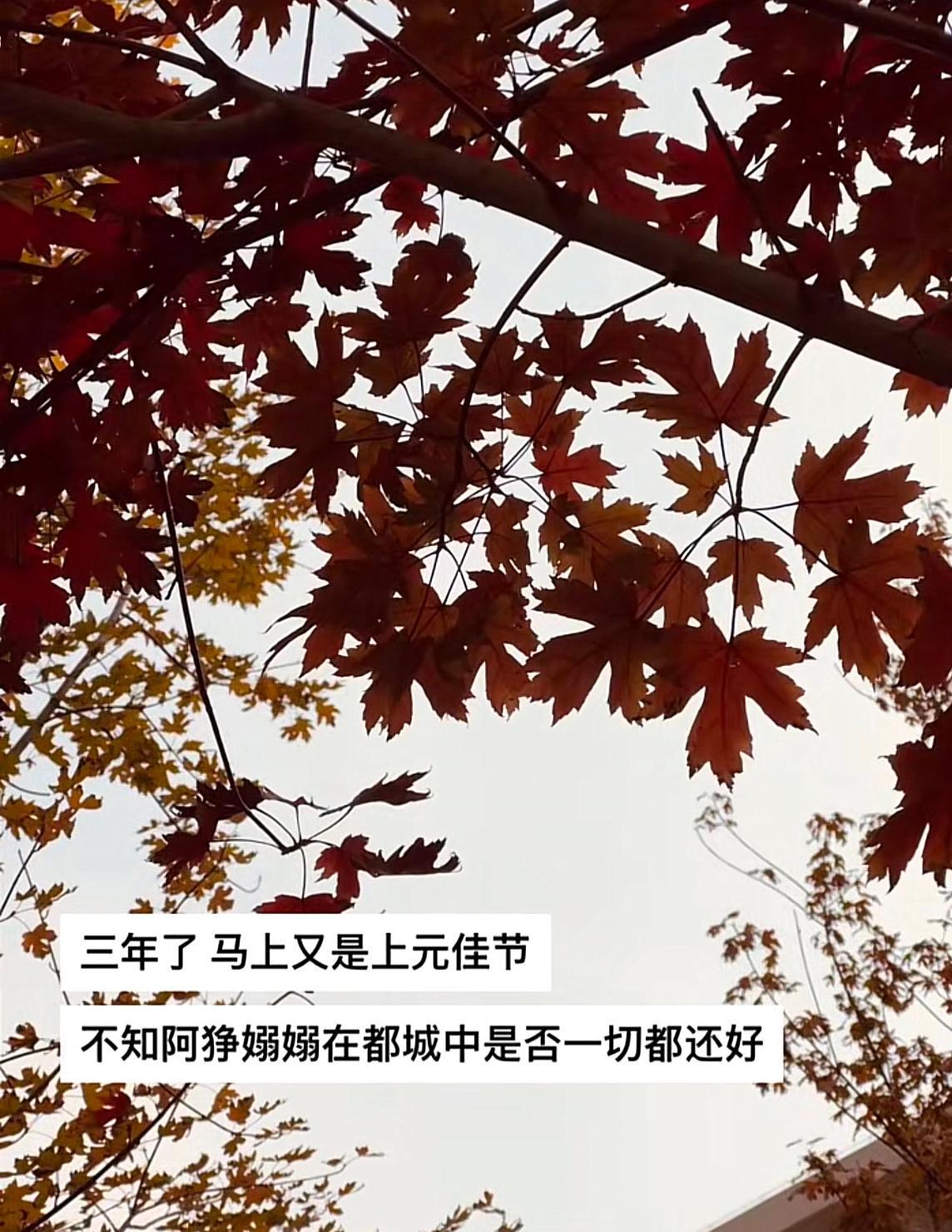南霭自立夏入伏之后,日头也似是掐准时间般每日高高悬挂,暑热难耐。
镇上的坊市也调整了早出和晚结的时间,人们想向老天讨些凉意,于是就试图将时间更拉长了些。
霍懋也长大了些,日日在云居的小院落之中赤着脚丫被阿起带着疯跑,程少商终于在他们二人打落第三个腌渍水菜的瓦罐后忍无可忍,在那日入夜,同霍不疑商量着把霍懋送去镇上的学塾。
霍不疑摇着蒲扇,两个人宽衣而眠,她穿的清凉,他也打着赤膊,头轻轻靠在他怀里,她的手指在他胸口轻轻划着圈。
“学墅难免也太沉闷了些,那些过了益学堂后的稚子送去便可,现下懋儿的年纪也小些,”霍不疑将经过夜息香熏制的蒲扇放下,吻落在了她额头,含混地低头就去寻她的唇,“...再过些日子。”
程少商在他怀中被阵阵清凉也哄得迷糊,唇舌纠缠一番还是抵着他的胸膛推开了他,“...懋儿一会儿又要来敲门喊你帮他打蒲扇。”
霍不疑不应,只是柔柔地把吻一个个地落在她光滑白皙的肩头,像是轻吻着锦缎般珍重。“..屋里落了两重锁,白日我同他说过了。”
程少商被吻得头晕,看着竹制矮桌上的小鱼灯盏里的灯火被映在墙面,伸手也攀上了他的肩,把吻回给她。
快三年了,小团子也早就滚成了能上学塾的大团子,她也不管了。
-
他们的云居院落背靠青山,青山地缓的矮坡处也长着大片的竹林,大暑过后雨露丰沛,竹林应声着抽出生力生长,偶有被大雨击打却也不弯曲,反而随着暴雨和劲风摇曳成了簌簌的声浪。近竹林处也生着一汪水泽,也算是他们云居里避暑的好去处。
若非当值,也无边防烦扰,霍不疑时常带着斗笠和蓑衣,手里提着青竹西线做的鱼竿,一坐便是半个日头。
随身带着的竹编小篓里是他哄着霍懋在雨后泥地里挖出的鳅鱼,混着磨碎的粟揉成小团,散着抛入水中,又大又黑的青鱼最喜食。
阿起难得笑他也有了中年男子不爱归家的烦扰,他却也不反驳,只笑骂让他早日成家。快近日午,日头晒得平稳的水潭也是极热,青鱼不愿冒头,朗日无风,棉麻的衣袍黏在身上也让人不舒爽,他也打算收了杆回家用饭,回头却远瞧着熟悉的人影向他一步步走来。
是嫋嫋。
日头刺了眼,他用手在眉骨处搭了个凉棚望着她一点点走近,一瞬只是笑。
爱人总是不必勉强迎合,心意总是时时相通。程少商提着简易的食盒,离了老远就看见了霍不疑披着斗笠回头瞧着她,她一步步走向他,伸手指了指旁边的凉亭,示意他过去。
今日来药堂来问药的人不多,她顺手把需要挑捡的几位药材理好后就同先生退了值,洗手做了几道小菜便来寻他。
青瓜简略的用盐腌渍过,又混了去火的苦荼,牛肉腌渍过后在石板上用脂油炙烤过,滚好了的粟粥也放了凉,他的口味同她差不多,霍懋也随了他,吃穿用度不挑捡,壮实也好养活。
她摆下几个小碟,笑眯眯地问他,“鱼脍我算是吃不上了?”
“再等等,青鱼总得挑个更大些的。”霍不疑不急,有的是耐心,“也不急,我方才钓上几尾还不及手掌大小,全都放回了。”
苦荼涩得很,用醋中和了些许苦味舌尖上还是生涩,他皱了皱眉头,叨起一筷子直接喂给了她。
程少商咽下了小口的米浆正欲说话,突如其来的一筷子让她反应不及。
“.....”她挑眉看着他,霍不疑只是笑,笑得诚恳又坦然,眼里却总是闪着很狡黠的光。
打算做坏事的时候,他总是如此。
“敢问郎君可要归家用饭?”她从宽袖袍里寻了把扇子,苦荼不好吃,苦得她直皱眉。
“当然,会比当值时回得早。”霍不疑伸手掐了把她的脸蛋,自己眼前娇小的小妇人总喜爱挽起发髻,着青绿罩衫,摇着折扇,自在洒脱得像是富贵人家的风流公子。
她拍开他的手,正了神色,摇着折扇绕到霍不疑那端的阴凉处作风流样式用香帕把他鬓角处的薄汗轻轻擦掉,她轻笑着说出来的话就像是话本子里定好的词,“莫要让本公子等得太久。”
霍不疑放下竹筷偏过头,两个人表情整肃,可眼神相接时,眼中的笑意却掩饰不住,他长臂一揽将她的腰代近自己怀中,好心情地听着她的惊呼化在他耳边。
他凑近她脖颈,闻得到薄荷同白芷混在一起的香味,她时时泡在药堂,身上总多些药香。他埋在她颈畔深吸口气,心也更安定些,他哑着嗓子,“懋儿呢?”
程少商坐在他腿上,把头抵靠在他肩膀,水泽旁也应景的起了阵风,在凉亭的荫蔽处更舒适了些。“哄他午睡了,我从药堂回时,阿起刚巧还在院中没走。”
揽过她肩头时,他粗粝的指腹是喜爱摸着她耳后细嫩软肉的,霍不疑轻声唤她,极温存的在她脖颈留下清清浅浅的吻,”嫋嫋,你什么时候也能软着嗓子同我困觉?”
程少商的脸腾得一下就红了起来,手里随手抓着带来的蒲扇明显摇起来都更快了些,她笑骂着想要挣脱他怀抱,“年岁长起来,你的脸皮也更厚了。”霍不疑也笑着紧紧揽着她,一来一回两人身上起了薄汗,但他仍就这样缠抱着她。
日子时间从指缝间溜走,转眼竟也是三年。
在州县府衙时,他常听着值夜的梆子响了好几声才能将将纵马踏着青石板落夜回来,他也就听过那么一次她软着嗓子轻声给霍懋唱着童谣,格律韵调都不同乐府诗,她的声音总是更清丽些。
午后无风,灼人的日头晒不到凉亭里的他们,倒是更惬意了。霍不疑记性好,他轻声一句句把记忆中的唱词念出来,“日入而息念流水,暮陇山头,月儿明明照九州。“可惜他只记得唱词,却不记得音律,他哄着她,闹得她没办法,于是他惊喜的听见了唱词的下阙,
“此生忆忆,青山雪,共白头。”
程少商顺着唱出了下阙,但旁边的男人却没了声响,她抬起头,看见霍不疑只是望着眼前碧蓝发绿的湖水不作声,“下阙你总听不到,懋儿也听不到,他总是在我唱到上半句就囫囵着睡着了,你也总是晚归,所以也不知。”
此生忆忆,青山雪,共白头。
他们虽然还年轻,可竟也好似半生如流水圭表般规律地经过了,霍不疑也不止一次的同程少商讲,在与她相遇前,他从不笃信天命。他只想着把自己的性命全盘用作仇恨来赌咒,所以即便是知晓前路造化的结局是必死,也无所畏惧。
但直到遇见了她,他自己都不曾知晓的对“共白首”多了许多的贪慕,心头竟也生出惧怕。
“好听,我喜欢最后一句”他把程少商手里的蒲扇接过,凉风吹拂向她,“你再教我唱一遍。”
“那以后都要你唱给我听才行。”
“当然。”
他只是觉得打头的暑热被一句又一句的青山雪消了难耐,心里只剩下仿若被柔荑拂过的清凉欢喜。
程少商故意将调子放得轻缓悠长,手掌被他握进手心,两只手交叠,他也总是习惯在思考时无意识地用拇指一下又一下蹭过她手背,她知晓,他仍旧总是下意识地会陷入某种回忆里,感叹又惶恐地念着她的好,害怕着什么。
在这大千世界之中彼此相逢定有既定因果,她紧紧回握着他的手,也瞧着不知何时蹭过来的阴云遮了日头给湖面盖上阴影后又随时间经过的散开,她太明白他心里是怎样的感觉了。
虽坦然望前路,却也因这样来之不易的平静而失了所愿和幸福。
于是程少商的声音里更多了许多真挚,随着格律轻轻晃着脚上的鞋履,也忽得想起了那年他送她的蛇皮履。
“霍不疑,”程少商又唱完了一遍清了清嗓子,极正式的唤他的名字,
“嗯?”
“我晚上能吃得上鱼脍吗?”
霍不疑笑了,看着架在一旁的长杆,难得的不知怎么辩白,“我学会了,晚上先唱给你听。”
“我要吃鱼脍。”
“..那等明日我下值给你拎回一条。”
“我要吃这碧湖里的,这里的更好...”
“…我给你拎回来的更好…”她努嘴任性的样子实在可爱,他低头直接吻上她的小嘴,不让她有机会再言语。
此生忆忆,青山雪,共白头。
-《清泽》-
上元佳节,同安康 ,共喜乐[小狗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