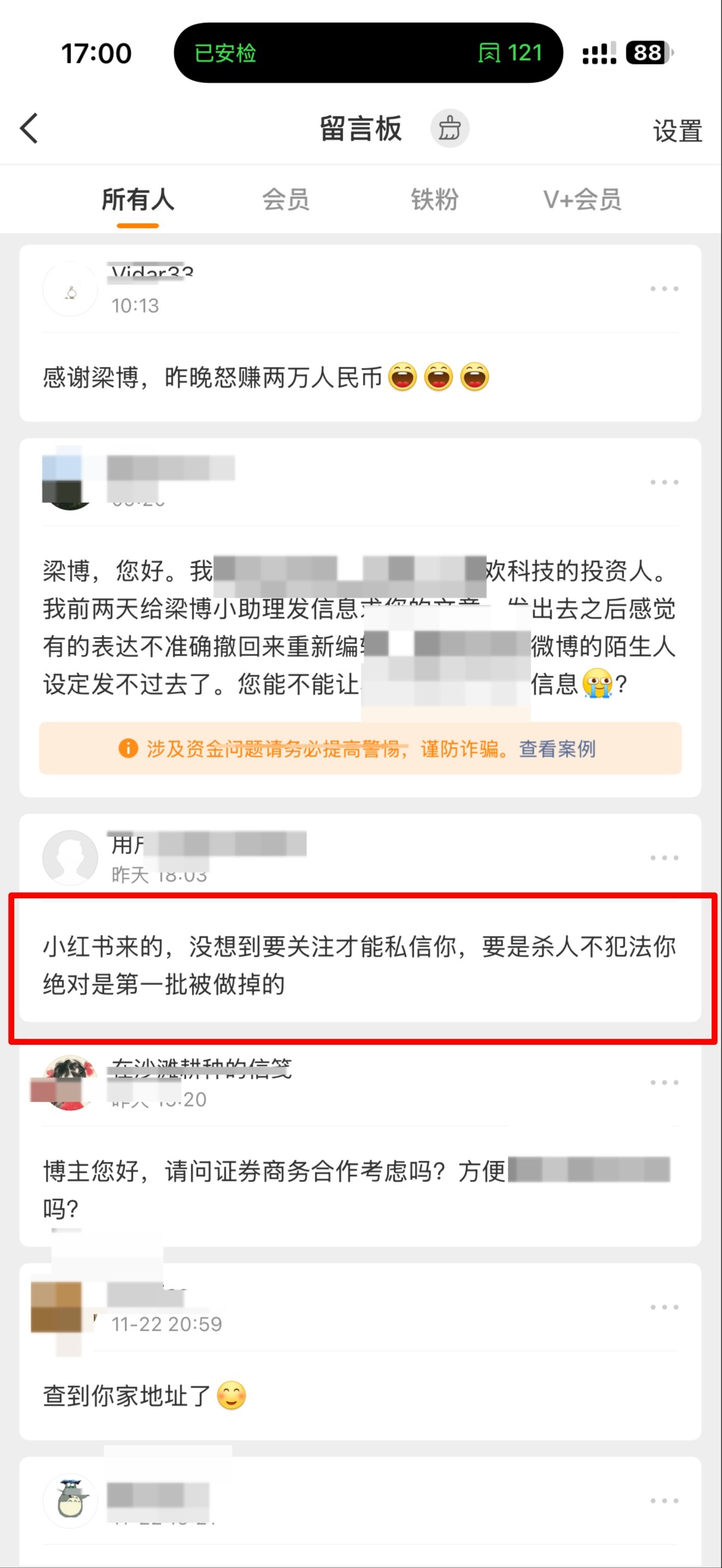1999年腊月二十三,杭州火车站的人多得挤不动。
一个圆脸妇女凑到我旁边,递过一把瓜子:“妹子,回贵州的吧?我也是。”
我往旁边挪了挪,没接。
她也不在意,絮絮叨叨说起自己在外打工的辛苦,说家里孩子想娘想得直哭。
我心里那点防备慢慢松了。
“候车室太闷了,我老乡在外头摆摊,咱去喝口热水?”
她拉着我七拐八拐,走进一条僻静的巷子。
巷子尽头停着一辆旧面包车。
我站住脚,心里发毛:“这不是车站吧?”
她拧开一瓶矿泉水递过来,笑得很和善:“先喝口水,走了这么远。”
水有点甜,还有股怪味。
我想吐出来,眼前却开始发黑。
最后听见的,是她带笑的声音:“别怕,睡一觉,醒来就有新家了。”
01
窗棂外透进灰蒙蒙的光,天还没全亮。
陈满山的脚步声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他在院子里收拾背篓和镰刀,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动。
我躺在床上,手搭在隆起的肚子上,能感觉到里面轻微的动静。
孩子又在踢我了。
这感觉很奇怪,像有一条小鱼在腹中游动,搅动着原本死水一般的日子。
我侧过身,听着外间的声响。
陈满山推门进来,带进一股清晨山间的寒气。
他把一碗冒着热气的玉米粥和两个煮鸡蛋放在床头的小木凳上。
碗沿有个小豁口,是他上次不小心磕的。
他没说话,只是把东西放下,看了我一眼,又很快低下头。
他的目光在我肚子上停留了一瞬,然后转身要走。
我叫住他:“今天还去老鹰崖吗?”
他脚步顿了顿,没回头,只“嗯”了一声。
声音闷闷的,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那地方太险了,上次的伤还没好利索。”
我说这话时,自己都有些意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在意他会不会受伤。
他转过身,黝黑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有些闪烁。
“没事,我小心点。”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那边……有值钱的药材,再不去,季节就过了。”
他说完就出去了,轻轻带上门。
我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慢慢坐起身。
粥还烫着,鸡蛋是家里那只芦花鸡下的,平时婆婆都攒着舍不得吃。
我剥开蛋壳,蛋白细腻光滑。
咬一口,蛋黄在嘴里化开,带着淡淡的腥味。
这味道让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家时母亲也会给我煮鸡蛋。
她说女孩子要多吃点,补身子。
那时候的我,怎么会想到有今天呢?
窗台上晾着几把草药,是陈满山前天采回来的。
有的叶子细长,有的根茎粗壮,我都叫不出名字。
但它们散发出的那种清苦气味,已经弥漫在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
就像陈满山这个人,沉默,苦涩,却无处不在。
吃完早饭,我扶着腰慢慢走到院子里。
山里的早晨雾气很重,远处的山峦隐在乳白色的雾气里,看不真切。
院子角落的柴垛旁,放着陈满山昨天编好的新背篓,用的山上的老藤,看起来很结实。
婆婆从屋后喂完猪回来,看见我站在院子里,皱了皱眉。
“站着做什么?回屋躺着去,别动了胎气。”
她的语气算不上好,但比起我刚来时那非打即骂的样子,已经算温和了。
至少,她现在承认我是她孙子的娘。
我应了一声,却没立刻回屋,而是走到窗台下,看那些晾晒的草药。
有些已经半干了,蜷曲着,颜色由鲜绿转为暗绿。
婆婆跟过来,随手翻检着。
“满山这孩子,最近像疯了一样往山里钻。”
她叹了口气:“我知道他是想多攒点钱,等娃生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没接话,只是看着那些草药。
陈满山攒钱,真的只是为了孩子吗?
我心里有个模糊的念头,却不敢深想。
婆婆拿起一株紫色的草药,凑到眼前仔细看。
“这是紫背天葵,稀罕东西,长在悬崖背阴处,难采得很。”
她转头看我:“满山没跟你说过吧?他爹当年就是采这个摔下山没的。”
我心里一紧。
“那他还……”
“唉,男人嘛,认准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
婆婆把草药放下,拍拍手上的灰:“再说了,现在药贩子给价高,这一把晒干了,能卖十几块钱呢。”
十几块钱,在城里或许不算什么,在这里,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盐油钱。
我忽然想起陈满山手上的那些伤,新伤叠着旧伤,有些已经结痂,有些还红肿着。
他从来不喊疼,就像那些伤不是长在他身上。
中午的时候,太阳出来了,雾气散了些。
我把草药翻了个面,让它们晒得均匀些。
做完这些,我坐在门槛上晒太阳。
肚子越来越大,坐着都感觉吃力。
山风穿过山谷,带来远处树林的沙沙声。
这声音听久了,会让人昏昏欲睡。
就在我快要睡着时,院门被推开了。
陈满山回来了,比平时早很多。
他的背篓里装得满满当当,脸上却带着疲惫。
更让我心惊的是,他左臂的袖子撕开了一道口子,里面渗出血迹。
“你怎么又受伤了?”
我站起身,想过去看看。
他摆摆手:“没事,树枝刮的。”
他把背篓放下,从最上面拿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
“给,路上摘的。”
我接过,打开一看,是几个野山莓,红艳艳的,沾着清晨的露水。
果子不大,但个个饱满,在阳光下像红宝石一样。
“老鹰崖那边有片野莓子,今年结得好。”
他说着,蹲下身开始整理背篓里的药材。
我捏起一颗山莓放进嘴里,酸甜的汁液在口中爆开。
这味道让我鼻子有些发酸。
陈满山总是这样,不会说好听的话,却会用最笨拙的方式表达关心。
一颗野果,一碗热粥,一次深夜的寻找。
这些细微的善意,像水滴一样,慢慢侵蚀着我心中那座由恨意筑成的高墙。
婆婆闻声出来,看到背篓里的药材,眼睛亮了亮。
“哟,这么多!今天收获不小啊。”
她蹲下来帮着整理,嘴里絮絮叨叨:“这根参不错,须子都完整,能卖上好价钱。哎,这灵芝小了点儿,不过品相还行……”
陈满山只是埋头干活,把药材分门别类放好。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对母子。
婆婆的头发已经花白,背也有些驼了。
陈满山才四十出头,看上去却像五十岁的人,常年风吹日晒让他的皮肤粗糙得像树皮。
这个家太穷了,穷到要用三千二百块钱买一个媳妇。
穷到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悬崖采药。
穷到连一颗鸡蛋都要省着吃。
那一刻,我忽然有些理解陈满山了。
理解他的沉默,理解他的拼命,甚至理解他当初为什么要买我。
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就像我,现在不也别无选择地留在这里吗?
命运有时就是这样残酷,把两个不相干的人拴在一起,在绝望的泥潭里互相取暖。
傍晚,陈满山把晒了一天的药材收进屋。
他坐在小板凳上,就着油灯的光,仔细地捆扎。
每一捆都扎得整整齐齐,像对待什么珍贵的东西。
我坐在他对面,缝一件小衣服,用的是婆婆从箱底翻出来的旧棉布。
“满山。”我轻声叫他。
他抬起头,眼里有询问。
“老鹰崖……以后别去了,太危险。”
他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不行,那边的药材值钱。”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这话冲口而出,说完我自己都愣住了。
我居然在关心他的命。
他显然也愣住了,灯光下,他的眼睛亮得有些异常。
“我……我心里有数。”
他低下头,继续捆扎药材,但手上的动作明显慢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说:“娃快生了,得多攒点钱。镇上卫生院的医生说,现在生孩子都兴去医院,安全。”
原来他是为了这个。
我心里五味杂陈。
“在家生不行吗?村里不都这样?”
“不行。”他的声音很坚定:“村里接生婆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万一……我不想你冒险。”
他说这话时没看我,耳根却有些发红。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么长的话,也是第一次明确感受到他的关心。
不是为了孩子,是为了我。
油灯的光晕在他脸上跳跃,勾勒出他硬朗的轮廓。
这个男人,用最沉默的方式,扛起了他能扛起的所有责任。
晚上睡觉前,陈满山照例去了柴房。
那里四面漏风,冬天冷得像冰窖。
我曾让他回屋里睡,他总说不用。
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维持着最后一点尊严,或者说,给我留一点余地。
躺在床上,我听着柴房那边传来的咳嗽声。
一声接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他感冒了,或许是今天在山里着了凉。
我起身,倒了一碗热水,推开柴房的门。
他正蜷在干草堆上,身上盖着那床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被。
看到我,他急忙坐起来,有些无措。
“喝点热水吧。”
我把碗递给他。
他接过去,手有些抖,热水洒出来一点,烫到了他的手背,但他没吭声。
“明天别上山了,在家歇一天。”
我说。
他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着热水,热气蒸腾上来,模糊了他的脸。
“不行,明天镇上有集,得把药材卖了。”
“那晚一天去卖不行吗?”
“药贩子明天在,后天就走了。”
他顿了顿,又说:“这次收的价格高,错过就得等下个月。”
我知道劝不动他,叹了口气。
“那你自己小心点。”
他点点头,把空碗还给我。
我转身要走,他忽然叫住我。
“春梅。”
这是我到这个家以来,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我转过身。
油灯的光很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看到他眼里闪烁的光。
“谢谢你。”
他说。
声音很轻,但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退了出去。
关上门的那一刻,我靠在门上,心里翻江倒海。
谢我什么?
谢我留在这里?
谢我怀了他的孩子?
还是谢我给了他一点微不足道的关心?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和陈满山之间,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改变。
像冰封的河面裂开第一道缝,虽然细微,却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回到屋里,我躺回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手不自觉地抚上肚子,感受着里面小生命的动静。
这个孩子,是我在这绝望境地里唯一的慰藉,也是我永远无法挣脱的羁绊。
我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还在等我回家过年?
还有弟弟,他拿到那个随身听了吗?
这些问题,我都不敢深想。
一想,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疼。
有时候我会做噩梦,梦见自己还在杭州火车站,那个圆脸妇女笑着朝我走来,递给我一瓶水。
我想喊,想跑,却怎么也动不了。
然后就会惊醒,一身冷汗。
陈满山听到动静,会敲敲我的门,轻声问:“怎么了?”
我说做噩梦了。
他就说:“别怕,我在外面。”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我莫名安心。
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山村里,陈满山成了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多么讽刺。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
山里的夜很静,静得能听到虫鸣,听到远处的狗吠,听到风吹过树梢的声音。
我就在这些声音里,慢慢睡去。
梦里,我带着一个孩子,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山路上。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必须往前走。
身后,陈满山的声音远远传来:“春梅,等等我。”
我想回头,却怎么也回不了头。
只能一直走,一直走。
直到天亮。
02
醒来时,天已大亮。
陈满山早就出门了,说是要去镇上卖药材。
婆婆在灶间忙活,锅里熬着粥,咕嘟咕嘟响。
我起身,慢慢挪到院子里。
晨雾已经散了,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院子里的鸡在啄食,那只芦花鸡下了蛋,正在得意地咯咯叫。
婆婆从灶间探出头:“醒了?粥马上好,你先坐着。”
我应了一声,在门槛上坐下。
肚子越来越沉,坐一会儿就腰酸。
婆婆端了粥出来,还有一小碟咸菜。
“满山天没亮就走了,说赶早去,能卖个好价钱。”
她在我旁边坐下,也端了碗粥。
“这孩子,最近跟不要命似的。”
她叹了口气:“我知道他是想多攒点钱,可也不能这么拼啊。上次从老鹰崖回来,手上那么大一道口子,我看着都心疼。”
我没说话,慢慢喝着粥。
粥熬得很稠,米香浓郁。
“春梅啊。”婆婆忽然叫我。
我抬起头。
“我知道你心里苦,一开始恨我们,我都知道。”
她的语气不像平时那样硬邦邦的,反而带着几分疲惫。
“可咱们女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我当年也是爹娘做主嫁过来的,连男人面都没见过。嫁过来才知道,这家穷得叮当响。”
她顿了顿,继续说:“满山他爹死得早,我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难啊。满山是老大,懂事早,小小年纪就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好吃的都让给弟弟,好穿的也紧着弟弟。”
“他弟弟志刚,倒是有出息,读书好,考出去了,在城里安了家。”
说到小儿子,婆婆脸上有光,但也有一丝苦涩。
“可志刚这一出去,就再没回来过。写信也少,更别说寄钱了。满山嘴上不说,心里都明白。他说弟弟在城里也不容易,咱们别去拖累他。”
“就这样,满山把自己耽误了。等想起来该成家了,已经三十九了,哪个姑娘愿意嫁到这山沟沟里来?”
婆婆看着我,眼神复杂:“所以我才……才攒了那三千二百块钱。那是我攒了半辈子的钱,一分一毛攒起来的。我知道对不起你,可我没法子啊。”
她说这些话时,声音有些哽咽。
我听着,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恨吗?
当然恨。
可恨谁呢?
恨婆婆?恨陈满山?还是恨这该死的命运?
我说不清。
“春梅,满山是个好人,就是嘴笨,不会说话。可他心里有数,对你是真心的。”
婆婆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硌得我生疼。
“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对满山也不一样了。这样挺好,好好过日子,等娃生了,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
她拍拍我的手,起身收拾碗筷去了。
我坐在原地,心里翻腾得厉害。
婆婆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那扇紧闭的门。
我开始真正理解这个家,理解陈满山。
理解那种被贫困和命运逼到绝境的无奈。
那天下午,陈满山回来了。
背篓空了,脸上带着难得的轻松。
他把卖药材的钱一张张数给婆婆,都是十块二十块的零钱。
“这次卖得好,药贩子说咱们的药材质量好,给了高价。”
他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婆婆数着钱,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好,好啊。攒着,给娃用。”
陈满山看了我一眼,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
“给,镇上买的。”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几块芝麻糖。
糖块不大,用油纸包着,散发着甜香。
“听说孕妇爱吃甜的。”
他低声说,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我捏起一块放进嘴里,甜味在舌尖化开,一直甜到心里。
“谢谢。”
我说。
他摇摇头,转身去收拾背篓了。
晚上,陈满山照例睡柴房。
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声。
忽然,柴房那边传来剧烈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停不下来。
我坐起身,披上衣服,端着油灯走过去。
推开柴房的门,我看见陈满山蜷在草堆上,咳得脸都红了。
“你怎么了?”
我快步走过去,把油灯放在地上。
他摆摆手,想说话,却又是一阵咳嗽。
我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
“你发烧了!”
“没事……咳咳……睡一觉就好了。”
他说得艰难。
“不行,得吃药。”
我想起他采回来的草药里,有退烧的。
去灶间找了生姜和柴胡,熬了一碗药汤。
端回来时,陈满山已经咳得坐起来了。
我扶着他,把药汤一点点喂给他喝。
他喝得很慢,每喝一口都要喘几口气。
喂完药,我又打来热水,用毛巾给他擦额头和脖子。
他闭着眼睛,任我摆布。
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我这才发现,他其实长得不丑。
眉毛很浓,鼻子挺直,只是常年风吹日晒,皮肤太糙了。
如果没有这些苦难,他应该也是个端正的男人吧。
“春梅。”他忽然开口,声音沙哑。
“嗯?”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
是啊,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
因为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他是我唯一的依靠?
还是因为,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我看到了他坚硬外壳下那颗柔软的心?
我说不清。
“别说话了,好好休息。”
我说。
他却不依不饶:“我知道,一开始你恨我,恨这个家。我也恨我自己,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可我没法子,春梅,我真没法子。”
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此刻脆弱得像孩子。
“我娘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怕她等不到我娶媳妇那天。村里人都笑我,说陈家要绝后了。我……我受不了……”
他捂住脸,肩膀颤抖着。
我从未见过他这样。
在我印象里,陈满山永远是沉默的,坚硬的,像山里的石头。
原来他也会哭,也会疼。
“别说了,都过去了。”
我轻声说。
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过不去,春梅,这事永远过不去。我买了你,这是我一辈子的债。”
我看着他的眼睛,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拼命。
他是在赎罪。
用汗水,用鲜血,用生命去赎罪。
“睡吧。”
我说。
他点点头,躺下了。
我给他掖好被角,端着油灯退出去。
回到屋里,我再也睡不着了。
陈满山的话在我耳边回荡。
一辈子的债。
是啊,我们都被这笔债困住了。
他困在对我的愧疚里,我困在对他的恨和渐渐滋生的感情里。
这笔债,要怎么还?
怎么还得了?
天亮时,陈满山的烧退了。
但他脸色还是很差,咳嗽也没完全好。
婆婆让他今天别上山了,在家休息。
他答应了,却闲不住,拿起斧头去劈柴。
我坐在院子里缝小衣服,看着他一下一下劈柴。
他的动作不如平时利索,显然身体还没恢复。
“满山,歇会儿吧。”
我说。
他摇摇头:“没事,这点活累不着。”
正说着,院门被推开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进来,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脸上堆着笑。
是村长陈福贵。
“满山,劈柴呢?”
陈福贵笑呵呵地说。
陈满山放下斧头:“村长,有事?”
“没啥大事,就是过来看看。”
陈福贵的眼睛在院子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哟,春梅这肚子不小了啊,快生了吧?”
我低下头,没说话。
陈满山走到我身前,挡住了陈福贵的视线。
“还有一个月。”
“好啊,到时候生了,一定要告诉我,我给娃包个红包。”
陈福贵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陈满山一根。
陈满山摆摆手:“不抽,咳嗽。”
“哦,对,听说你昨天去镇上卖药材了?卖得不错吧?”
“还行。”
陈满山的回答很简短。
陈福贵吸了口烟,慢慢说:“满山啊,最近镇上风声紧,听说上面在查买媳妇的事。你们家……可得注意点。”
我心里一惊。
陈满山的脸色也变了变:“村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啥意思,就是提醒你一下。春梅是外来的,没户口,没身份,万一有人查起来,不好办。”
陈福贵吐了口烟圈:“不过你也别太担心,咱们村偏僻,一般没人来。就是……最近村里有人说闲话,说看见春梅老在村口转悠,是不是还想跑啊?”
“没有的事。”陈满山立刻说:“春梅现在安心过日子,不会跑的。”
“那就好,那就好。”
陈福贵把烟头扔地上,用脚踩灭:“我就是提醒一下,让你们注意点。毕竟,买媳妇这事,说出去不好听,对你,对春梅,对娃都不好。”
他说完,拍拍陈满山的肩膀,走了。
院门关上,院子里一片寂静。
我看着陈满山,他的脸色很难看。
“他在威胁我们。”
我说。
陈满山没说话,只是握紧了手里的斧头。
我知道陈福贵的意思。
他是想敲打我们,让我们老实点,别给他惹麻烦。
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村长就是土皇帝。
他想护着你,你就能安稳过日子。
他想整你,你就别想好过。
“春梅。”陈满山忽然叫我。
“嗯?”
“你放心,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
他说得很慢,但每个字都像钉在木头上一样结实。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有坚定,有决心,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狠厉。
这个男人,平时沉默得像块石头,关键时刻,却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我相信你。”
我说。
他点点头,继续劈柴。
斧头落下,木柴应声而裂。
那声音,像是在宣告什么。
下午,陈满山又出门了。
他说要去山上看看有没有新长出来的药材。
我知道,他是想多攒点钱,以防万一。
婆婆在屋里翻箱倒柜,找出了几块旧布,说要给娃做尿布。
我们坐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做针线。
“春梅,刚才村长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婆婆说:“他就是吓唬人,想捞点好处。咱们村买媳妇的又不止咱们一家,他要真查,全村都得乱。”
“那怎么办?”
“没事,回头让满山给他送点东西,堵堵他的嘴。”
婆婆叹了口气:“这世道,没钱没势,就得受人欺负。”
我没说话,心里却想着陈福贵的话。
上面在查买媳妇的事。
这是真的吗?
如果真的查到这里,我能得救吗?
可是得救了又怎样?
我肚子里怀着陈满山的孩子,我能抛下孩子一走了之吗?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缠在我心里。
傍晚,陈满山回来了。
他背篓里只有几把常见的草药,显然今天收获不大。
但他脸上没有沮丧,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表情。
“满山,怎么样?”
婆婆问。
“没事,我都处理好了。”
陈满山说得很含糊,但我和婆婆都明白他的意思。
他肯定是去找陈福贵了,送了些东西,打点好了。
“那就好,那就好。”
婆婆松了口气。
陈满山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春梅,以后尽量少出门,就在家待着。”
“嗯。”
我应了一声。
我知道,他是怕节外生枝。
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小心。
晚上,陈满山没睡柴房,而是睡在了堂屋。
他说柴房漏风,咳嗽没好,怕加重。
但我知道,他是想离我近一点,万一有事,能及时照应。
堂屋和我的房间只隔着一道门板。
我能听到他翻身的声音,咳嗽的声音,还有偶尔的叹息。
这个男人,把所有的压力和担忧都藏在心里,一个人扛着。
我忽然觉得,他比我想象中更累,更苦。
“满山。”
我轻声叫。
“嗯?”
“你睡了吗?”
“没。”
“我有点怕。”
门外沉默了一会儿。
“别怕,有我在。”
简单的五个字,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是啊,有他在。
这个用三千二百块钱买了我,又用生命守护我的男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
夫妻?不像。
仇人?也不是。
也许就像婆婆说的,这就是命。
两个被命运捉弄的人,在绝境中互相取暖,互相依靠。
“春梅。”
“嗯?”
“等娃生了,我带你离开这里。”
他说。
我愣住了。
“离开?去哪?”
“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
他的声音很低,但很坚定:“我知道你不属于这里,你是城里人,读过书,见过世面。这山沟沟困不住你,也不该困住你。”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原来他一直都明白。
明白我的不甘,明白我的痛苦。
“那你呢?你舍得离开这里吗?这是你的家啊。”
“家?”他苦笑一声:“除了我娘,这里没什么可留恋的。再说,我娘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可是……”
“别可是了,我已经想好了。”
他说:“等我再攒点钱,够我们在外面安家了,我们就走。去一个小县城,开个小店,你做裁缝,我卖药材,日子总能过下去。”
他说得那么认真,那么笃定。
仿佛未来真的可以按照他的设想,一步步实现。
“好。”
我说。
除了这个字,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睡吧,很晚了。”
他说。
“嗯,晚安。”
“晚安。”
这一夜,我睡得很踏实。
梦里,我牵着孩子的手,和陈满山一起走在一条开满野花的山路上。
路很长,但阳光很好。
我们一直走,一直走。
走向一个未知的,但充满希望的未来。
03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肚子越来越大,离预产期只剩不到半个月。
陈满山采药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天不亮就走,深夜才回来。
每次回来,他都带着一身的疲惫和或多或少的伤。
手上的口子一道叠着一道,旧的还没好,新的又添上。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劝不住他。
他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要趁着孩子出生前,多攒些钱。
我知道他说的“多攒些钱”不只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他承诺的那个“离开”。
那个承诺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让我对未来的恐惧中,生出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婆婆也开始忙碌起来。
她翻箱倒柜,找出了压箱底的几块新布,说是当年留着给陈满山娶媳妇做被面的,现在正好给娃娃做小被子。
她还托人去镇上买了红糖、鸡蛋,甚至割了一小块肉,说要给我坐月子补身子。
这个曾经对我非打即骂的老太太,如今眼里只有她未出世的孙子,连带着对我也和颜悦色了许多。
有时她会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讲陈满山小时候的事。
说他三岁就会帮她烧火,五岁就跟着爹上山认草药,十岁那年爹没了,他就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
“满山是个苦命的孩子。”婆婆总是这样结尾,眼里泛着泪花。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默默听着。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
也是我被拐卖一周年的日子。
那天早上,陈满山没有上山。
他在家里忙前忙后,把屋子从里到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连墙角的蜘蛛网都扫了,窗户擦了又擦,直到能照见人影。
他还把院子里那堆乱七八糟的柴火重新码放整齐,劈好的柴摞得高高的,像一座小山。
“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勤快。”
婆婆笑着打趣他。
陈满山没说话,只是埋头干活。
中午,他做了一件让全家都震惊的事——他把家里那只下蛋的芦花鸡杀了。
那只鸡是婆婆的宝贝,每天下一个蛋,从不间断。
婆婆平时连碰都不让我们碰,说那是家里的“钱袋子”。
可陈满山说杀就杀了,动作干净利落。
婆婆起初急了,举着扫帚要打他:“你个败家子!那是下蛋的鸡!杀了以后吃什么?”
陈满山挡开扫帚,平静地说:“妈,春梅快生了,得补补身子。一只鸡算什么,以后我挣钱买十只。”
婆婆举着扫帚的手慢慢放下,眼圈红了。
“你呀……跟你爹一个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她转身进了屋,没再阻拦。
陈满山把鸡炖了,放了好多姜,汤熬得浓浓的,满屋子都是香气。
炖好之后,他盛了满满一碗,端到我面前。
汤很烫,他小心地吹凉了,才递给我。
“趁热喝。”
他说。
我接过碗,看着碗里金黄色的鸡汤,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
这一年来,所有的委屈、恐惧、挣扎,似乎都融进了这碗汤里。
“哭什么?”
陈满山有些无措。
“没什么。”
我抹了把眼泪,小口小口地喝着汤。
汤很鲜,鸡肉炖得烂烂的,入口即化。
陈满山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喝汤。
他的眼神很温柔,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春梅。”
他忽然开口。
“嗯?”
“对不起。”
他说。
我愣住了。
“为……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为所有的事。”他低下头,声音闷闷的:“为我买了你,为我妈打了你,为把你困在这里……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捧着碗,汤的热气蒸腾上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都过去了。”
我说。
其实没有过去,那些伤痕还在,那些疼痛还在。
但我不想再提了。
“不,过不去。”陈满山摇头:“我这辈子都欠你的。所以我要补偿你,用我剩下的所有时间补偿你。”
他说得很认真,每个字都像刻在心里一样。
“怎么补偿?”
“带你离开这里,给你和孩子一个像样的家,让你过上好日子。”
他看着我的眼睛:“我发誓。”
我没说话,只是继续喝汤。
汤很暖,一直暖到心里。
下午,陈满山又出去了。
他说要去村口的杂货铺买点东西。
婆婆在屋里缝小被子,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腊月的阳光很珍贵,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驱散了山里的寒气。
我摸着肚子,感受着里面小生命的动静。
孩子很活泼,经常踢我,有时候半夜都会被踢醒。
陈满山听到动静,会敲敲墙,轻声问:“怎么了?”
我说孩子在踢我。
他就会说:“这小子,这么调皮,将来肯定有出息。”
他总说“这小子”,好像笃定是男孩。
其实男孩女孩我都喜欢,只要健康就好。
正想着,陈满山回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神色有些匆忙。
“妈呢?”
他问。
“在屋里。”
他快步走进堂屋,不一会儿又出来了,手里空着。
“你买什么了?”
我问。
“没什么,一点日用品。”
他说得含糊。
我也没追问。
晚上,我们早早吃了饭。
陈满山烧了一大锅热水,让我擦擦身子。
山里条件差,洗澡是件奢侈的事,平时只能用毛巾擦擦。
他特意把炭盆搬到我屋里,把屋子烤得暖暖的。
“小心别着凉。”
他说。
我擦完身子,换上干净衣服,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
陈满山端走脏水,又把炭盆的火拨旺了些。
“你睡吧,我就在外面。”
他说。
“你也早点休息。”
“嗯。”
他退出去,轻轻带上门。
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也许是白天睡多了,也许是心里有事。
窗外传来风声,呜呜的,像有人在哭。
山里的夜总是这样,安静得让人心慌。
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半夜,我被一阵急促的狗吠声惊醒。
村里的狗平时很少这么叫,除非有陌生人进村。
我坐起身,侧耳听着。
狗吠声越来越近,好像就在我们家附近。
接着,我听到了脚步声,很杂乱,不止一个人。
还有说话声,虽然听不清内容,但语气很凶。
我心里一紧,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时,我房间的门被轻轻推开了。
陈满山闪身进来,神色凝重。
“春梅,快起来。”
他说。
“怎么了?”
“别问,快起来穿衣服。”
他的声音很急,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赶紧爬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
陈满山走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小布包,塞进我怀里。
“拿好,千万别丢了。”
“这是什么?”
“钱,和我给你写的东西。”
他说着,又塞给我一把小小的、磨得发亮的旧钥匙。
“这是后院地窖的钥匙,里面我放了干粮和水。如果……如果出什么事,你就躲进去,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
“满山,到底怎么了?”
我抓住他的胳膊,手在发抖。
他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凉,但很用力。
“听着,春梅,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保护好自己和孩子。这些钱够你和孩子生活一段时间。等风声过了,你就离开这里,永远别再回来。”
“你要去哪?”
“我……”他顿了顿,眼神闪烁:“我有点事要处理。你记住,如果天亮了我还没回来,你就按我说的做。”
“不,我要和你在一起。”
我哭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别哭。”他擦掉我的眼泪,动作很轻:“春梅,你是个好女人,是我对不起你。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堂堂正正地娶你,好好对你。”
他说完,在我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
很轻,像羽毛拂过。
然后他转身就走,没有回头。
“满山!”
我追出去,可他已经消失在夜色里。
堂屋里,婆婆也起来了,正站在门口,望着儿子离去的方向。
她的背影佝偻着,在昏暗的油灯下,显得那么苍老,那么无助。
“妈……”
我叫她。
她转过身,脸上满是泪水。
“春梅,听满山的话,快去地窖。”
“可是……”
“没有可是!”婆婆的声音忽然严厉起来:“满山是为了你,为了孩子!你要辜负他的一片心吗?”
我愣住了。
婆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在抖。
“春梅,满山是个好孩子,他一直都知道自己错了。这一年来,他拼了命地挣钱,就是想赎罪,想给你和孩子一条活路。现在……现在机会来了,你得抓住,知道吗?”
“什么机会?”
“别问了,快去吧。”
婆婆推着我往后院走。
我一步三回头,可陈满山已经不见了。
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声音。
地窖在后院的柴垛后面,很隐蔽,平时堆满了杂物。
我打开锁,推开沉重的木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里面不大,但确实如陈满山所说,放着一些干粮和水囊。
还有一床旧棉被,叠得整整齐齐。
我走进去,关上门,世界瞬间安静了。
地窖里一片漆黑,只有门缝里透进一丝微弱的光。
我靠在墙上,怀里紧紧抱着那个布包。
布包鼓鼓囊囊的,里面是陈满山用命换来的钱。
还有他说的“写的东西”。
是什么?
我想打开看看,可手抖得厉害,怎么也解不开那个结。
外面传来了更大的动静。
狗吠声、脚步声、叫骂声混在一起,越来越近。
好像有很多人闯进了我们家院子。
我听到了婆婆的声音,她在和什么人争吵。
接着是东西被砸碎的声音,还有婆婆的哭喊。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想冲出去,可想起陈满山的话,又不敢动。
他让我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
外面的动静渐渐小了,脚步声远去,狗吠声也停了。
四周恢复了寂静,死一般的寂静。
我蜷缩在地窖的角落里,浑身发抖。
怀里那个布包像一块烙铁,烫得我心疼。
天快亮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轻轻推开了地窖的门。
院子里一片狼藉。
水缸被打碎了,水流了一地。
鸡笼被踢翻了,几只鸡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堂屋的门敞开着,里面黑漆漆的,像一张张开的嘴。
我慢慢走出去,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妈?”
我轻声叫。
没有人回答。
我走进堂屋,油灯还亮着,火苗跳动着,映照着空荡荡的房间。
婆婆不见了。
陈满山也不见了。
只有桌子上,放着那个熟悉的旧布包,鼓鼓囊囊的,旁边是一张皱巴巴的草纸。
我走过去,拿起那张纸。
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字,是用血写的,笔画颤抖,最后一笔拉得很长——
“跑!”
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打开布包,里面塞满了钱,都是十块二十块的零钱,皱皱巴巴的,还带着草药的味道。
我数了数,整整四千三百块。
这是陈满山这一年来,用命换来的所有的钱。
他留下了钱,留下了血书,然后消失了。
带着婆婆,消失在这茫茫大山里。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个“跑”字,是什么意思?
让我跑去哪里?
我站在空荡荡的堂屋里,手里攥着那张血书,怀里抱着那包钱。
肚子忽然传来一阵剧痛,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
孩子要出生了。
在这个最不该来的时候。
我扶着桌子,疼得直不起腰。
窗外,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新的一天开始了。
可我的天,塌了。
04
剧烈的腹痛像山洪一样冲垮了我最后一丝力气,我瘫在地窖潮湿的泥土上,手里攥着那张被血浸透的“跑”字。
汗水湿透了头发,眼前一阵阵发黑。
但怀里那个小小的、温热的新生命在动,微弱的哭声提醒我:不能晕过去。
我摸索着找到那块干硬的布,咬在嘴里,用尽全身力气将孩子完全娩出。
地窖里没有光,我只能凭感觉摸索着剪断脐带,用陈满山留下的旧衣服把孩子紧紧裹住。
是个男孩。
我把他贴在胸口,感受那微弱但顽强的心跳,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
就在这时,地窖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狗吠。
一个粗嘎的声音在吼:“仔细搜!每个角落都别放过!”
是周胖子的声音!
那个把我卖到这里的人贩子!
我浑身僵住了,连呼吸都停滞了。
孩子似乎感觉到了危险,停止了哭泣,只是不安地扭动着。
脚步声越来越近,有人在院子里翻找,瓦罐被打碎的声音格外刺耳。
“队长,屋里没人!”
“后院!地窖!”
“这地窖锁着的!”
周胖子骂了一句脏话:“砸开!”
我抱紧孩子,蜷缩到地窖最深的角落,心脏狂跳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完了。
就在我以为木门即将被砸开时,另一个声音响起了。
“等等。”
是村长陈福贵。
“周队长,这地窖我知道,里面全是破烂,锁头早锈死了。那女人大着肚子,怎么可能躲这里?肯定跑了。”
陈福贵的声音带着谄媚的笑。
外面沉默了几秒。
周胖子哼了一声:“跑了?她能跑哪儿去?这大山里,她能飞出天去?”
“可屋里确实没人啊。”
陈福贵说:“要不这样,我让村里人帮着找,这方圆几十里都是山,她一个城里女人,还刚生了孩子,跑不远。”
“刚生了孩子?”
周胖子的声音陡然拔高。
坏了。
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个致命错误——刚才剪脐带时,有一些污物和血迹留在了地窖门口。
如果周胖子仔细查看……
“队长!这里有血迹!”
果然,有人发现了。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砸开!”
周胖子的声音里透着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