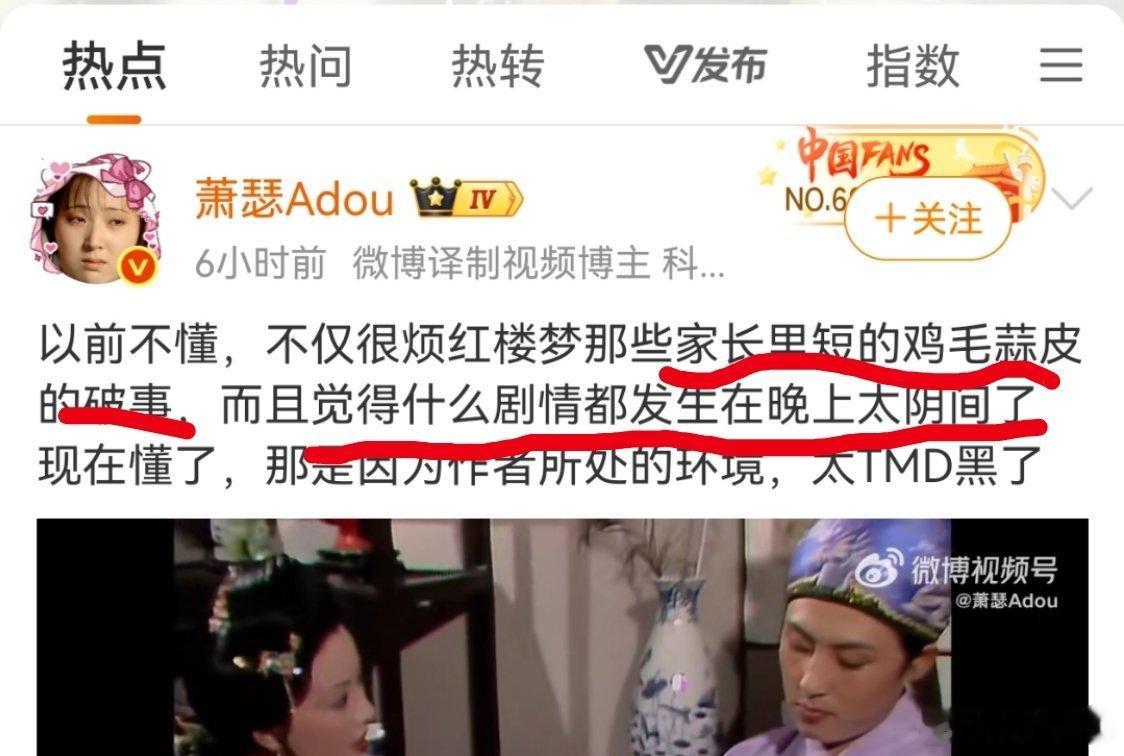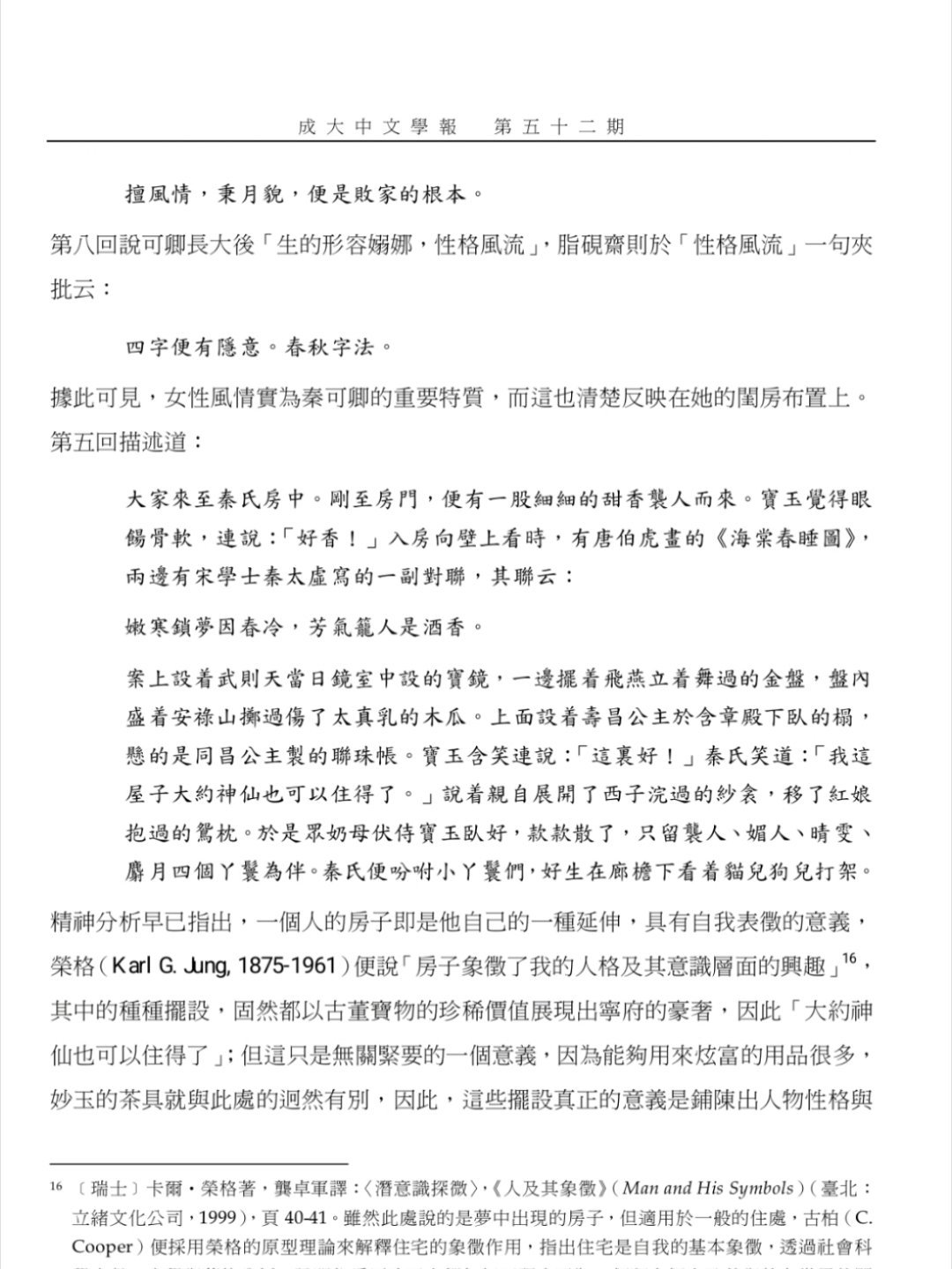曹雪芹在作品对家族、对社会种种弊端、黑暗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是否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情绪或民族意识,流露出对满清政权的不满,曹雪芹是否在作品中表达了其民族文化认同感,这也是《红楼梦》研究中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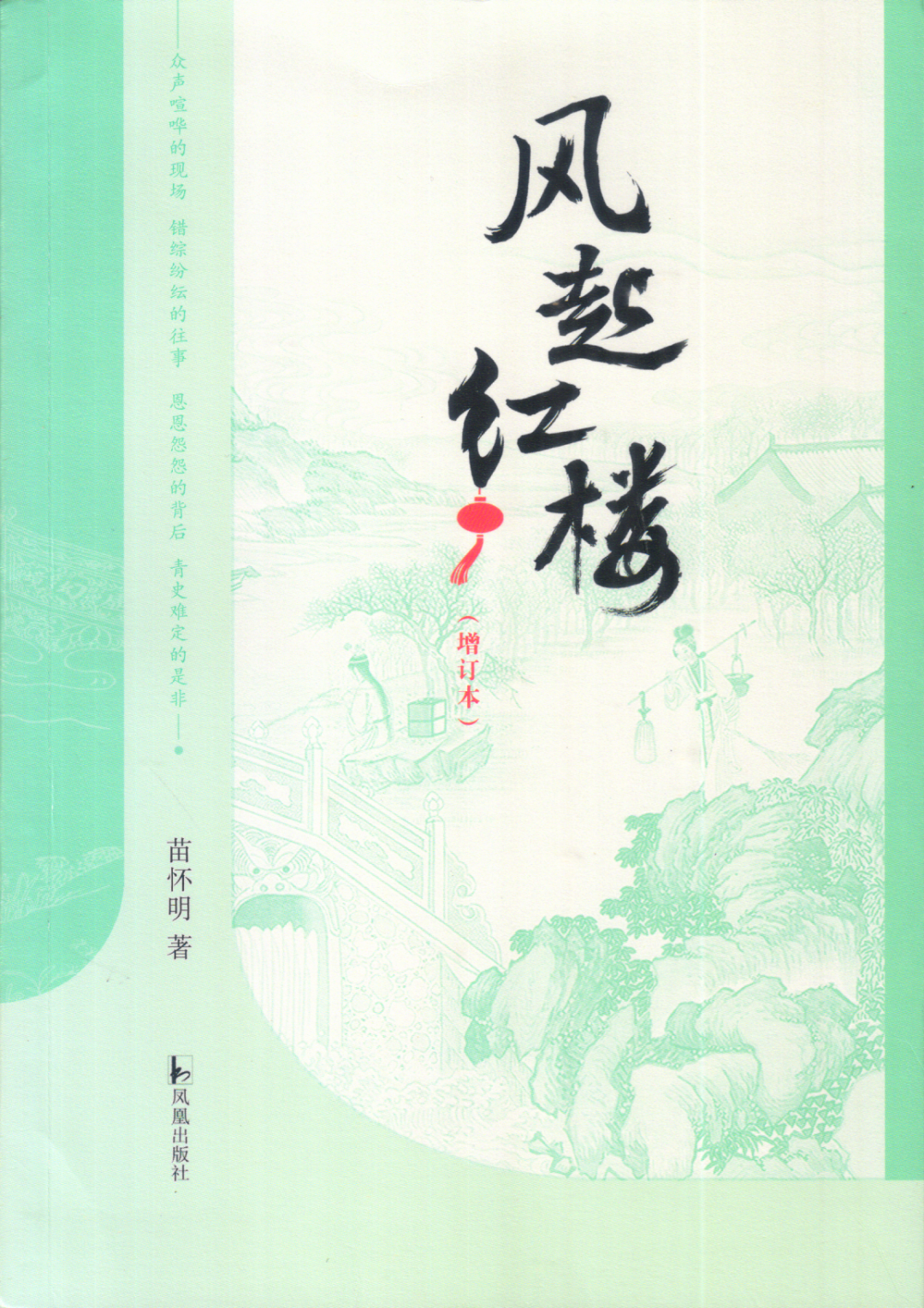
《风起红楼》增订本
作品的民族意识问题历来为读者及研究者所关注,早在清代就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如满人玉麟指出:“《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甚至串成戏出,演作弹词,观者为之感叹唏嘘,声泪俱下,谓此曾经我所在场目击者。其实毫无影响,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齿冷也。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污蔑我满人,可耻可恨。”[1]
显然,他认为《红楼梦》污蔑了满族人,但并没有指出这种污蔑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事实上,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是太多,人们的关注点并不在此。
到了清末民初,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强化民族意识成为革命党人对抗满清政府的一种重要政治宣传手段,在社会上曾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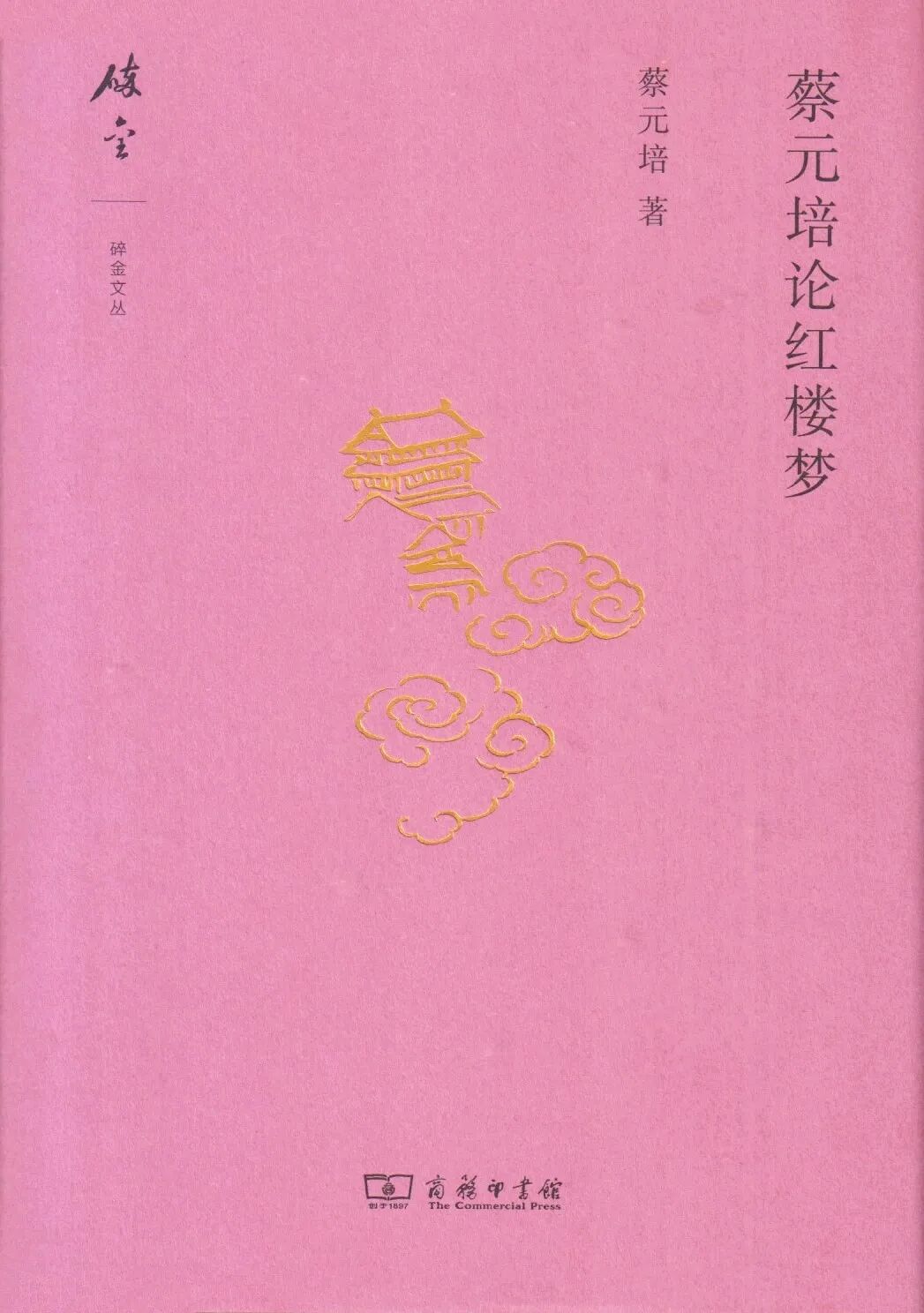
《蔡元培论红楼梦》,苗怀明整理,商务印书馆2025年8月版。
有些人遂从这一角度来解读《红楼梦》,并有意放大、强调其中的民族问题,如蔡元培就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2]。这种观点在当时曾产生较大影响。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过胡适等人的批驳,这一观点的信奉者已不多,不过仍有人在坚持,如三十年代出版的景梅九《石头记真谛》一书,基本延续蔡元培的反清复明观点,并进行新的发挥。
其后,仍不断有人提出这一问题,如潘重规就指出:“作者反抗侵略我们的异族,仇视压迫我们的异族;因此对于异族攻击呵责,无所不至。它大声斥责伪朝秽德,极其不堪。……我读过此书后,我耳中仿佛听见当时民族志士的呼号,我眼中仿佛看见当时民族志士的血泪。”[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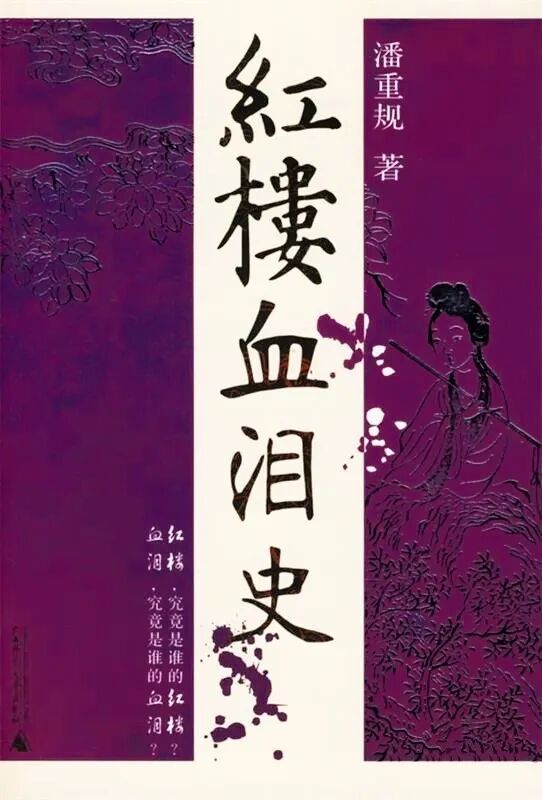
《红楼血泪史》
显然,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鲜明民族倾向的小说。直到当下,仍有人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相关论著及论文不时可以看到。
遗憾的是,《红楼梦》的民族意识问题长期以来主要是索隐式研究者所关注的话题,甚至成为判别索隐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学界对此问题则关注不多,甚少正面的探讨。
由于索隐式研究重点在作品真假的揭示上,并没有真正从思想文化角度探讨这一话题,在观念、方法上存在诸多致命缺陷,大多采用谐音、拆字等方式进行研究,而不是真正从文本出发,因而并未取得多少进展。
《红楼梦》中的民族意识能否构成一个话题,是否有深入探讨的价值,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
一是要看相关人物、事件的具体描写及所流露的倾向,看其在作品中是否构成了民族情绪或民族意识这样一个话题;二是要结合作者的家族背景和生平经历来进行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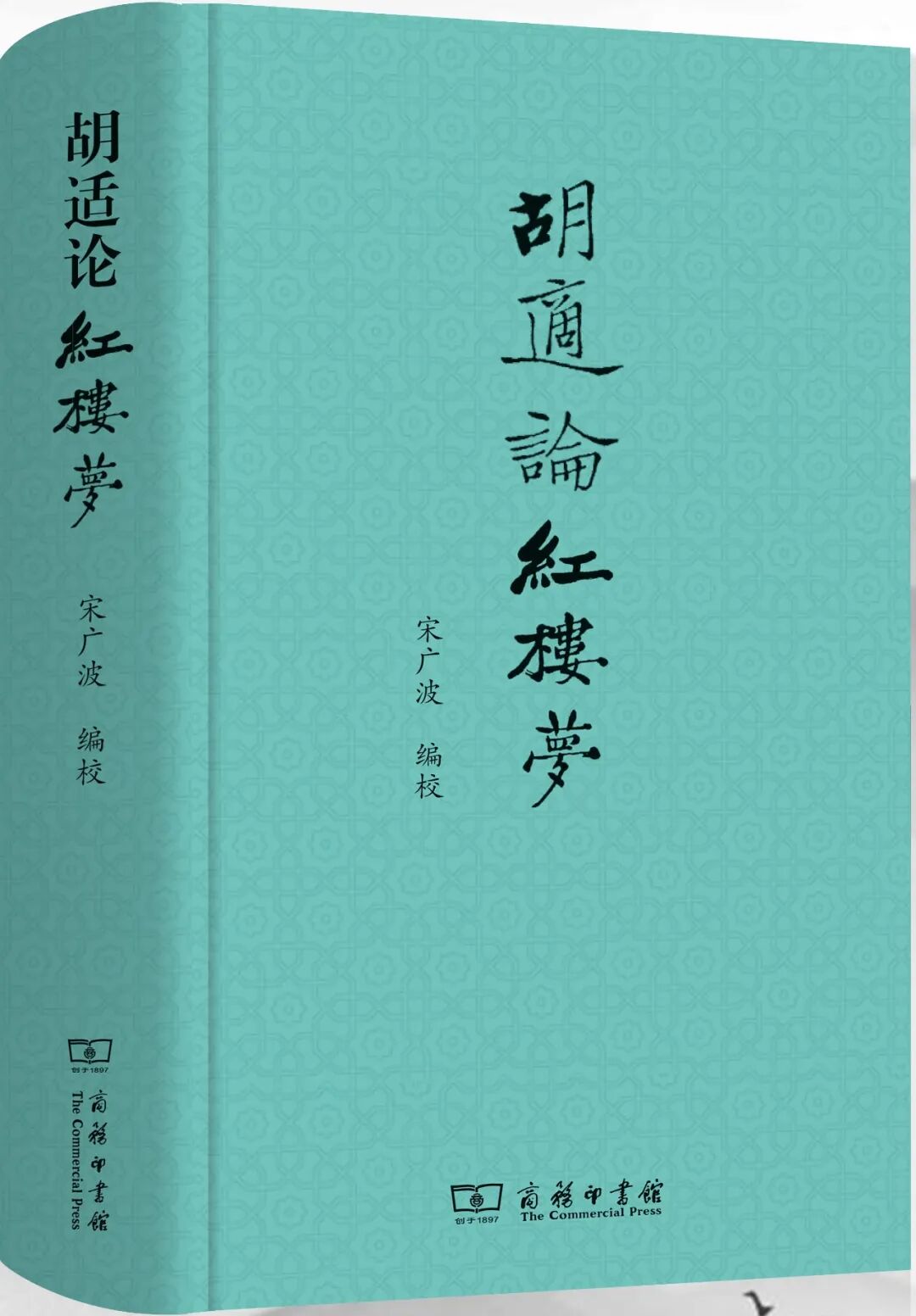
《胡适论红楼梦》,宋广波编校,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版。
从相关描写来看,作品中有如下几处描写涉及到民族问题:
脂本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曾有一句这样的描写:“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
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部分,贾宝玉因芳官的男性装扮而为其起名叫“耶律雄奴”,并由此大发议论:“‘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第七十八回中所写的姽婳将军林四娘,她实际上是死于清兵之手,并非“‘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所害[4]。
自然,在今天看来,说这些地方涉及民族问题似乎有些小题大做,过于敏感。但在文网森严、动辄得咎的乾隆时期,这些词语及人物都是相当敏感的、犯忌的,很容易引起注意,招惹祸端。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
这会不会是曹雪芹的无意之举呢?从情理上恐怕难以说通,作者曹雪芹的身份具有特殊性,他对本朝残酷、严苛的文字狱不会陌生。因此,在创作时其态度是很谨慎的,强调“毫无干涉时世”。
这说明他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有意进行回避。在写到这些地方时,他是不会不留意的。比如后来的高鹗、程伟元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将“大明角灯”中的“大明”二字删去,不仅“耶律雄奴”这一段议论文字,连芳官、湘云、葵官打扮这段情节也都全部删去。
让人困惑的是,既然要避开森严的文网,为什么又要使用这些敏感的字眼呢?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意?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作者这样做,应该是有其用意的,他是不是想通过不经意之笔、以打擦边球的方式较为隐蔽地表达一点自己的民族意识呢?这种可能性不能说一点也没有。
众所周知,曹雪芹的家世及经历比较特殊,其祖先原为汉人,后入八旗,成为满人。其父祖们在担任江宁织造时,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尊崇显贵,风光无限。对主子他们自然也是忠心耿耿,不会产生什么民族意识,比如曹玺临死前,“遗诫惟训诸子图报国恩,毫不及私”[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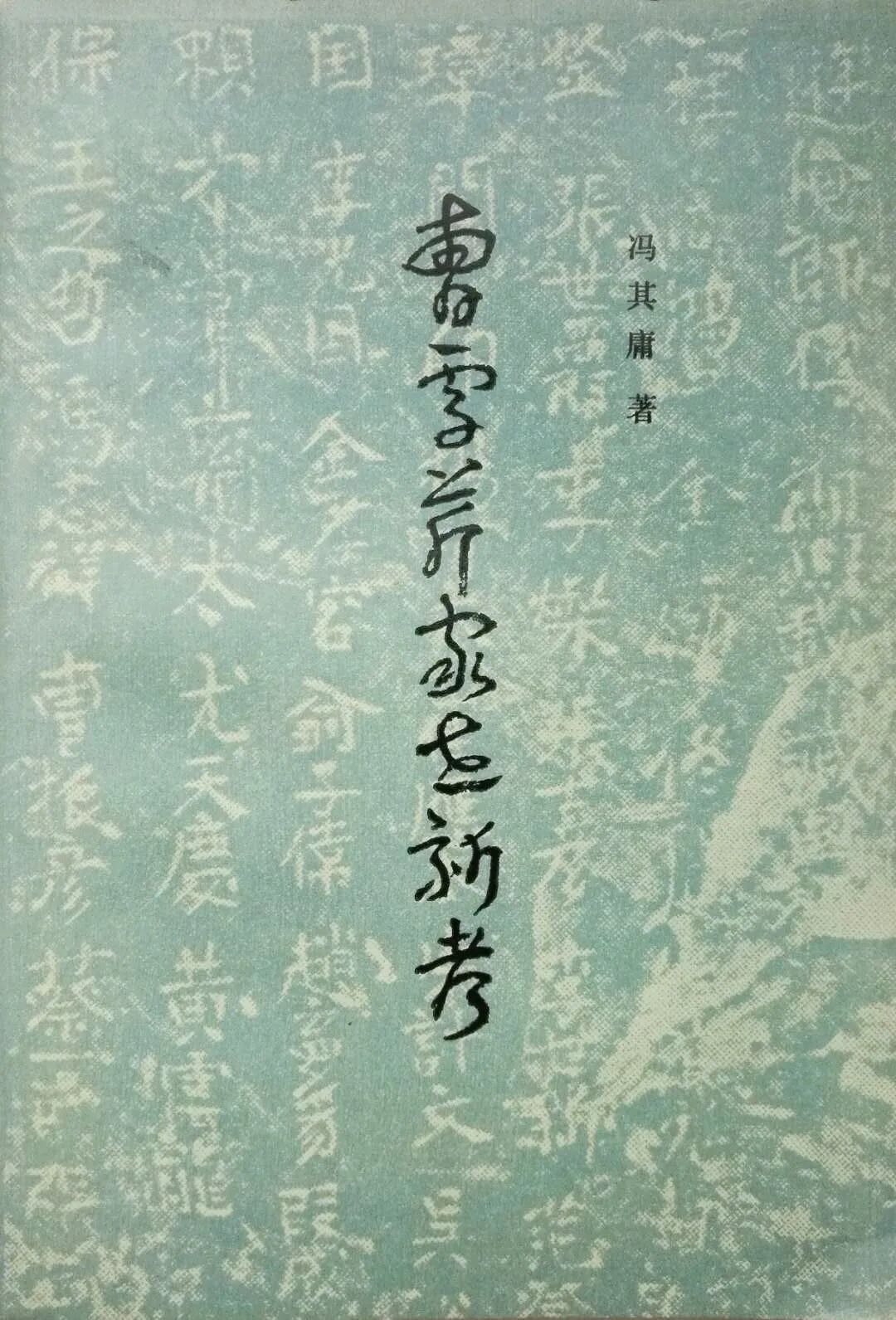
《曹雪芹家世新考》
曹玺没有这一想法,他的子孙如曹寅、曹颙、曹頫等也都受到康熙的特别恩遇,同样不会产生这种想法,这是由他们自身的境遇所决定的。
但是,当曹家经历一番磨难,遭受重创,走向破败之后,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了。对家族苦难的承受者曹雪芹来说,由于境遇各异,他对社会乃至朝廷的看法和态度肯定与其父祖们不同,在其对统治者不满与愤懑的情绪中会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识呢?
《红楼梦》中虽然也写到不少满人的风俗、服饰,但其文化底色却是汉族的,他所接受的也主要是汉族文化。在进行痛苦的反思时,曹雪芹会不会将家族悲剧的根源上溯到民族问题,后悔其祖先当初的选择呢?毕竟自己是“魏武之子孙”,归降满人后换来的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眼云,到头来终究是一场噩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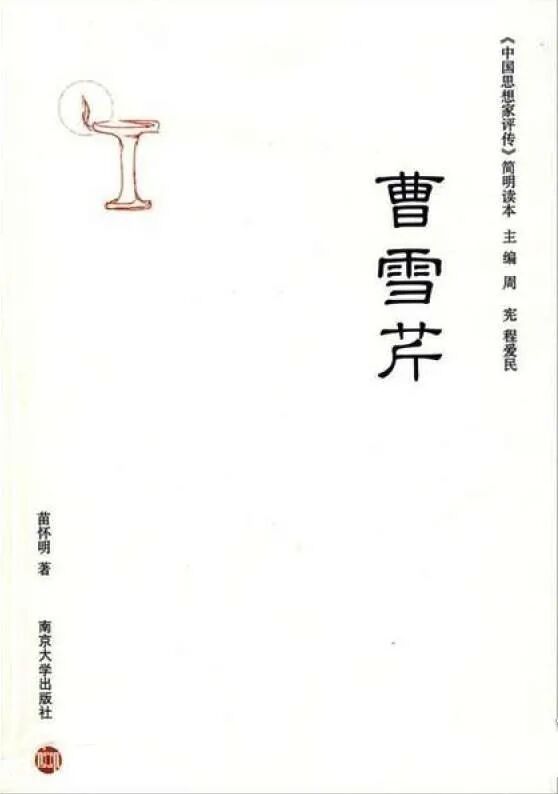
《曹雪芹》
余英时先生认为“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渐发展出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在我看来,是很顺理成章的心理过程”[6]。笔者大体赞同这一看法。
再者,从曹雪芹身边的朋友来看,无论是敦诚、敦敏,还是张宜泉,都是当时社会上的不得志者。他们和曹雪芹一样,对社会有种种不满,满腹牢骚,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文中看出来,尤其是张宜泉的诗歌更是大胆直露。他们的思想无疑会感染并影响着曹雪芹,因此其民族情绪或意识的产生也不算让人感到太意外的事情。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曹雪芹只是在作品中流露出一些迹象,表明他有民族意识的潜在思想倾向,但其表露则是相当克制和含蓄的,最多只是一种情绪的流露和表达而已,还远谈不上激烈或激进,比如彻底否定满清政权,反清复明之类,其程度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概括的:“说《红楼梦》中偶有讽刺满清的痕迹,却并不等于回到‘索隐’的‘反清复明’理论。‘反清’或‘刺清’在《红楼梦》中只是作为偶然的插曲而存在,它决不是《红楼梦》的主题曲。”[7]

台湾联经版《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这种把握还是比较符合作者及作品实际的,但不能由此作无限的引申发挥,要客观、审慎地看待这一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从作品的实际描写来看,这并不是《红楼梦》的核心话题。
至于当下网上流行的悼明之说,不过是一种根据汉字音、形、义随心所欲搭接的文字游戏,仅具玩梗价值,说是索隐,但还没达到传统的索隐式研究水准,没有学术含量。在一些流量博主的鼓动下,不少年轻人带着极端思想和情绪走火入魔,所谓悼明梗已经沦为一场集体反智行为,形成一股网络暴力,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这是需要引起警惕和防范的。
注释:
[1] 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4,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366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2]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7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3] 潘重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载其《红楼血泪史》第4-5、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林四娘故事,各类笔记多有记载,如《聊斋志异》即从感伤故国的角度进行描写。
[5] 康熙二十三年《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
[6] 余英时《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载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57-15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7] 余英时《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载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6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