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时,大人物们英明神武的形象,总让让身为平凡人的你我自惭形秽。然而,揭开历史的幕布,我们也总能发现,大人物们也有普通人的荒诞、迷茫和局限。他们和我们一样在“时代的浪潮中挣扎”,充满反差、滑稽与投机。也是在此时,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完美历史形象”其实并不存在。这一点,在张勋复辟的人物群像里面更是显露无疑。
1917年7月1日,张勋率辫子军突袭紫禁城,支持12岁的溥仪重新登基,改年号为“宣统九年”,宣告“清朝回归”,张勋自封“忠勇亲王”。
复辟令下,北京商家被勒令悬挂龙旗。但民国六年,龙旗早已绝迹。商家只好连夜用黄布画龙,因不熟悉龙纹,有的画成“四爪蛇”,有的龙眼画反,被市民戏称为“纸糊龙旗”。许多清朝旧臣家中尚存朝服,但年轻官员无此物。有人租戏服充数,导致朝堂上出现“蟒袍配马褂”“顶戴歪斜”的滑稽场面。更有甚者,因朝珠丢失,用念珠代替,被御史弹劾“亵渎圣朝”。
而张勋的倒行逆施,也很快就遭到国内外的声讨。各国公使馆拒绝承认复辟,段祺瑞在天津组织“讨逆军”。7月12日,段祺瑞率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军迅速溃散,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退位。
然而,这场仅仅12天的复辟大戏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清朝的遗老遗少,还是民国政府的地方实力派,大人物在复辟风潮中的反差,无不充满滑稽与投机,让人啼笑皆非。

张勋:逆时代的复辟“小丑”
作为复辟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和执行者,张勋曾公开宣称 “非复辟不能救中国”,也因此,他在民国成立后仍坚持留辫(其部众称 “辫子军”),表面以 “恢复大清” 为己任,实则是想借复辟攫取更高权力。当太保世续劝他剪辫时,他竟在溥仪面前辩称:"辫子能防奸宄之徒混入",并得意于街头突然涌现的"假辫子民众",认为这是"民心所向"。
1917 年,张勋以 “调解府院之争” 为名,率 5000 辫子军入京,未经任何政治协商、未考虑军事部署,便仓促宣布溥仪复位,并颁布 “谕旨” 恢复宣统年号、废除民国法令。整个复辟过程,他既未争取到北洋军阀的普遍支持,也未安抚民众情绪,甚至连官员任命都混乱不堪。他让前清遗老仓促上任,有人穿不上朝服就用戏服代替,有人连 “谢恩折” 都不会写,场面滑稽。
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哗然,段祺瑞组织 “讨逆军” 进攻北京。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仅 12 天便全线溃败。他本人从清宫逃入荷兰使馆避难,复辟闹剧草草收场。

康有为:“本朝从未有无须宰相”
康有为曾是戊戌变法的核心推动者,高举 “君主立宪” 旗帜,主张学习西方、变革制度,是清末 “进步文人” 的代表。然而,在张勋复辟中,康有为的行为堪称 “颠覆认知”。
先是主动联络张勋,为复辟起草《复辟宣言》,将民国称为 “乱世”,宣称 “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完全否定了自己早年倡导的变革理念。而当复辟成功后,康有为便渴望担任 “内阁大学士”。不过,因为他在戊戌变法后剪发易服,复辟时辫子仅长六七寸,被讥为“蒲草辫”。从而遭到瑾太妃否决:“本朝从未有无须宰相”。康有为为此急购生须水涂抹,甚至“揽镜自照如农夫望禾苗”,然最终未能如愿,仅被任命为 “弼德院副院长”,气得他私下抱怨 “张勋是个武夫,不懂政治”。不过,康有为仍然身穿清朝朝服,头戴红顶花翎,大摇大摆出入紫禁城,俨然“帝师”姿态。
从 “维新先锋” 到 “复辟急先锋” 的转变,彻底击碎了时人对他 “文人风骨” 的最后期待,鲁迅曾评价他 “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拉,拉还是拉,然而他拉了一通,连车带人掉到沟里去了”。

前清遗老的滑稽幻象
刘廷琛:复辟的“口号党”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北大校长)的刘廷琛,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政治人物、书法家及教育实践者。其首创分科教学体系,奠定近代高等教育基础。
作为复辟核心策划者,刘廷琛在御前会议上力主恢复纲常名教,甚至亲自在复辟诏书中加入“以纲常名教为宪法之精神”等语句,被帝师陈宝琛赞为“半部《论语》治天下”。
复辟时,刘廷琛作为内阁成员积极参与强制推行三跪九叩礼,其“辫子不剪”的言论与张勋的“头可断,辫不可剪”形成呼应。然而,复辟仅12天即失败,宣称“吾既忠于故君,当与同尽”的刘廷琛迅速剪辫并致信段祺瑞表忠心,与复辟期间言论形成鲜明反差。《顺天时报》的批评其“口号复辟,投机保命”。
沈曾植:遗老中的“学术小丑”沈曾植,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被誉为“中国大儒”。31岁中进士,受光绪帝师翁同龢赏识,历任刑部主事、安徽布政使等职,精研律法与舆地之学。早期支持维新变法,失败后转向文化改革,提出“务财劝农,通商惠工”等纲领。
这位精通经史的遗老在复辟期间,竟用《易经》占卜论证“复辟天意”,将唐肃宗灵武劝进的历史事件与复辟类比,宣称“乾卦九五,飞龙在天,正应今日”。复辟失败后,他连夜烧毁手稿,称“天机不可泄露”。其牵强附会的“学术论证”被《大公报》讽刺为“用《易经》给复辟开光”。
胡嗣瑗:复辟的“文书戏子”胡嗣瑗,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北洋法政学堂总办等职。民国初年因文名受冯国璋赏识,任直隶督军公署秘书长。作为复辟期间的“内阁阁员”,他坚持用文言文起草诏书,甚至要求恢复“跪呈”奏折制度。某次因写错一个“朕”字,竟当众自扇耳光,高呼“罪该万死”。其迂腐的仪式感被时人比作“活着的木偶戏”。复辟失败后,胡嗣瑗隐居杭州。1922年起追随溥仪,成为其核心幕僚,负责天津“行在办事处”事务,被溥仪称为“胡大军机”。1932年随溥仪赴东北,任伪满洲国执政府秘书长,后因日方不满调任参议。
郭曾炘:复辟的“哭丧专业户”郭曾炘,光绪六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右侍郎等职,并担任实录馆副总裁,主持编修《德宗本纪》。
在张勋复辟期间,郭曾炘作为遗老群体中的活跃分子,每日前往溥仪处痛哭流涕,甚至因情绪过于激动而晕厥。复辟失败后,他立刻停止表演,并写信给段祺瑞称“痛改前非”。《京报》讥讽其“眼泪比复辟的寿命还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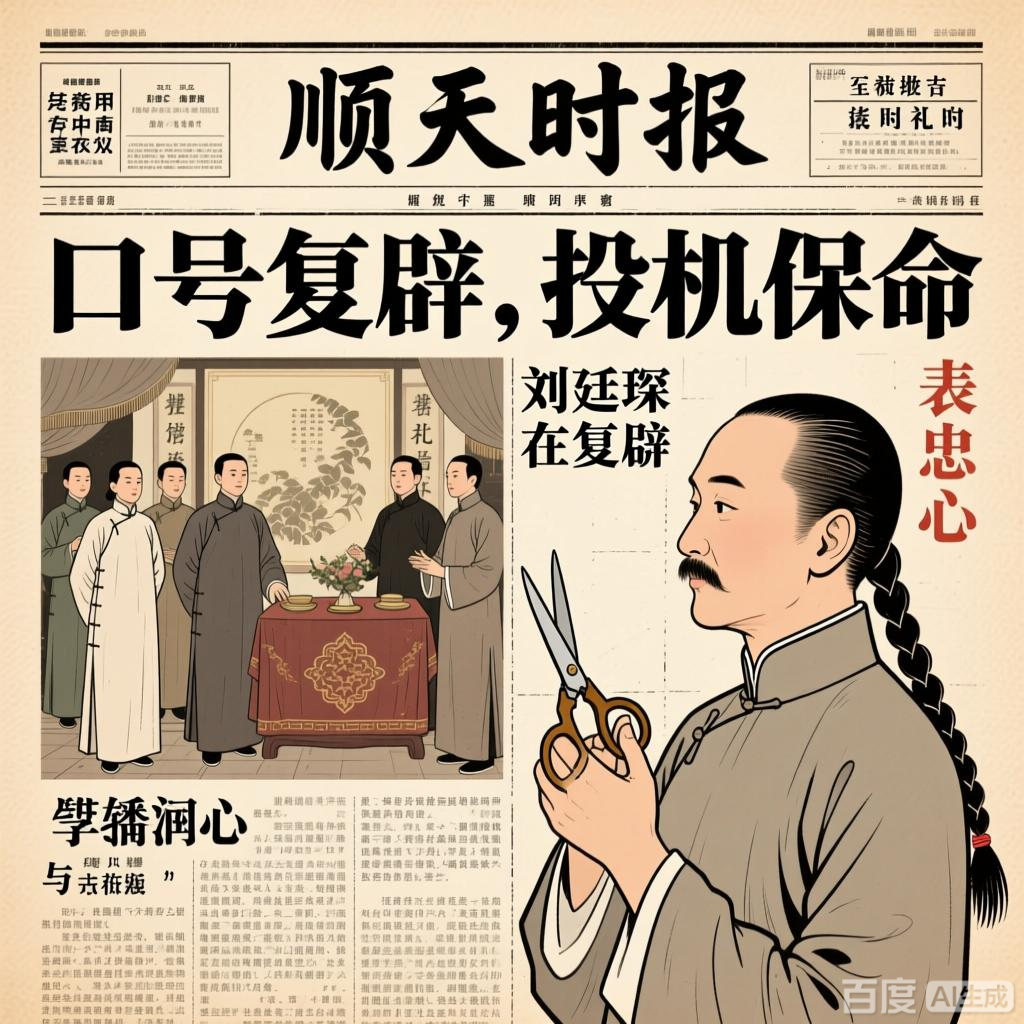
北洋军中的变脸大师们
张镇芳:投机者的“变脸大师”张镇芳,清末民初重要政治人物,与袁世凯有姻亲关系(其姐为袁世凯兄嫂),其子张伯驹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作为张勋的盟友,张镇芳复辟前高喊“誓死效忠清室”,拿出自己的私产资助辫子军,声称 “愿为大清复国立功”。因此,张镇芳被任命为度支部尚书,积极筹款并支持复辟。荒唐的是,他试图将民国的财政收入纳入 “复辟政权”,结果因银行拒绝配合、官员抵制,连军费都无法筹集,导致辫子军军饷短缺,士兵士气低落。
失败后,张镇芳第一时间向段祺瑞告密,称“张勋擅自行动,与我无关”。其反复无常的嘴脸被《申报》称为“川剧变脸”。
冯国璋:表面 “观望”,实则投机冯国璋是北洋直系首领,复辟初期曾秘密发电报 “祝贺” 溥仪复位,试图借此试探局势,甚至暗中与张勋联络,希望在复辟政权中分得一杯羹。但当他看到全国反对复辟的浪潮高涨、段祺瑞 “讨逆军” 势不可挡时,立刻转变立场,通电谴责张勋 “背叛民国”,并出兵协助 “讨逆”。
其后,由于张勋死党万绳栻掌握冯国璋支持复辟的“黄绫子”证据,冯国璋不得不以20万现洋买回销毁,此事成为北洋系政治投机的经典案例。
王士珍 :“北洋龙”的“妥协与沉默”王士珍与段祺瑞、冯国璋并称为 “北洋三杰”,因性格沉稳、善于调和矛盾,被视为北洋系的 “老好人”。但在复辟事件中,他的 “沉默” 与 “妥协”,彻底打破了 “北洋元老” 的形象。张勋入京后,以 “北洋兄弟” 的名义拉拢王士珍,希望他出任 “内阁陆军大臣”。王士珍虽不认同复辟,但因不愿得罪张勋,也不愿公开反对,竟选择 “默认”,甚至一度协助张勋维持北京秩序。
当段祺瑞组织 “讨逆军” 时,派人劝说王士珍倒戈,他仍犹豫不决,直到看到辫子军节节败退,才最终通电 “反对复辟”,并出任 “京师治安会会长”,协助段祺瑞稳定北京局势。他的 “骑墙” 态度,不仅让北洋系内部对他失望,更被时人讽刺为 “老滑头”。作为北洋元老,他本应坚守共和底线,却因个人利益的考量选择妥协,最终沦为复辟闹剧中的 “被动参与者”。
倪嗣冲:短暂 “效忠”,迅速倒戈倪嗣冲是北洋皖系将领,时任安徽督军,复辟时率先通电 “支持”,并宣布安徽 “恢复大清建制”,甚至派人到北京 “朝贺”。但当他得知张勋的辫子军战败后,立刻撕毁 “复辟通电”,转而宣布 “服从民国政府”,并出兵攻打张勋残部,其 “墙头草” 行为被时人讽刺为 “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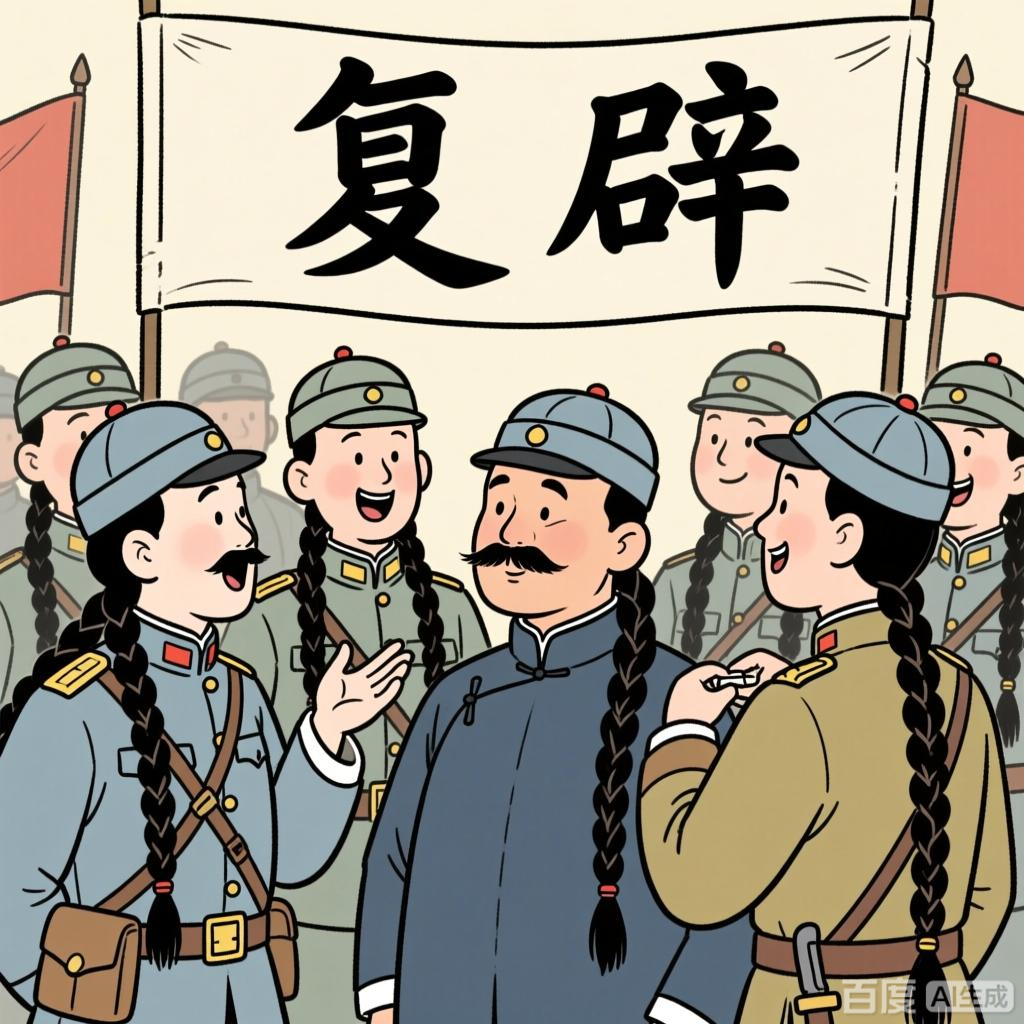
张勋复辟发生在民国建立 6 年后,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参与者们却看不到真实的民意与趋势,仍然相信武力和投机之道。
他们或为个人野心,或为旧权私欲,无坚定信念,又短视虚伪,从而让自己在这场仅持续 12 天的复辟闹剧中,所作所为让人 “大跌眼镜” ,“光环尽失”,成为莫名其妙的笑柄与“丑角”。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