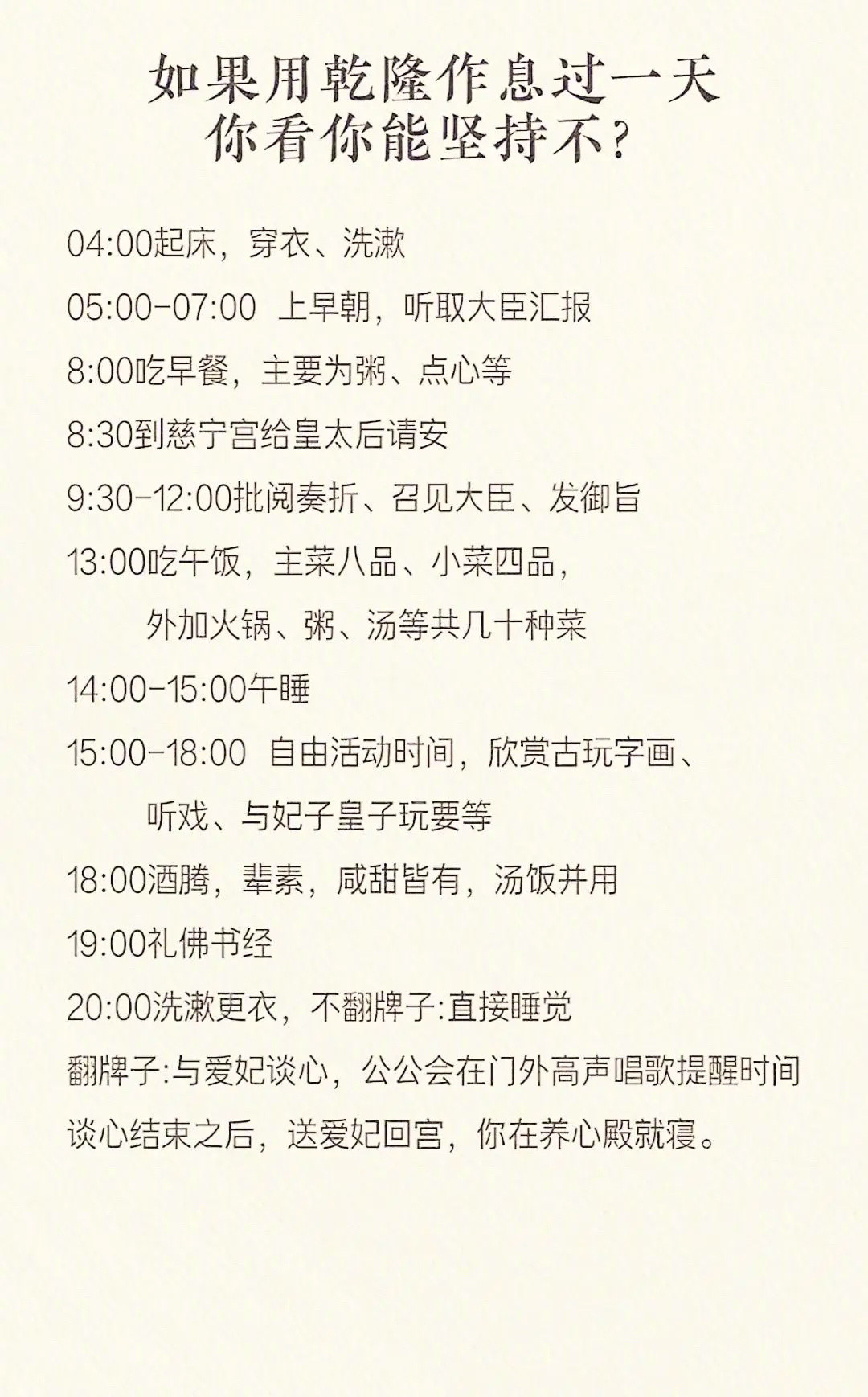康熙六十一年冬,当遗诏宣布传位于四阿哥胤禛时,许多人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而此刻站在乾清宫阶前的新帝——雍正,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张龙椅,坐上去才是第一步;能不能坐稳,要看接下来怎么走棋。
而他棋盘上最棘手的棋子,正是那些曾经与他血脉相连、如今却可能随时掀翻棋局的兄弟们。
废太子胤礽,是第一个被他划入“可留”范畴的人。
这位二哥的人生堪称一部跌宕的悲剧:刚满周岁就因生母难产而亡被立为太子,做了三十多年的储君,两度被废,最后彻底心灰意冷。
雍正去看过他一次——在咸安宫的软禁处。

胤礽穿着半旧的袍子,正对着院里的枯树发呆,听到脚步声回头,眼里竟没什么波澜,只缓缓跪下口称“皇上”。那一刻雍正就知道,这个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一具不想再挣扎的躯壳。
所以雍正给了他体面:提高用度,厚赏银钱,还封了他的儿子做郡王。
朝中有老臣感动得说“皇上仁德”,雍正听了只淡淡一笑。
他心里明镜似的:一个彻底丧失威胁的废太子,是彰显新君宽仁最好的招牌。
更何况父皇临终前确有交代,善待胤礽。
这步棋,赢的是名声,费的是小钱,何乐不为?
胤礽在雍正三年病逝时,葬礼办得风光,许多人都念着新帝的好。
可没人知道,葬礼那天雍正独自在养心殿批折子到深夜——他没时间去哀悼,因为还有更多活着的兄弟需要他应付。
大阿哥胤禔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位大哥被圈禁在宗人府已经十几年,却始终没消停。
雍正登基不久,就有宗室试探性地提出:“先帝驾崩,新朝当施仁政,是否可赦免大阿哥?”雍正当时正喝茶,放下茶盏时瓷底碰在紫檀案上,轻轻一声响。
“皇考当年亲自下旨圈禁,必有深意。”他声音平静,“朕若违背,便是不孝。”
话是这么说,实则另有考量。胤禔不同胤礽——他是有过军功的长子,性格刚狠,当年就敢提议替父杀弟,被关了这么多年,怨气只怕比当年更盛。
雍正曾看过宗人府密报:胤禔在狱中仍与外界有书信往来,字里行间全是不甘。放他出来?那无异于放虎归山。

只要这位大哥活着一天,“长子”的身份就可能被有心人利用,质疑自己继位的正当性。
所以,就让他在高墙里关到死吧。雍正十二年,胤禔病死在宗人府的消息传来时,雍正正在批阅西北军务的奏折,他只点了点头,朱笔在折子上划了一道:“知道了。”
真正让雍正寝食难安的,是八阿哥胤禩。这位“八贤王”太会做人了,朝中上至部院大臣,下至地方官吏,叫他笼络了大半。
康熙晚年,八爷府的轿子能从胡同口排到街尾,那场面雍正亲眼见过——每个人都笑脸相迎,每个人都心怀算计。
刚登基时,雍正不得不封胤禩为廉亲王,让他管着户部。
那段时间,两人在朝堂上兄友弟恭,一个称“皇上”,一个叫“八弟”,演得情真意切。
可每次下朝,雍正回到养心殿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粘竿处的人汇报:今天八爷见了谁,说了什么,收了什么礼。
转折发生在雍正二年。那年黄河大水,户部拨粮赈灾,胤禩办得漂亮,朝野一片赞誉。
庆功宴上,胤禩敬酒时笑着说:“为皇上分忧,是臣弟本分。
”雍正举杯还礼,杯中酒映着烛光,也映着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冷意——这个弟弟太得人心了,得人心到让人害怕。
清算来得很快
。雍正四年初,几条罪状突然砸向胤禩:办事不力、结党营私、贪污敛财……罪名一条比一条重。
抄家那天,廉亲王府里抄出的金银不多,却找到了几封与边将往来的书信,字句含糊,意味深长。够了,这就够了。
胤禩被削爵圈禁,改名叫“阿其那”,满语里是“待宰的鱼”的意思。同年九月,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八王爷,病死在禁所高墙之内。
消息传来那晚,雍正罕见地没有批折子,他站在窗前看着秋雨,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少年时的胤禩曾教他放过风筝。线断了,风筝就没了。
对待十阿哥胤䄉和十四阿哥胤禵,雍正留了余地。

老十是八爷党的核心,按理该重惩,但他母亲温僖贵妃出身钮祜禄大族,在关外根基深厚。
雍正掂量再三:关可以关,但不能死。于是革爵圈禁,饮食起居却还照应着,关了十年也就放了。
这是政治家的权衡——得罪一个家族和稳住一个家族,他选后者。
老十四更特殊。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康熙晚年派去西北统兵,俨然有储君之势。
雍正永远记得十四弟回京奔丧时的眼神——那里面有悲痛,有不甘,还有一种冰冷的质疑。兄弟俩在灵前对峙,四周静得能听到烛火噼啪声。
“皇上召臣弟回来,有何吩咐?”胤禵问,故意把“皇上”二字咬得很重。
雍正看着他,许久才说:“皇考山陵需人守护,你去吧。”
这是变相的软禁,却给了个体面的名头。一来母亲仁寿皇太后还健在,他不能对亲弟弟下杀手;二来十四弟在军中确有威望,逼急了反而不美。
这一守就是十三年,直到乾隆继位才召他回京。放人那天,雍正已经病重,他躺在床上对弘历说:“你十四叔……让他回来吧。”这话里有多少是亲情,多少是算计,连他自己也分不清了。
回过头看雍正这十三年的帝王路,他对兄弟的每一个决定,都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
善待的,是因为无害且有用;铲除的,是因为危险且致命;留有余地的,是因为代价太大或不值得。皇权像一柄锋利的刀,握刀的人不能有情,有情就会手软,手软就会丧命。
但雍正又不仅仅是冷酷。他在位的十三年,设军机处加强皇权,整顿吏治追缴亏空,推行摊丁入亩减轻贫农负担。

康熙晚年留下的国库空虚、吏治腐败的烂摊子,被他一点一点理清。他批的奏折堆起来能塞满半间屋子,每天只睡两个时辰是常事。
或许正因见过兄弟阋墙的惨烈,才更明白集权的重要;或许正因经历过夺嫡的凶险,才更要把权力牢牢抓在手中。
雍正十三年八月,皇帝病危。那个秋天紫禁城的枫叶红得特别早,像血染过一般。
临终前,他召来亲信大臣,交代完后事,忽然轻声问:“老八……葬在哪儿了?”
无人敢答。
雍正闭上眼睛,最后一口气叹得极轻极长。
这一生,他赢了皇位,清了国库,稳了江山,也失了所有兄弟。
紫禁城的黄昏照进殿内,把龙椅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得像是要把整个王朝的孤独都承担起来。
在这把椅子上,没有父亲,没有兄弟,只有皇帝——从来如此,也只能如此。

![所以说嘉庆给乾隆上高宗的庙号是恶意的推测完全有道理[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6960296013947822428.jpg?id=0)

![多尔衮用一辈子给了后世人一个答案[吃瓜]](http://image.uczzd.cn/2961177908594312148.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