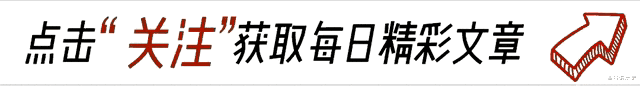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黑白三国。
建安二十四年深秋,荆州大地战云密布。
关羽挥师北伐,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樊城曹仁苦苦支撑。
眼看着关羽的威震华夏要更进一步,后方却暗流涌动。

先锋官糜芳、傅士仁因军械库失火遭关羽杖责,一个被遣回南郡,一个留守公安。当王甫忧心忡忡提醒关羽:“糜芳、傅士仁恐非竭诚之人,需一重臣总督荆州”时,关羽只淡然一指潘濬:“有潘治中在,何忧?”
他未曾察觉,这张看似稳固的荆州权力网,早已布满裂痕。

《三国志》冷冷记载:糜芳、士仁“统属关羽,与羽有隙”,潘濬“亦与关羽不穆”。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性格,此刻正将荆州推向深渊。
三颗棋子的叛变东吴吕蒙的白帆悄然划过长江。荆州门户公安城下,说客虞翻一番犀利言辞直刺傅士仁软肋:“将军坐守孤城,外无救援,不降何待?”傅士仁无奈,只能哭着投降。

糜芳,这位刘备落魄时倾家相助的妻弟,面对城下故友与寒光闪闪的吴兵,最终一声长叹,打开了城门。史书并未详述他内心的挣扎,只留下冰冷的“叛迎孙权”四字。
治中潘濬的选择更具戏剧性。荆州易主,官员皆降,唯有他称病不出。孙权亲临榻前,以楚地先贤观丁父、彭仲爽为例开导:“贤者屈伸,贵在适时。”
潘濬涕泪纵横,伏床不起。直到孙权派人亲手用面巾给他擦拭眼泪,他才起身拜谢,将荆州虚实和盘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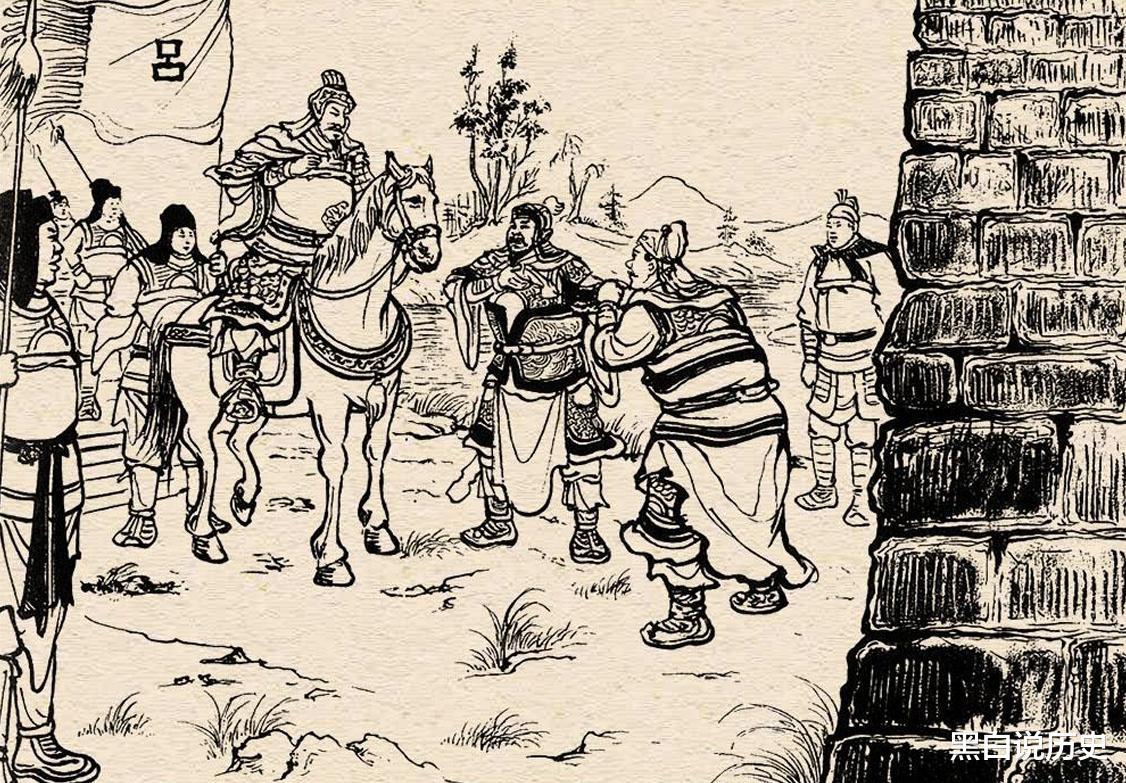
虽然都是降将,但是三个人的命运也不尽相同。
糜芳虽被孙权任命为将军,却在东吴受尽白眼。
一次行船相遇虞翻,他令对方避让,虞翻厉声呵斥:“忠心和信义都失去了,你还有何脸面侍奉君主呢?你还直接导致自家损失两座城池,你也好意思称作将军?”糜芳满面羞惭,乖乖退让下去。

后来,当虞翻的车驾经过麋芳所在营门受阻,他怒叱道:“该关的门却打开,该打开的门却关闭,有你这么做事的么?”论阴阳怪气,虞翻实在是佼佼者。
这位刘备的皇亲国戚,在故国是关羽“骄于士大夫”的受害者,在新朝又成了道德瑕疵的象征,终生在夹缝中煎熬。
傅士仁则如沉入水底的石子,史册再无波澜。或许对他而言,消失在记录中,反而是更好的结局。

唯独潘濬,在孙权麾下绽放出耀眼光芒。
他先被拜为辅军中郎将,黄武六年(227年)更接手奋武中郎将芮玄部曲,屯驻夏口。这份信任在私兵林立的东吴,堪称殊荣。
黄龙三年(231年),孙权授其符节,命他与吕岱督军五万讨伐五溪蛮夷。潘濬运筹帷幄,数年斩获数万,终于平定了蛮夷的叛乱。嘉禾年间,面对孙权宠臣吕壹的弄权,潘濬甚至密谋在宴席间手刃此獠,事泄后仍持续面谏,终致吕壹倒台。

当流言指其暗通蜀汉大将军蒋琬(潘濬表兄)时,孙权一句“承明不为此也”,足见信重之深。
被演义掩盖的真相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蜀汉正统观服务,给了糜芳、傅士仁一个“大快人心”的结局——刘备东征时二人杀吴将马忠归降,却被盛怒的刘备处以凌迟。
历史却远比小说冷静残酷。

二人终老东吴,糜芳更在黄武二年(223年)随贺齐攻蕲春,俘获魏将晋宗,以吴将身份走完余生。
潘濬在演义中被王甫贬为“多忌而好利”,历史上却是让孙权亲自登门劝降、托付兵符的重臣。
陈寿在《三国志》中虽未单独立传,但其事迹散见诸卷,勾勒出一个能力卓著、刚毅敢为的能臣形象。蜀汉痛失的经世之才,反成东吴稳定荆南的柱石。

关羽的败亡,远非“大意失荆州”的轻描淡写。
荆州核心团队的集体叛变,是一场精心设计却终被引爆的管理灾难。 刘备留下糜芳(皇亲)、傅士仁(旧部)、潘濬(荆州士族代表)的组合,本意是兼顾忠诚与本土根基。
关羽却未能弥合缝隙,反使矛盾激化。

糜芳的遭遇尤具悲剧性。糜家对刘备恩同再造,其妹更是刘备患难之妻。如此根正苗红的人物,竟在关羽麾下受到怠慢,最终在吴营中背负骂名苟活。
而曾与关羽关系紧张的潘濬,却在孙权“以巾拭面”的诚意感召下倾心效力,成为一代名臣。
这多少,令人意难平啊!
(本文主要参考《三国志》)
诸位看官,在你看来,这三位降将,究竟为何会离心离德,导致荆州拱手相让呢?
欢迎评论区煮酒论英雄,友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