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背过李绅的《悯农》,诗中对农民的悲悯、对粮食的珍视,让无数人以为他是个心怀百姓的君子。
可历史上真实的李绅,却与诗中形象判若两人 —— 他靠才华登科入仕,最终官至宰相,却在发迹后彻底暴露了贪婪残暴的本性。
李绅的才华毋庸置疑。他出身官宦世家,27 岁考中进士,一路从地方官做到宰相,成为晚唐政坛的重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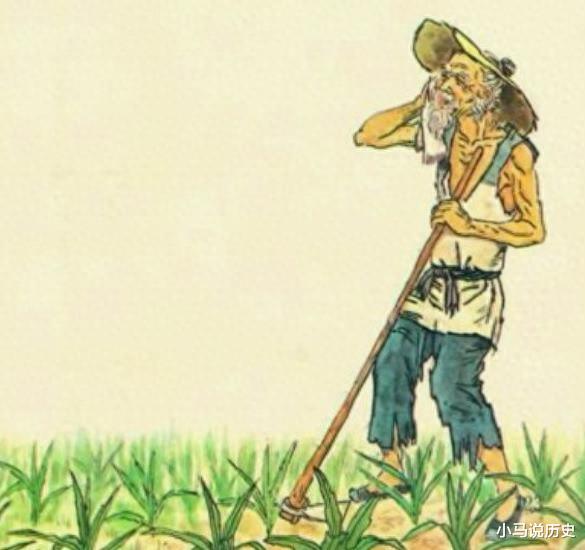
可随着地位的提升,李绅早年的 “悯农之心” 早已被权力与财富吞噬。史书记载,他晚年生活极度奢靡,单是一顿饭的花费就高达千万钱。
最夸张的是他爱吃 “鸡舌羹”,每次制作这道菜,都要宰杀三百多只活鸡,只取鸡舌入药,其余鸡肉则随意丢弃,堆积如山 —— 这般浪费,与他诗中 “粒粒皆辛苦” 的劝诫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更可怕的是他的为官之道。李绅任淮南节度使时,当地发生兵变,他派兵镇压后,竟下令将所有参与兵变的人连同家属全部处死,甚至连无辜的百姓也被牵连,一时间血流成河。
百姓私下称他为 “酷吏”,可他却毫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
晚年的李绅卷入 “牛李党争”,最终被罢官贬谪,病逝于贬所。他的《悯农》传为千古绝唱,可他的人品,却连 “普通人” 的底线都未守住。
第二位----宋之问:“近乡情更怯”?是怕被人报复害怕了吗?若论唐代诗歌的发展,宋之问绝对占有一席之地。当年,武则天游洛南龙门时,他作《龙门应制》,一句 “宿雨霁氛埃,流云度城阙” 将大唐气象写得恢弘壮阔,竟让武后当场收回赐予他人的锦袍,转赠于他,留下 “夺袍取诗” 的文坛轶事。

可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人品上却堪称 “卑劣”。
他一生最擅长 “攀附权贵”—— 武后掌权时,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权倾朝野,宋之问便不顾文人风骨,主动投靠二张,不仅为他们代笔写诗文讨好武后,甚至为了讨好张易之,甘愿做其 “捧溺器” 的侍从,这般谄媚姿态,早已将文人的清高抛诸脑后。

神龙政变后,二张被杀,唐中宗复位,宋之问失去靠山,被贬为泷州参军。可他受不了蛮荒之地的清苦,竟偷偷逃回洛阳,躲进好友张仲之家中。彼时张仲之正与王同皎等人密谋诛杀专权的武三思,满心信任地将计划告知宋之问。
谁知宋之问转头就跑到武三思府上告密,将好友的生死置之度外。最终,张仲之、王同皎等人被满门抄斩,而宋之问却因 “告密有功” 被武三思提拔,甚至连私自逃回洛阳的罪名也被一笔勾销。

后来,李隆基登基后,开始清算武周及中宗时期的奸佞之徒。宋之问因早年依附二张、武三思,又参与过多场宫廷斗争,被列为 “奸党”,赐死于钦州。这位写出无数清雅诗句的诗人,终究没能逃过 “善恶终有报” 的结局,他的才华被载入诗史,而他的人品,却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三位----元稹,诗有多深情,人就有多渣!元稹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把对亡妻的 “深情” 写得感天动地,多少人拿这句当爱情圣经,觉得他肯定是个 “一生只爱一个人” 的痴情种。
还有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朋友白居易生病,他写得比自己生病还着急,光看诗还以为他俩是 “过命的交情”。

可现实中的元稹,跟诗里的形象比起来,简直像换了个人。先说说他的感情史,那叫一个 “混乱又离谱”。早年他在蒲州当官,认识了才女崔莺莺,俩人迅速坠入爱河,元稹天天给崔莺莺写甜言蜜语的诗,把姑娘哄得死心塌地。
结果没过多久,元稹要去长安考功名,为了攀附权贵,直接把崔莺莺抛到脑后,娶了高官之女韦丛。
更缺德的是,他后来还写了本《莺莺传》,把自己塑造成 “被美色诱惑的受害者”,说崔莺莺是 “妖孽”,把始乱终弃说得理直气壮,妥妥的渣男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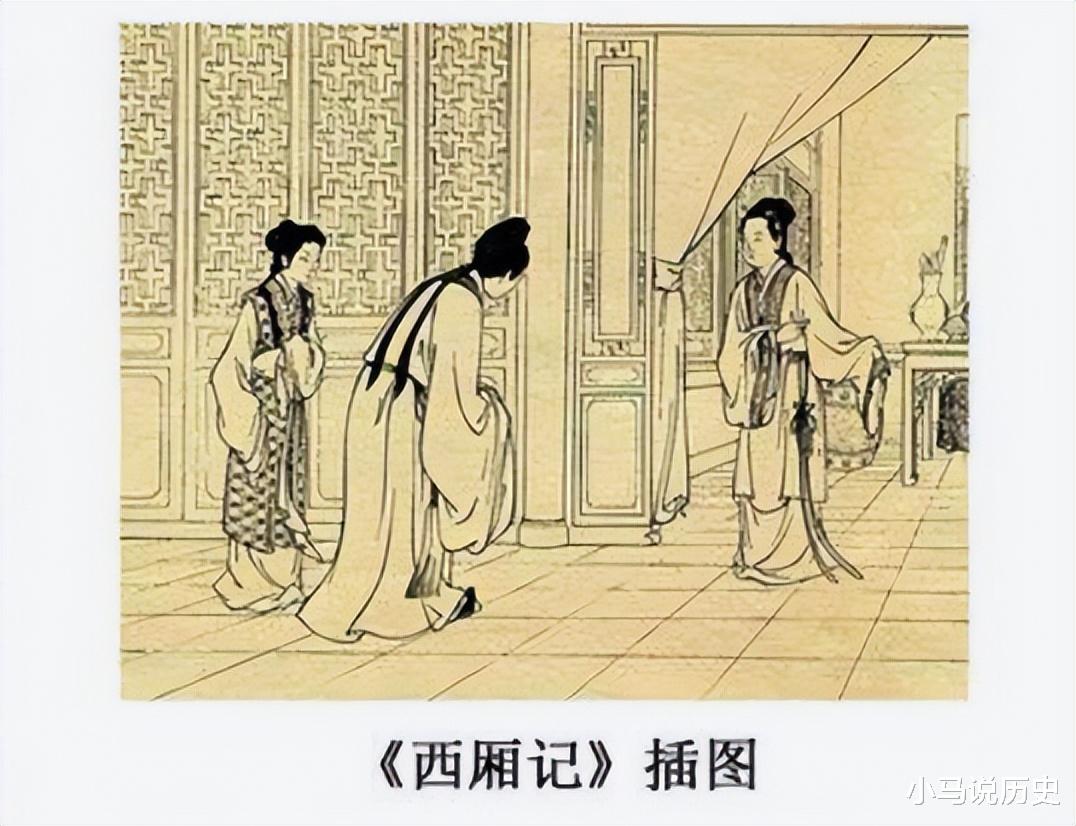
后来他的妻子韦丛去世,元稹写出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还以为他得多深情,结果,不到一年,元稹就耐不住寂寞,跟比他大 11 岁的女诗人薛涛搞起了 “姐弟恋”。他天天给薛涛写暧昧的 “情书诗”,什么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把薛涛迷得神魂颠倒。

后来啊,朝廷一道命令让他去蜀地当官,他立马收拾行李跑路,连句告别都没有,只留下薛涛一个人对着满桌诗稿伤心。后来薛涛专门做了 “薛涛笺”,就是为了写给他的诗,可这些诗最后全成了 “单相思的废纸”,想想都替薛涛不值!
不光感情渣,元稹当官也没什么底线。有次为了打压政敌,他故意编造罪名诬陷对方,把人家害得家破人亡。白居易看不下去,劝他 “做人留一线”,结果元稹嘴上答应,转头该咋干还咋干。晚年他官至宰相,可名声早就臭了,连他的好朋友都跟他渐渐疏远。

最讽刺的是,元稹一辈子写了无数深情的诗,可他的行为却一点都不深情;他写过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比如《织妇词》里 “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看似同情织妇,可他当官时却没少搜刮民财。
宋之问的诗能流传千古,可他的人品,却永远成了历史的 “笑柄”。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