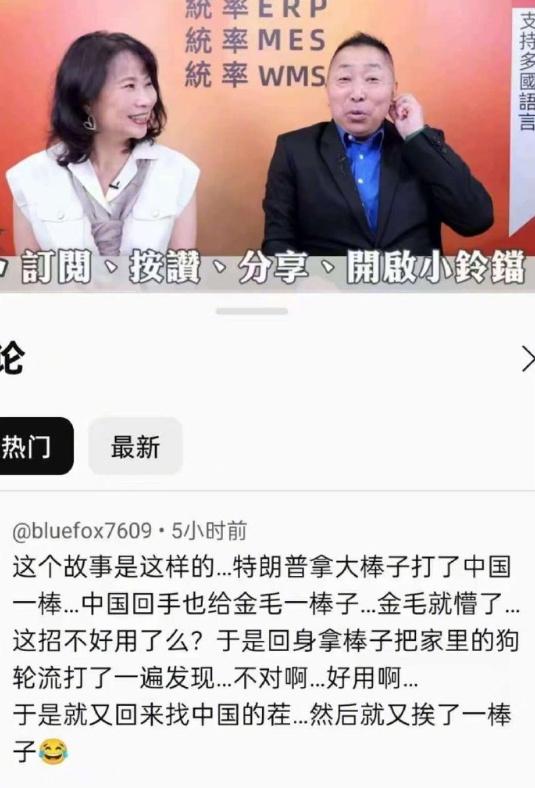我叫陈玉玲,今年七十多了,现在坐在西安家里的阳台晒太阳,看着窗外的钟鼓楼,总想起在宝鸡县孙家塬插队的那些年,想起刘大妈——那个让我喊了一声“干妈”,就记了一辈子的老人。这事儿说起来快五十年了,可每一个细节都跟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清楚楚。
1969年春天,我刚满十七,跟郭强、“李建国”他们一群西安知青,坐了大半天火车,又转了拖拉机,才到孙家塬大队。我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生,郭强比我大一岁,是六六届的,他人高马大,说话办事都透着实在,后来成了我们知青点的小组长。李建国跟我是同班同学,那时候就总跟在我身后,放学一起走,周末一起去图书馆,现在想想,他那点心思我后来才明白,可当时光顾着适应农村生活,没心思琢磨这些。
到了大队,孙队长给我们分住处,因为队里没现成的知青点,就让我们暂时借住老乡家。我被分到了刘大妈家——她是烈军属,男人在潼关保卫战的时候没了,三十岁就守了寡,后来唯一的儿子又牺牲在渡江战役,才十九岁。那时候刘大妈不到六十,头发白了一多半,可腰板挺得直,说话声音也亮。
我刚到她家的时候,她把西窑收拾得干干净净,炕上铺了新晒的褥子,还带着太阳的味儿。“娃娃,你住炕头,暖和。”她边说边把我的行李往炕头挪,自己却抱了床旧棉絮铺在炕梢。我赶紧说:“大妈,我年轻,不怕冷,您住炕头。”她却摆手:“不行不行,你们城里娃娃细皮嫩肉的,冻着了咋干活?我都冻惯了。”
从那天起,刘大妈就把我当亲闺女待。每天天不亮,她就起来烧炕做饭,玉米糊糊熬得稠稠的,还会就着咸菜蒸个红薯。等我睡醒,洗脸水都倒好了,温度正好不烫嘴。吃完饭我想刷碗,她一把夺过碗:“你歇着去,就俩碗,我顺手就刷了。”起初我还不好意思,后来发现不管我咋抢,她都不让我沾家务,说:“你白天要下地干活,累得慌,家里这点活儿我能干。”

那时候郭强和李建国常来串门,每次来都不空手,要么帮刘大妈挑两桶水,要么把院子里的柴火劈好码整齐。刘大妈也不客气,留他们吃饭,煮面条的时候会卧个鸡蛋,自己舍不得吃,都夹给我们三个。“大妈,您也吃。”郭强把鸡蛋往她碗里推,她又推回来:“我老了,吃了浪费,你们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晚饭后是我跟刘大妈最亲近的时候,她坐在炕沿上,手里纳着鞋底,跟我讲她男人的事:“那时候他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日本人来的时候,他带着人去埋地雷,回来的时候裤腿都炸烂了,腿上全是血,还笑着说‘没让小鬼子占便宜’。”讲起儿子,她声音就低了:“我娃跟你一般大的时候,就报名参军了,走的时候说‘妈,等解放了我给你盖瓦房’,可他再也没回来……”说着说着,她就抹眼泪,我也跟着哭,伸手抱了抱她:“大妈,以后我就是您的闺女。”
这话刚说完,刘大妈突然愣了,然后一把抱住我,哭得浑身发抖:“娃娃,你说啥?你再说一遍?”我鼻子一酸,大声说:“大妈,我当您的闺女,我叫您干妈!”她这才止住哭,擦着眼泪笑:“好,好,我有闺女了!二十年了,没人叫我妈了……”
那年秋后,队里给知青打了新窑洞,成立了知青点,我要搬走的时候,刘大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放,眼泪掉在我手背上,烫得慌。“干妈,我常来看您。”我也哭,她点头:“哎,你有空就来,我给你做玉米饼子。”
搬到知青点后,我果然常去刘大妈家,她也总往知青点跑,有时候拎着一篮煮好的毛豆,有时候揣着两个烤土豆,见了我就往我手里塞。有一次我感冒了,发烧浑身疼,郭强背着我去公社卫生院,回来的时候发现刘大妈在知青点门口等着,手里拎着个砂锅,里面是熬好的姜汤,还放了红糖。“娃娃,快喝了,发发汗就好了。”她端着砂锅,看着我一口一口喝下去,才放心地走。
图片
那时候我跟郭强的心思慢慢不一样了,他总护着我,下地的时候重活他都抢着干,我割麦子割到手,他赶紧掏出自家带的创可贴,小心翼翼地给我包上,还说:“以后别这么拼命,我多割点就有了。”李建国看在眼里,后来就不怎么跟我们一起去刘大妈家了,有一次我撞见他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抹眼泪,问他咋了,他说“没事,迷了眼”,现在想想,那时候他心里得多难受啊——后来他跟我说,从小学三年级我帮他捡过一次掉在泥里的课本开始,他就把我放在心里了,只是没好意思说。
1973年春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吓得不行,郭强也慌了,拉着我回西安找父母。双方父母都挺开通,说“既然有了孩子,就结婚吧”。我们回到孙家塬,去公社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就请知青和刘大妈吃了顿面条,刘大妈却给我塞了个红布包,里面是五十块钱和一对银镯子。“这是我当年的陪嫁,给你当念想,以后好好过日子。”我不要,她却急了:“你是我闺女,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你不收就是嫌我老。”
自从我怀孕,刘大妈更上心了,每天都来知青点,给我送鸡蛋,有时候是自家鸡下的,有时候是她用玉米换的。她还去找孙队长:“陈娃娃怀了孕,不能干重活,你给她安排点轻省的,比如晒麦子、捡棉花啥的。”孙队长笑着说:“刘大妈,您比她亲妈还上心。”她梗着脖子说:“她就是我亲闺女!”
快到春节的时候,我生了个儿子,取名叫郭长安,希望他平平安安。那时候我爸妈和郭强爸妈都没来,刘大妈主动来伺候我坐月子,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熬成汤给我下奶,还用家里不多的小麦换了小米,每天给我熬小米粥。晚上她跟我睡一个炕,帮我哄孩子,孩子哭了她就抱起来拍,让我好好休息。“你刚生完娃,身子虚,别累着。”她熬红了眼睛,却从不说累。
郭长安从小就跟刘大妈亲,别的孩子先会叫“妈妈”,他第一声叫的是“奶奶”,一叫出口,刘大妈抱着他哭了半天,说:“我娃认我,我娃认我。”长安会走了以后,天天跟在刘大妈身后,“奶奶”长“奶奶”短地叫,刘大妈走到哪带他到哪,给他摘野枣,编蚂蚱笼,比我们当父母的还上心。有一次长安摔了一跤,膝盖破了皮,我还没来得及哄,刘大妈先把他抱起来,吹着伤口骂“这破石头咋不长眼”,那模样,比自己受伤还心疼。
后来知青开始陆续招工回城,我和郭强因为结了婚有了孩子,一直没等到机会,心里挺难受的。刘大妈看出来了,安慰我们:“娃娃,别愁,在哪不是过日子?孙家塬的人都待见你们,你们在这住,我天天给你们做饭,长安也有人带,多好。”话是这么说,可我们知道,她心里也盼着我们好,只是怕我们难受,才这么说——有一次我听见她跟孙队长念叨:“要是长安能去城里上学就好了,城里的学堂比咱这好。”
1979年夏天,终于有了好消息:我妈提前退休,我可以顶岗去她单位——西安人民搪瓷厂上班;郭强他爸的单位也同意安置他,去西安冶金机械厂。我们拿着通知,第一时间就去告诉刘大妈,她比我们还高兴,忙着给我们收拾东西,把家里的晒干菜、核桃都往包里塞,可眼睛却红了,手也不停发抖。
回城那天,刘大妈抱着长安不肯放,长安也哭,抱着她的腿喊:“奶奶,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还没跟你去摘枣呢!”刘大妈抹着眼泪,把自己戴了几十年的银镯子摘下来,套在长安手腕上:“娃,这个你带着,想奶奶了就看看它,奶奶有空就去看你。”车子开的时候,我从车窗回头看,刘大妈还站在村口,手里挥着我们给她买的蓝布衫,身影越来越小,直到看不见,我眼泪哗哗地流,郭强也红了眼。
回到西安,我们有了自己的家,郭强家住房宽敞,两室一厅,我爸妈也常来帮忙做饭,可长安天天夜里哭,喊着要找奶奶,有时候睡着睡着就坐起来,揉着眼睛问“奶奶咋还不来”。有一次我实在没办法,抱着他给刘大妈打电话,电话里长安哭着说“奶奶,我想你做的玉米饼子”,刘大妈在那头也哭,说“娃,奶奶也想你,等秋收完了就去看你”。

郭强的爸妈看在眼里,跟我们说:“要不把刘大妈接过来吧,她一个人在村里也孤单,过来跟咱们一起住,互相有个照应,长安也能安心。”我和郭强一听,赶紧点头,这正是我们想的。郭强说:“妈这辈子不容易,没享过福,咱们得给她养老送终,不能让她一个人在村里受苦。”
中秋节过后,我们一家三口买了好多东西——给刘大妈的棉袄、棉鞋,给孙队长的酒,给村里孩子的水果糖,坐火车去了孙家塬。刚到村口,就看见刘大妈站在老槐树下等,头发又白了不少,可看见长安,眼睛一下子亮了。长安扑到她怀里,哭着说“奶奶,我好想你”,刘大妈抱着他,眼泪掉在长安的头发上:“娃,奶奶也想你,天天想。”
我们跟刘大妈说想接她去西安,她却犯了难,搓着手说:“我去了会不会给你们添麻烦?我老了,干活也不利索了,还得你们照顾。”孙队长在一旁劝:“刘大妈,您就去吧,陈娃和郭强都是好孩子,您去了他们也放心,长安也能天天跟您在一起,多好啊。”村里的老乡也说:“您该去享享福了,您对陈娃那么好,他们孝顺您是应该的。”刘大妈这才点了头,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物,还有她男人和儿子的照片。
到了西安,刘大妈刚开始有点不适应,不敢用煤气灶,说“这玩意儿咋没火就热了”,不敢坐公交车,怕自己走丢。我和郭强就慢慢教她,郭强休班的时候,带着她去逛钟鼓楼,吃羊肉泡馍,她吃得直点头:“这馍真好吃,比咱村里的泡馍香。”后来她慢慢适应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饭,熬小米粥,蒸馒头,还去菜市场买了两只小鸡,养在阳台的角落里,说“给长安下鸡蛋吃”。
长安每天放学回来,第一句话就是“奶奶,我回来了”,然后就跟刘大妈讲学校的事,刘大妈坐在小板凳上,听得笑眯眯的,还帮他检查作业。有一次长安考了满分,刘大妈高兴得不行,去菜市场买了肉,给我们包了饺子,说“娃考得好,得奖励”。我要帮忙,她不让:“你上班累,歇着去,我来包,我包的饺子你爱吃。”
刘大妈还总帮我们做家务,扫地、擦桌子、洗衣服,我说“您歇着吧,这些我来就行”,她却说“我在家也没事干,干点活舒服,你不让我干,我就回孙家塬了”。没办法,我们只能让她干些轻活,每天提醒她别累着。邻居们都说:“你们家这位老人真好,这么勤快,还疼孩子,你们真是有福气。”刘大妈听了,就笑着说:“是我有福气,遇到这么好的娃,比亲闺女亲儿子还孝顺。”
休班的时候,我们常带着刘大妈去玩,去大雁塔,去华清池,她每次都要跟我们拍照,说“回去给孙队长他们看看,我也见了大世面”。有一次我们带她去买衣服,她非要买便宜的,说“衣服能穿就行,不用买贵的”,我硬给她买了件呢子大衣,她穿上舍不得脱,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说“这辈子还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幸福的日子过得真快,转眼长安上初二了,刘大妈也快七十了,身子骨一直挺硬朗,可那年冬天,她突然得了犯困的毛病,有时候端着饭碗就能睡着,说话也没以前利索了。郭强说要带她去医院检查,她却摇头:“不用去,我就是老了,觉多,过几天就好了。”后来她又说想家了,想回孙家塬看看,说“我好几年没回去了,想看看我的窑,想看看孙队长他们”。
从西安到孙家塬二百多公里,要坐火车再转汽车,我们怕她身体受不了,劝她:“等开春了,天气暖和了再去,现在天冷,路上不方便。”可她铁了心,说“我要是不回去看看,心里不踏实,觉都睡不好”,后来甚至说“你们不让我回去,我就不吃饭”。郭强没办法,跟厂长请假,想借单位的双排座汽车送她,她却不肯:“别麻烦人家,我坐火车就行,我身子骨好着呢,能走。”
拗不过她,我们一家三口请了假,买了好多东西,陪着她坐火车去了孙家塬。一路上,刘大妈精神特别好,跟我们讲她以前在村里的事,说“孙队长家的娃小时候总跟在我身后,现在也该娶媳妇了吧”,还说“我那窑后面有棵枣树,不知道还结不结果”。到了村里,老乡们都来接,孙队长握着刘大妈的手说“您可算回来了,我们都想您”,刘大妈笑得合不拢嘴,把带来的东西分给大家。
她的那两孔土窑,孙队长一直帮她照管着,隔一段时间就打开通风,院子里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窑里的被褥也晒得干干净净。刘大妈走进窑里,摸了摸炕沿,又摸了摸桌子,眼泪掉了下来:“还是我这老窝好,住着踏实。”那天她挨家串门,跟老乡们说她在西安的日子,说我们对她多好,说长安多懂事,说得满脸骄傲。
晚上我们在孙队长家吃饭,刘大妈喝了点酒,话也多了,说“我这辈子没白活,有陈娃和郭强这么好的娃,有长安这么好的孙娃,我知足了”。吃完饭我们回窑里住,孙队长的媳妇提前烧了炕,炕热乎乎的,刘大妈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睡得很沉,还打着小呼噜,我们以为她累坏了,也没多想。
第二天早上,太阳都晒到炕梢了,刘大妈还没醒,以前她从没睡过懒觉。我小声喊:“干妈,醒醒,该吃早饭了。”没动静,我又推了推她,这才发现她的身体已经硬了,脸上还带着笑,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是她男人和儿子的合影。
我一下子就哭了,郭强和长安也跪在炕上哭,哭得肝肠寸断,孙队长和老乡们听到动静跑过来,也都红了眼。在老乡们的帮忙下,我们给刘大妈办了后事,按照她的意思,把她葬在了她男人和儿子的坟旁边。烧纸的时候,长安哭着说“奶奶,您放心,我会常来看您的,我还记得您教我摘枣”。
回西安后,我把刘大妈的东西收拾好,她的银镯子、蓝布衫、还有她给长安编的蚂蚱笼,都放在一个箱子里,想她了就拿出来看看。每年清明节和她的祭日,不管多忙,我们都会带着长安回孙家塬给她上坟,给她带她爱吃的玉米饼子,跟她说家里的事——长安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跟她说“干妈,长安考上大学了,您要是在,肯定高兴”;长安结婚的时候,我们跟她说“干妈,长安结婚了,您有孙媳妇了”。
现在长安也有了孩子,每次带孩子去上坟,都会跟孩子说“这是太奶奶,她是个特别好的人,以前特别疼爸爸”。孩子会奶声奶气地喊“太奶奶”,我听着,就想起刘大妈当年抱着长安的样子,眼泪又会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