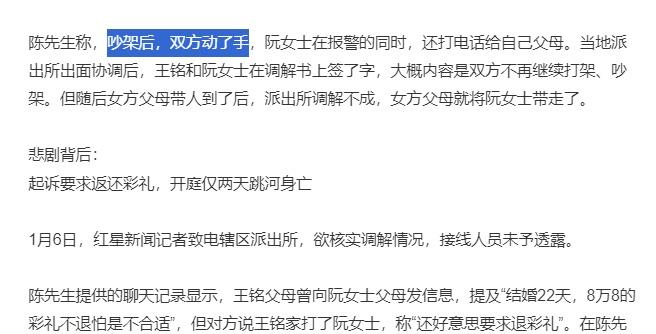1982年7月30日,一架载着外宾的专机从上海向北京飞去,飞机起飞后没多久,机长突然感觉头上的耳机被人摘掉,转头一看,一名歹徒恶狠狠地说道:“不许动,马上改变飞机航向,飞到台北的桃园机场!” 1982年7月30日,一架满载非洲某国军事代表团的飞机从上海起飞,仅仅起飞十几分钟,负责安保的郑延武,利用职务之便溜进了核心区域,随着锁门声,整个驾驶舱变成了一个密室。 郑延武早已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他右手持枪,左手已经泼洒了汽油并死死攥着打火机。 劫机者的意图非常明确,航向150度,直飞海峡对岸的桃园机场,面对枪口和足以把飞机炸成火球的汽油,机长兰丁寿和副驾驶张景海甚至连惊呼的时间都被剥夺了。 两位飞行员达成了一种令人惊叹的默契,面对“飞往台湾”的嘶吼,他们没有选择激怒歹徒,而是展现出一种经过伪装的顺从。 兰丁寿装模作样地调整仪表,将右边的罗盘刻度指像了150度,那个数字成了郑延武眼中的定心丸,让他以为计谋得逞露出了得意的冷笑。 然而,这只是机长设下的视觉陷阱,郑延武看不懂的是,就在他擦汗分神的那一瞬,飞机的控制权已经被悄然切换——右罗盘虽然指着东南,但实际上控制飞行的左罗盘早已带着飞机悄悄向西南方向折返。 在这场无声的博弈中,每一个眼神的交换都承载着全机人的性命,与此同时,副驾驶张景海的双脚正极其隐秘地在座位下摸索,悄无声息地拨开了地板上的通风口盖板。 如果不把高浓度的汽油味排出去,即便制服了歹徒,哪怕一颗走火的子弹击中地板,甚至是一个剧烈的摩擦,都可能引发瞬间爆燃。 此时,飞机的自动驾驶仪也被悄悄接通,两位驾驶员将座椅不动声色地调到了最后端,并悄悄解开了安全带——他们不是为了逃生,而是为了在狭小的空间里腾出那一丁点能让人暴起反击的施展余地。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通过地底通风口的气流效应,驾驶舱内让人晕眩的油气味终于开始变淡。 而在舱门之外,非洲贵宾们还在享受着航程,偶尔对于行程的小延误并不在意,他们丝毫不知道几米之外的驾驶舱里正在上演怎样的惊涛骇浪。 兰丁寿突然指着风挡玻璃外大喊一声,紧接着张景海也配合地喊出发现了“外国商船”,这种由于极度渴望成功而产生的条件反射,让郑延武本能地俯身贴向窗前查看——这是人性中无法克服的弱点,也是机组人员苦等的唯一破绽。 就像被压抑到极限的弹簧,兰丁寿和张景海几乎在同一毫秒从座位上弹射而出,死死扑向了那个可能会毁灭一切的身影。 狭小的空间瞬间变成了搏命的角斗场,身为受过特训的安保人员,郑延武的反应极快,在这毫厘之间,枪声还是响了。 狭窄的空间让这一幕惨烈无比:砰砰的枪声夹杂着发动机的轰鸣,在密闭空间里炸响,一颗子弹打穿了舱顶,另一颗直接钻进了张景海的大腿。 但肾上腺素的作用下,这种剧痛被暂时屏蔽了,三个人影扭打在一起,巨大的冲击力硬生生地撞开了那扇原本反锁的舱门,几个人像滚地葫芦一样从驾驶舱里摔到了外面的通道上。 一直在门外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的领航员刘铁军,此刻终于等到了介入的机会,但他面对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一幕:三个穿着同样白色短袖制服的人在地上翻滚、死掐,场面混乱至极。 “底下那个!底下那个!”伴随着战友声嘶力竭的吼叫,刘铁军没有任何犹豫,他早已抄起了早已备好的消防太平斧,在那电光石火间找准了目标。 随着手起斧落的闷响,这场持续了数十分钟的空中危机,终于在这个疯狂的安保干部的惨叫声中画上了句号。 即使在如此惨烈的搏斗之后,这架“子爵号”依然平稳地飞行在云端,重伤的张景海强忍着此时才袭来的剧痛,在清理现场后重新坐回驾驶位,配合机长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南京机场。 更令人称奇的是地面上的处置,舱门打开后,地勤与安保迅速介入,早已等待的救护车接走了伤员,而对于后舱毫不知情的贵宾们,这只不过是一次因为“机械故障”而导致的备降和换机,他们带着微笑走下舷梯,被礼貌地引导至另一架专机继续前往北京参加庆祝活动。 直至今日,那段航程的乘客们或许都不知道,就在他们谈笑风生的一板之隔,曾有一群中国机组成员,用智慧、鲜血和令人胆寒的勇气,把一场必死的劫难消弭于无形,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永远锁在了那个满是汽油味与火药味的驾驶舱里。 主要信源:(北京日报客户端——新中国劫机“第一案”:歹徒开6枪被制服,外宾丝毫未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