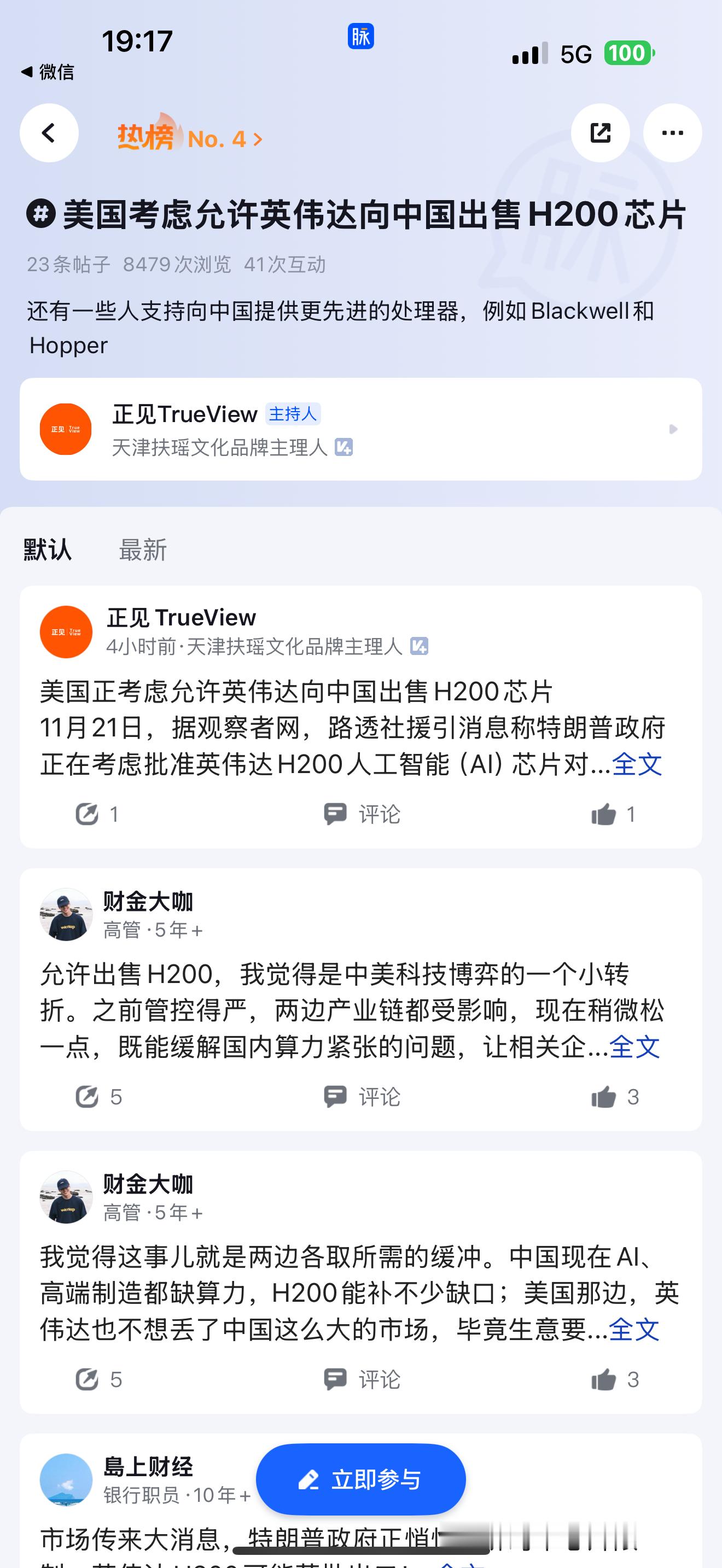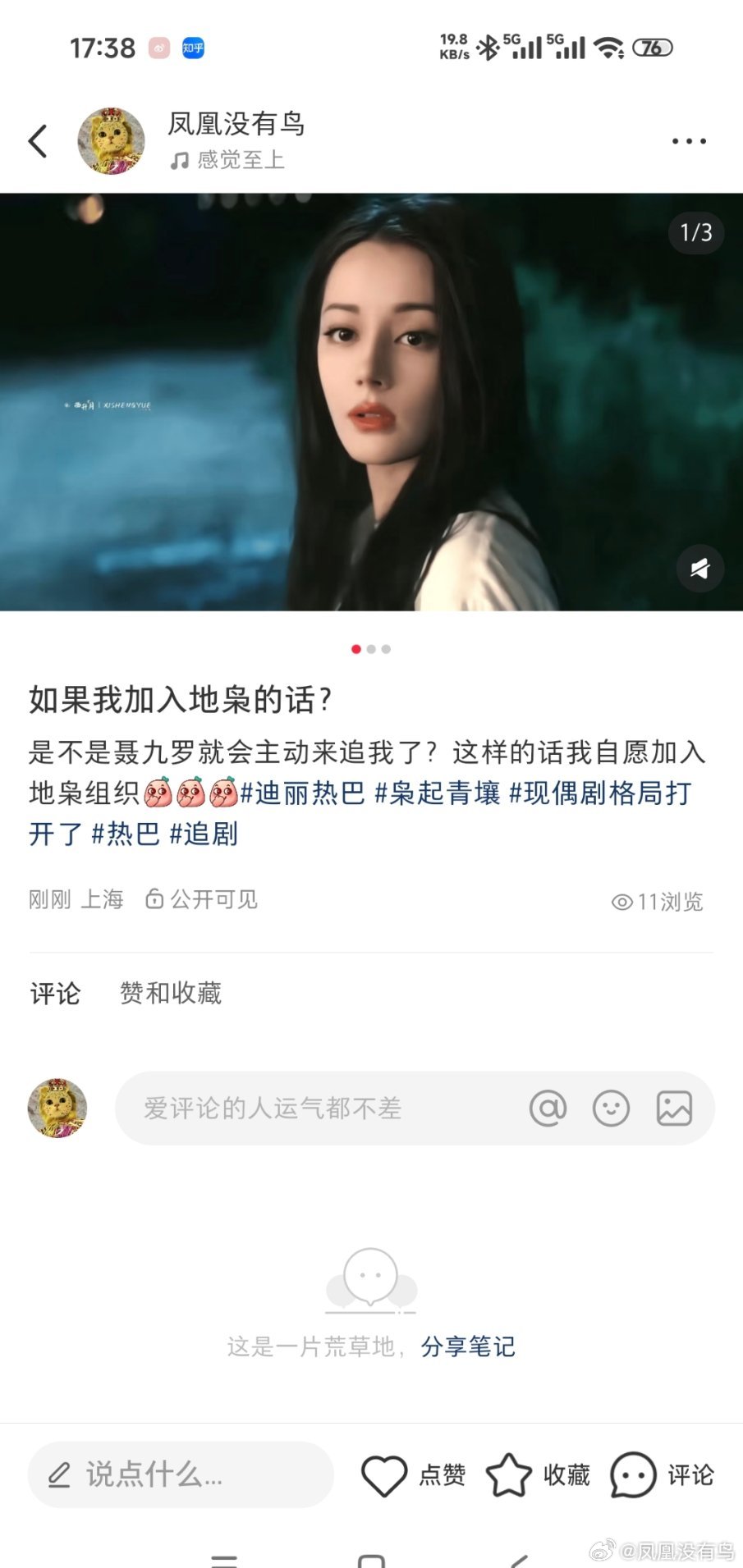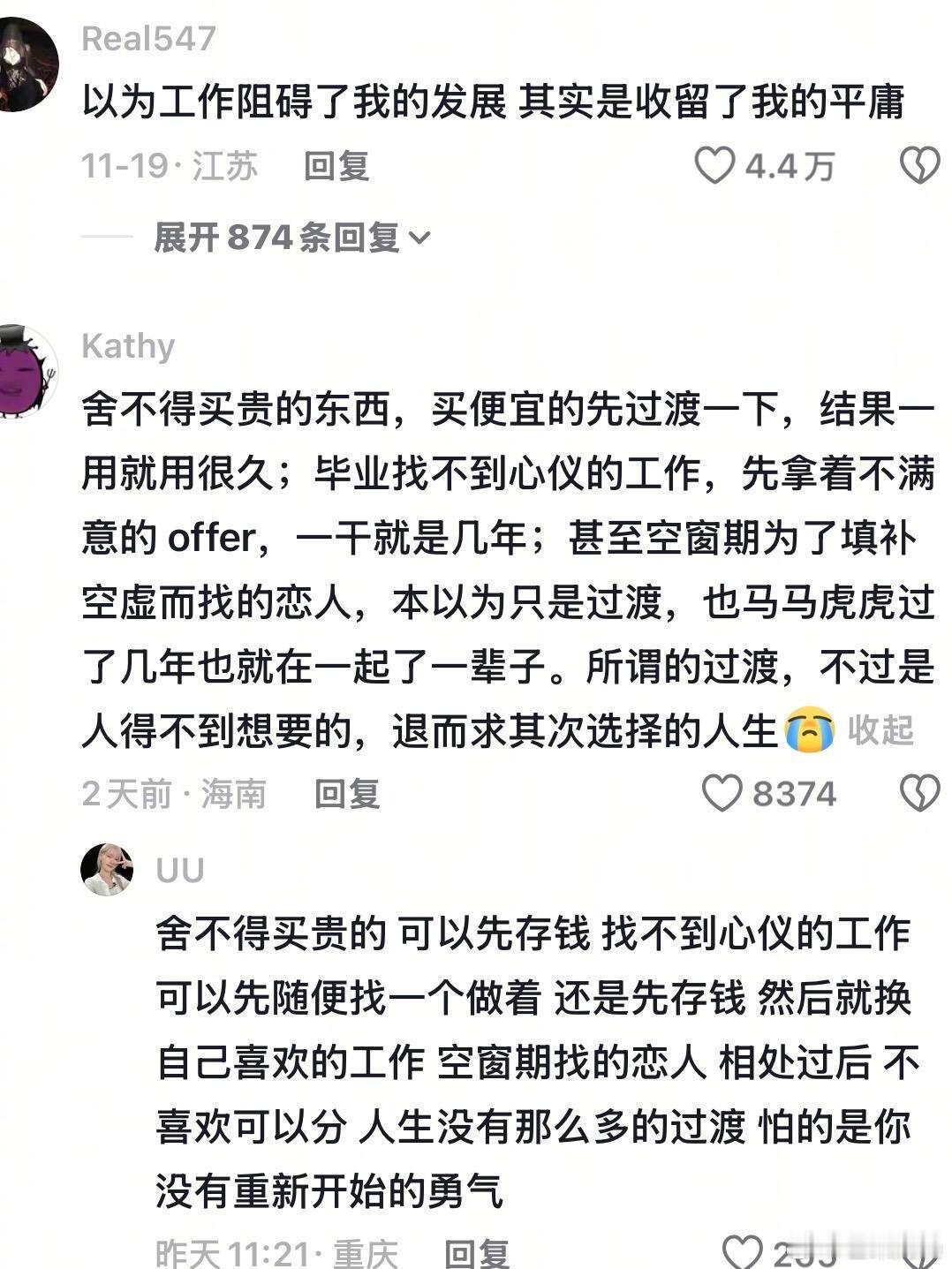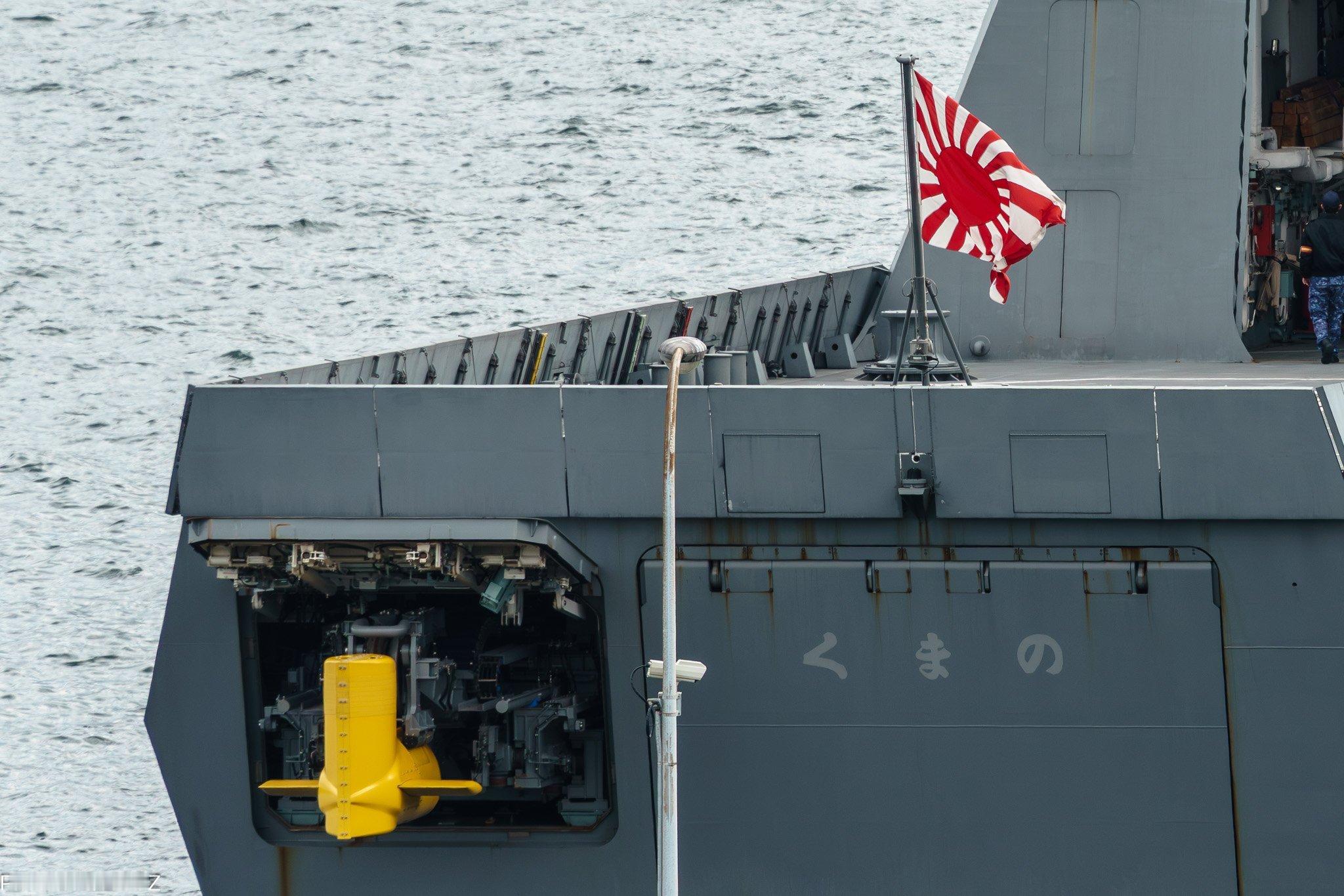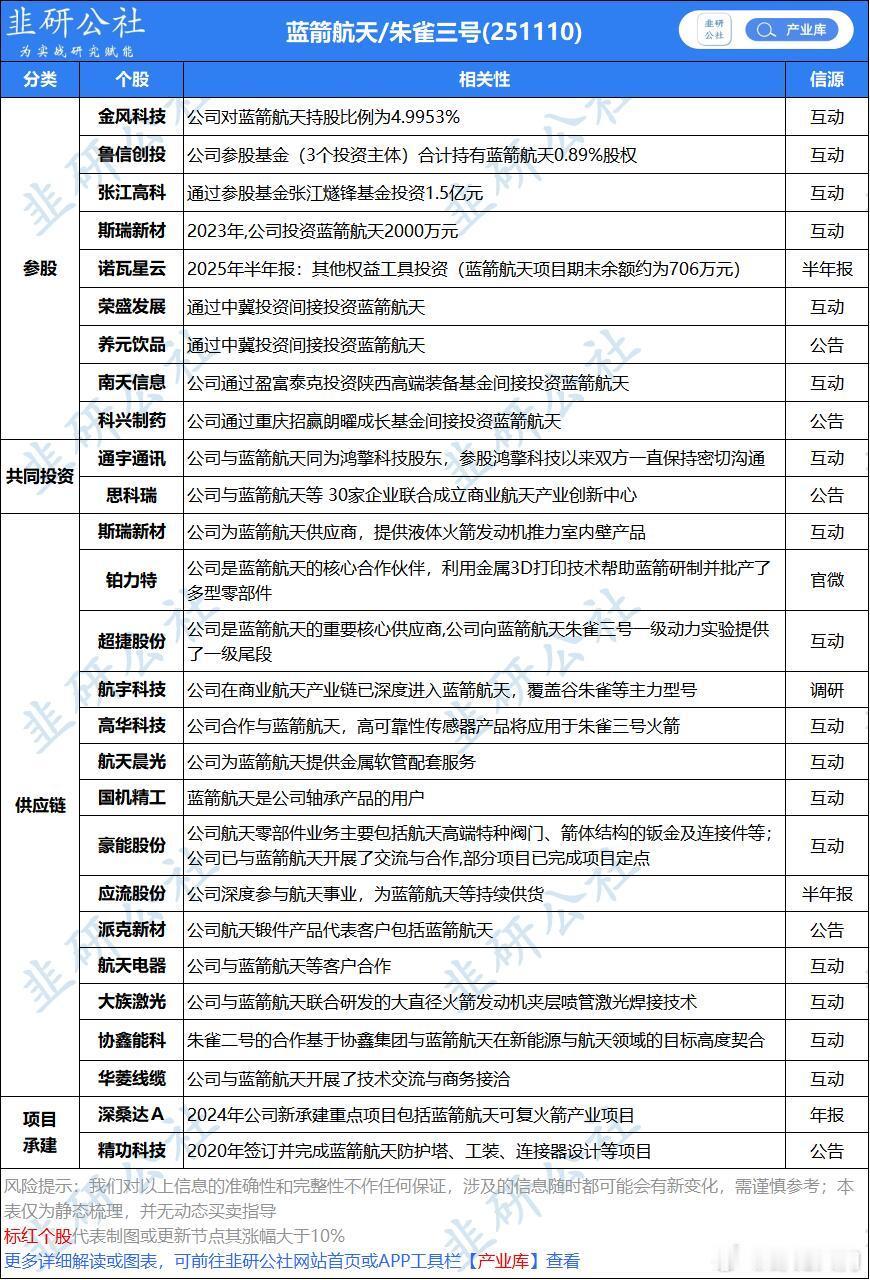那个毁掉周五晚宴的哔哔声
1957年10月4日,星期五。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里,一场盛大的鸡尾酒会正在进行。这本来是一场例行的外交寒暄,专门为当时正在华盛顿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会议的各国科学家准备的。美国科学家们举着香槟,正忙着和同行们谈论美国的宏伟计划。
当时的剧本是这么写的:美国即将在几个月后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先锋号”。每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在那个年代,美国就是科技的代名词,这就像大家都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一样自然。

《纽约时报》的记者沃尔特·沙利文也在现场,他正试图从一位苏联天文学家嘴里套点话。突然,使馆的新闻官匆匆走过来,趴在沙利文耳边低语了几句。
那一瞬间,沙利文的脸色变得比杯子里的白葡萄酒还难看。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房间,著名的美国物理学家劳埃德·伯克纳被人猛拍了一下肩膀。有人把他拉到电话机旁。电话那头是《纽约时报》编辑部打来的,声音急促得像机关枪:“俄国人发声明了。塔斯社刚刚宣布,他们把一个球送上天了。它在轨道上。它正在绕着地球转。每96分钟一圈。”
伯克纳挂了电话。他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但此刻他的手有点抖。他走回人群,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
“先生们,”他的声音在颤抖,“我想我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就在此时此刻,有一颗苏联卫星正在我们顶上呼啸而过。”
那一瞬间,宴会厅死一般的寂静。
美国科学家们的笑容僵在脸上,就像是被瞬间冻住的蜡像。这不仅仅是尴尬,这是羞辱。几个小时前,他们还在把苏联人当成只会种土豆、造拖拉机的人;几个小时后,他们却把一个能发出“哔——哔——”无线电信号的金属球,挂在了美国人的头顶。
最要命的不是那个球本身。那玩意儿只有83.6公斤重,除了像个过分勤奋的报时鸟一样约每1秒发一次信号外,什么也干不了。

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是逻辑推导:既然他们能把83公斤的东西扔进轨道,那只要稍微改一改参数,他们就能把几吨重的核弹头扔到华盛顿。
那一晚,很多美国将军失眠了。他们望着窗外的夜空,总觉得有一只红色的眼睛在盯着他们看。
最讽刺的是,直到此时此刻,哪怕是CIA那个庞大的情报网,都不知道这个把美国吓尿了的“总设计师”到底叫什么名字。
古拉格里的“无名氏”
如果在1957年之前你在莫斯科大街上遇到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你绝对不会把他和“太空征服者”这种词联系在一起。
他这人:身材敦实,脖子短粗,很少笑,眼神阴郁得像西伯利亚的冻土。他总是歪着脑袋看人,那是当年在古拉格劳改营里被狱警用玻璃水瓶砸断下巴后留下的后遗症。因为下巴愈合得不好,他甚至没法把嘴张大,这导致后来他做手术时插管插不进去,直接死在了手术台上。当然,那是后话。
在这个时间点,他没有名字。
在苏联的所有官方文件中,他被称为“首席设计师”(Glavny Konstruktor)。这既是荣誉,也是枷锁。克格勃给他的安保级别高得离谱,出门有卫队。西方情报机构只知道苏联有一个幽灵般的人物在主导导弹计划,但连他是男是女都拿不准。

科罗廖夫是个天才,但他的老板——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什么星辰大海、人类未来根本不感兴趣。
赫鲁晓夫感兴趣的只有一样东西:能打到美国的洲际导弹。
1957年初,科罗廖夫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负责研发的R-7火箭(就是后来著名的“联盟号”的前身)是个脾气暴躁的怪物。这东西大得离谱,捆绑了四个助推器,看着像个巨大的金属章鱼。

前几次试射都不顺利。赫鲁晓夫的耐心快被磨没了。
这时候,科罗廖夫玩了一手漂亮的“偷梁换柱”。
在那次决定命运的汇报会上,科罗廖夫并没有大谈特谈什么科学探索。他太懂这些政治家了。他凑到赫鲁晓夫跟前,用那种诱惑的语气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能飞越大洋的火箭。既然我们要测试它的射程,为什么不顺便……就在顶上放个小玩意儿呢?”
“什么小玩意儿?”赫鲁晓夫漫不经心地问。
“一颗人造卫星。”科罗廖夫赶紧补充,“美国人一直在嚷嚷着要发射卫星。如果我们抢在他们前面,这就是科学的胜利。“
听到“羞辱美国”这几个字,赫鲁晓夫的眼睛亮了。

“只要不耽误导弹的正事,你就去弄吧。”赫鲁晓夫挥了挥手,就像打发一个想买糖吃的孩子。
拿到了“尚方宝剑”的科罗廖夫回到设计局,发现麻烦才刚刚开始。
原本计划中的卫星是个大家伙,里面装满了各种复杂的科学仪器,代号“D物体”。但这玩意儿太重了,而且那群搞仪器的科学家磨磨蹭蹭,等到他们把仪器调试好,估计美国人的卫星早就上天了。
时间来不及了。间谍传来消息,美国的卫星计划虽然也是一团乱麻,但随时可能成功。
科罗廖夫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极其粗暴的决定。
“去他妈的科学仪器!”他在办公室里咆哮,唾沫星子乱飞,“把所有复杂的玩意儿都拆了!我们只要一个球!一个能发声的球!”
这就是代号PS-1(简单卫星1号)的由来。
没有盖革计数器,没有太阳能电池板,甚至没有像样的数据记录设备。它就是一个直径58厘米的铝合金球体,里面塞了两台无线电发射机和几块大得吓人的电池。为了防止过热,还加了个风扇。就这么简单。
但科罗廖夫对这个球的外观有着近乎变态的执着。他要求工程师把铝合金外壳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光亮。

“为什么要这么亮?”工程师不解,“到了太空又没人看得见。”
“为了反光。”科罗廖夫阴沉着脸,“我要让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能在夜空里看见它。我要让它像星星一样亮。”
其实他心里清楚,这不仅仅是为了反光。这是一种仪式感。这是人类制造的第一个天体,即使它是个只会哔哔叫的空心铁球,它也必须完美得像件艺术品。
1957年10月4日深夜,拜科努尔发射场。R-7火箭矗立在寒风中,喷着白气。
科罗廖夫站在掩体里,手里捏着那枚决定生死的钥匙。如果这次失败了,这枚火箭不仅会把他炸成灰,还会把他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他可能会再次回到古拉格,这次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
“点火!”
巨大的火焰吞噬了发射台。R-7火箭缓缓升起,仿佛在那一刻,它摆脱了苏联沉重的重力,也摆脱了冷战的泥潭。
几分钟后,地面接收站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有节奏的、尖锐的声音。
“哔——哔——哔——”
发射成功了。
被受限性安置在阿拉巴马的人
就在科罗廖夫在哈萨克荒原上发射火箭成功的同时,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亚拉巴马州,一个叫亨茨维尔的小镇上,有个德国人气急败坏了。
他叫沃纳·冯·布劳恩。

在1957年,他的处境非常尴尬。
冯·布劳恩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麻烦。二战期间,他为希特勒造出了V-2导弹,把伦敦炸得七荤八素。战败前夕,他带着几百名顶尖科学家和整火车的图纸,主动向美军投降。美国人虽然如获至宝(“回形针行动”),但心里一直犯嘀咕:用纳粹党卫军造出来的火箭送美国卫星上天?这听起来政治很不正确。
所以,冯·布劳恩和他的团队被受限性安置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亨茨维尔,也就是红石兵工厂。
在这里,他造出了“木星-C”火箭。这玩意儿实际上就是改良版的V-2,皮实耐操,劲大管饱。

早在1956年9月,也就是斯普特尼克上天的一年前,冯·布劳恩就进行了一次“木星-C”的试射。
那天,火箭飞得非常完美,高度达到了1100公里,速度达到了2.6万公里/小时。冯·布劳恩站在控制室里,心里跟明镜似的:只要在顶端再加一级小火箭,把那个该死的死重换成哪怕一只柚子,这玩意儿就能入轨。
人类第一颗卫星本该是美国的。
但五角大楼不想看到这一幕。
就在发射前,华盛顿发来一道死命令:哪怕是上帝亲自来求情,这枚火箭也不准入轨!为了确保这群“疯狂的德国佬”不搞鬼,陆军甚至派人专门检查了火箭的最上一级。
结果,冯·布劳恩被迫在火箭鼻锥里灌满了沙子。对,你没听错,沙子。
历史上最荒诞的一幕出现了:美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技术,却在那一年里,费尽心思地防止自己把卫星送上天。
为什么?除了刚才说的“纳粹身份”洁癖外,还有一个更可笑的原因:军种内斗。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个战争英雄,但他对太空这事儿看得挺淡。他觉得既然要发卫星,那是为了搞科学研究,那就得用“平民化”的火箭。

海军这时候跳出来了,说:“选我!选我!我们的‘先锋号’(Vanguard)火箭完全是为科研设计的,根正苗红,没有德国纳粹的臭味!”
哪怕“先锋号”当时连个像样的图纸都还没画利索,哪怕它的技术极其不成熟,艾森豪威尔还是拍板了:让海军去干。
冯·布劳恩就像一只被拴在链子上的斗牛犬,眼睁睁看着海军那帮人在泥坑里打滚,自己却只能在亨茨维尔的办公室里画图纸。
10月4日晚上,消息传来苏联发射卫星的时候,正在亨茨维尔接待新国防部长的陆军少将梅达里斯(冯·布劳恩的顶头上司)脸都绿了。
冯·布劳恩冲进会议室,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保持德国式的优雅,而是像个被抢了玩具的孩子一样咆哮:
“我们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我们一直在求你们让我们干!如果是我们,一年前就搞定了!”
他转过身,死死盯着在这场灾难中唯一能做主的人——刚上任的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这哥们儿之前是宝洁公司卖肥皂的)。
“部长先生,”冯·布劳恩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把那种愚蠢的政治偏见扔进垃圾桶吧。给我60天。只要60天,我就能把这该死的耻辱洗刷掉。”
麦克尔罗伊看着眼前这个激动的德国人,又看了看窗外漆黑的夜空。他知道,华盛顿那帮老头子现在的脸肯定疼得厉害。
但他还是不敢立刻答应。毕竟,海军的“先锋号”还要在12月进行第一次正式发射。那是美国的官方门面,要是现在换人,岂不是承认之前的决策全是狗屎?
比珍珠港时刻更糟的灾难
美国人喜欢用“珍珠港时刻”来形容突如其来的灾难,但斯普特尼克的出现,对美国公众心理的打击比偷袭珍珠港还要阴毒。
珍珠港被炸了,大家看到的是浓烟和残骸,大家知道敌人是谁,在哪,怎么打回去。但斯普特尼克呢?它是无形的,它在头顶。
第二天早上,当美国人拿起报纸,看到的不再是棒球比赛或者好莱坞八卦,而是满版刺眼的头条:《赤色月亮悬空!》、《苏联卫星正在监视美国!》。
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惧迅速蔓延。在克利夫兰,有老太太打电话给警察局,说她感觉到了某种“外星射线”让她的关节炎更疼了。在五金店,望远镜被一抢而空,大家都想亲眼看看那个该死的球。
最会煽风点火的是政客。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后来接替肯尼迪的那位)直接跳上了桌子。他在演讲中用那种极具德州风味的夸张语调喊道:
“我们要完蛋了!他们能从上面扔石头下来,他们能控制天气,这一秒是晴天,下一秒苏联人就能让德州下暴雪!”

虽然从科学角度看这些全是胡扯,但老百姓听得一愣一愣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宫的主人。作为二战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其实比谁都冷静。他手里有U-2侦察机的照片,他知道苏联并没有宣称的那么强大,所谓的“导弹差距”其实是苏联人吹出来的牛。他觉得那就是个小球,没必要大惊小怪。
在一次发布会上,记者问他对此是否担忧。艾森豪威尔耸耸肩,轻描淡写地说:“这完全没有引起我一丝一毫的忧虑。”
坏就坏在这个“一丝一毫”。
老百姓不想看总统装酷,他们想看总统抓狂。他们觉得总统老糊涂了,甚至有人开始怀疑美国是不是真的已经沦为二流国家。
这种社会压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高压锅,所有的蒸汽都喷向了一个出口:海军的“先锋号”。
“只要我们的卫星上天,哪怕比苏联人晚两个月,至少能证明我们不是傻瓜。”
这就是当时美国人的想法。于是,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12月6日。
“卡普特尼克”的尴尬表演
1957年12月6日,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
这不仅仅是一次发射,这是一场全美直播的真人秀。成百上千名记者架着摄像机围在发射场周围,甚至连好莱坞的明星都来了。美国政府太渴望一场胜利了,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度宣传。
“先锋号”火箭立在发射台上,又细又长,比起苏联那个粗壮的R-7,它看起来就像个精致的牙签。
倒计时开始了。
“三、二、一、点火!”
火焰喷射而出,火箭缓缓离地。人群开始欢呼,记者们开始敲打打字机。
火箭上升了大约……两秒钟。
也就是离地大概两英尺(约60厘米)的高度。
然后,仿佛是失去了动力,火箭重重地摔回了发射台。
“轰!”
巨大的火球吞没了整个发射架。燃料箱爆炸,鼻锥飞了出去。最滑稽的是那个“先锋号”卫星。它从烈火中滚落出来,掉在旁边的草丛里,居然没有坏。它顽强地继续发着信号,就像一只被踢了一脚还在叫唤的吉娃娃。
那一刻,全世界都笑得喘不过气来。
伦敦的《每日快报》给出了那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标题:《Oh, What a Flopnik!》(哦,多么失败的尼克!)。
接着,各种刻薄的绰号铺天盖地而来:
Kaputnik(完蛋尼克);
Stayputnik(呆住尼克);
Dudnik(哑弹尼克)。
在联合国,一位苏联外交官甚至假惺惺地问美国代表:“美国是否需要苏联对其落后的航天技术提供一点技术援助?就像对待其他欠发达国家那样?”
这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公关自杀。艾森豪威尔的脸被打肿了,海军的将军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就在这片废墟和嘲笑声中,国防部的电话终于打到了亨茨维尔。
这是冯·布劳恩一直等待的声音。
放德国人出来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冯·布劳恩并没有表现出狂喜。他只是冷冷地对他的团队说了一句:“好了,孩子们,别玩了,该干活了。”
但他面临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
因为就在美国人忙着炸自己的火箭时,苏联人又搞了个大新闻。11月3日,就在斯普特尼克1号上天不到一个月,科罗廖夫发射了斯普特尼克2号。
这次不是一个小球,而是一个重达半吨的庞然大物。更恐怖的是,里面坐着一只叫“莱卡”的流浪狗。

虽然莱卡在进入轨道几小时后就因为过热死去了(苏联人当时撒谎说它活了一周),但这释放了一个极其恐怖的信号:既然能把半吨重的东西送上去,那就意味着苏联的洲际导弹能把任何东西扔到美国本土。
冯·布劳恩的时间不多了。他之前吹牛说要60天,现在军方真的只给他60天。
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需要帮手。
火箭是现成的,那是他的“木星-C”(后来改名叫“朱诺1号”),但他还需要一个卫星。他找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
那里有一个叫威廉·皮克林的新西兰人和一个叫詹姆斯·范·艾伦的物理学家。
这三个人组成了临时的“复仇者联盟”。
皮克林负责造卫星外壳,范·艾伦负责里面的科学仪器(虽然只有几公斤重,但他塞进了一个盖革计数器),冯·布劳恩负责把这玩意儿送上去。
那个冬天,亨茨维尔和帕萨迪纳(JPL所在地)的灯光彻夜未熄。他们没有电脑辅助设计,甚至连计算轨道都要靠一群女计算员手摇计算机来算。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豪赌。如果冯·布劳恩也失败了,美国人真的可能要在这个星球上抬不起头了。
那个举起火箭的人
1958年1月31日,深夜。
这一次,没有直播,没有记者团。为了避免再次丢脸,军方封锁了消息。整个发射过程都在一种令人窒息的低调中进行。
冯·布劳恩甚至不在现场。他被军方强行按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里“听消息”,以防万一失败了,有人能立刻给大人物们解释为什么。
在卡纳维拉尔角,只有皮克林和负责发射的库尔特·德布斯。
“点火!”
朱诺1号火箭怒吼着升空。这一次,它没有爆炸。它像一只离弦的箭,刺破了佛罗里达的夜空,钻进了大气层。
但最煎熬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火箭虽然飞走了,但没人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入轨了。当时没有全球覆盖的雷达网。他们必须等待。等待火箭绕地球一圈后,重新出现在加利福尼亚的地震谷(Goldstone)接收站的信号范围内。
按照计算,信号应该在发射后106分钟出现。
大家都在等。冯·布劳恩在华盛顿喝着冷掉的咖啡,手心全是汗。
106分钟过去了。没有信号。
107分钟。寂静。
108分钟。还是寂静。
有人开始叹气了。是不是又失败了?是不是掉进海里了?
直到第109分钟。
加州的电传打字机突然疯狂地跳动起来。
“Goldstone has the bird!(戈德斯通抓到那只鸟了!)”
原来,冯·布劳恩的火箭推力太大,把卫星推得比预定轨道更高,所以它多花了几分钟才绕回来。
“探险者1号”成功了。
这一刻,没有像苏联那样举国欢庆的游行,但在五角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一群老男人像孩子一样抱头痛哭。
紧接着,那张经典的照片诞生了: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冯·布劳恩、皮克林和范·艾伦三个人,像举起奖杯一样,把那个像擀面杖一样的卫星高高举过头顶。

范·艾伦笑得最开心,因为他的盖革计数器发回了数据,发现了环绕地球的辐射带(后来被命名为“范·艾伦辐射带”)。这是人类在太空时代的第一个重大科学发现。
起跑线上的枪声
就在那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成千上万的美元被砸进了学校,只为了让美国孩子能学会微积分,别输给苏联孩子。
几个月后,一个叫NASA(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机构成立了。
而在铁幕的另一边,那个没有名字的科罗廖夫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看着美国人追上来的身影,只是轻轻哼了一声。在他的案头,已经摆着下一张图纸。那是一个能把活人送上去的更大的东西。
他已经在物色那个将要被写进历史的人选了。听说空军有个叫尤里·加加林的小伙子,笑起来挺好看的。

美苏太空竞赛的起跑枪才刚刚打响。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这两个大国在这片星辰大海里,上演人类历史上最疯狂、最烧钱、但也最浪漫的追逐战之一。
正如冯·布劳恩后来所说:“我们在太空中学会了如何去恨,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那里学会如何去爱。”
但在1958年的那个春天,没人想什么爱不爱的。大家只想一件事:
快!比那个该死的混蛋飞得更高一点!
免责提示:本文基于公开历史资料与技术文献整理,部分细节为叙事化演绎,仅供科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