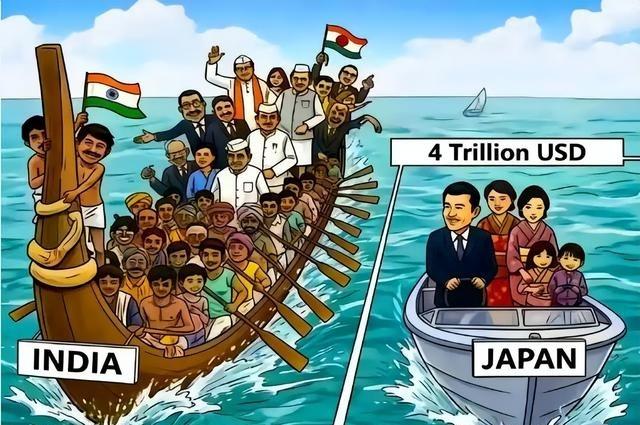印度的国家元首常年隐身,行政实权尽归总理掌控。
单从头衔来看,印度总统的分量似乎重若千钧——身为国家元首兼三军最高统帅,头顶着国家最高荣誉的光环,可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这一职位更像是一件精致的礼仪摆设。
与总统的产生方式不同,普通民众并没有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的权利,总统职位由联邦议会及各邦立法机关选举产生的议员共同投票选出,每五年举行一次换届选举。
就拿现任总统德劳帕迪·穆尔穆来说,2022年7月25日正式就职时曾引发全国性的关注热潮,因为她不仅是印度首位女性部落总统,其来自奥迪沙邦的部落背景更象征着边缘群体的政治突破,这样的历史意义让相关新闻连续多日占据媒体头条,但热潮褪去后,她便迅速回归低调,淡出了公众的核心视野。
总统日常公开露面的场合早已形成固定范式:出席各类活动的开幕式、签署议会通过的法案文件、偶尔以国家象征身份出国访问,即便在这些有限的场合中,每一个环节的流程和内容也都必须遵循内阁的安排,丝毫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

印度宪法第74条有着明确规定,总统行使职权必须依据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建议,说得直白些,就是莫迪领导的内阁团队提供什么方案,总统便负责盖章确认,完成形式上的生效程序而已。
与总统的象征性角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理才是印度政坛真正掌控局势的核心人物。
莫迪自2014年首次出任总理,2019年成功实现连任,到2024年6月9日第三次宣誓就职,已经稳坐总理宝座超过十年,这样的执政稳定性绝非偶然。
尤其在2024年开启的第三任期内,即便印度人民党未能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需要联合其他政党组成联盟政府,莫迪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执政姿态,从未显露丝毫慌乱。
从重大经济改革的推进到关键外交谈判的落地,所有核心政策的制定与拍板都由他亲自定调,印度近年来的发展轨迹上,几乎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深深镌刻着莫迪的印记。
内阁的核心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理一人之手。

内阁会议由总理亲自主持,国家预算的分配方案由总理最终敲定,即便涉及国防部署这样的敏感事务,也只有总理办公室拥有最终决策权。
2025年1月31日,总统穆尔穆按照惯例在议会预算会议前发表致辞,在讲话中强调印度政府的效率已实现三倍提升,这番表态看似是总统对政府工作的肯定,实则不过是按照内阁提供的纲要,为总理团队的施政成果背书造势。
在具体政务操作环节,总统与总理的权责划分更为清晰——穆尔穆只需在预算会议上完成形式上的预算书递交仪式,转身之后,预算案的辩论、修改以及后续的执行工作,便全部交由总理办公室统筹处理,总统彻底沦为"仪式感担当"。
这种角色分工在议会制政体中并不罕见: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专注于礼仪性工作,而国家治理的实权则牢牢掌握在实际操盘的政府首脑手中。
回溯印度的制度设计源头便会发现,1950年颁布的印度宪法早已奠定了这样的权力格局,宪法制定者刻意限制了元首的实际权力,避免出现个人独裁的风险,转而确立了集体决策的核心原则。
议会制政体的核心要义便是责任共担,政府首脑及其团队必须获得议会多数派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一旦失去议会信任,便会面临立即倒台的风险,这种机制从根本上决定了总理必须成为政策的核心制定者。
过去十年间,只要提及印度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高铁网络投资或是全民疫苗接种计划,这些标志性成就的背后必然贴着"莫迪标签",从未有任何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是由总统亲自挂帅推进的;相反,2025年上半年穆尔穆出访非洲期间,即便签署了若干合作协议,也多以文化交流、民间友好等象征性领域为主,真正涉及大额贸易的核心协定根本轮不到她介入,那些关键合作早就在G20峰会等重要场合由莫迪提前敲定。

这样的权力安排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现实逻辑,印度地域辽阔,宗教信仰多元,民族构成复杂,若让缺乏议会支持的总统介入实际治理,极易引发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而总理由议会多数党推举产生,拥有坚实的民意基础和政党支撑,在推行政策时自然更具权威性。
比如莫迪开启新任期后,立即着手调整内阁阵容,将边防安全与数字化转型列为重点工作方向,这样的决策速度之快,让反对党根本来不及反应,相比之下,总统参与的剪彩、慰问等仪式性工作,根本无法引发媒体和公众的持续关注,所有全媒体镜头的焦点,都自然而然地围绕着总理这一核心人物转动,这既是制度设计的结果,也是复杂国情下的现实需求。
归根结底,宪法与制度的规矩早已将总统的权力框定得明明白白:即便宪法赋予总统赦免罪犯、宣布紧急状态等权限,但这些纸面权力的行使必须经过内阁同意才能生效,哪怕是解散人民院或批准国际条约这样的重大事项,总统也只是按部就班完成程序,没有任何自主决策的空间。
即便穆尔穆偶尔获得公开亮相的高光时刻,比如主持公务员培训大会时提及Adi Karmayogi计划,也无法改变权力的本质格局——该计划的整体框架和实施细则,早在几年前就由莫迪总理牵头制定并推进落地,总统的发言顶多算是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补充几句表态,做些收尾性的总结而已。
在国际舞台上,这种权力分工同样清晰可见,2025年天津上合组织峰会上,能源合作等核心议题的谈判虽由各国外长先行沟通铺垫,但最终的关键决策仍需莫迪亲自出面敲定——等到合作协议正式生效时,穆尔穆只需发布一封贺电表示祝贺,点到为止即可,无需也不能过度参与。
在司法领域,总统虽拥有咨询最高法院的权利,但这种咨询仅停留在顾问层级,根本无法影响司法判决的最终走向。
这种元首虚位、总理实权的模式,与美国的总统制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掌握着核心行政权力,甚至拥有否决国会法案的权力;而在印度,包括德国、新加坡等采用议会制的国家都遵循着类似的逻辑,通过明确的权责分工避免"一言堂"的出现,防止制度运行出现偏差。
1975年印度实施全国紧急状态的历史事件便是典型例证,当时紧急状态虽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但幕后的实际推动者却是政府核心圈层,总统只是履行了形式上的程序。
紧急状态结束后,印度对相关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但元首虚位、总理实权的核心结构从未改变,一直延续至今并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