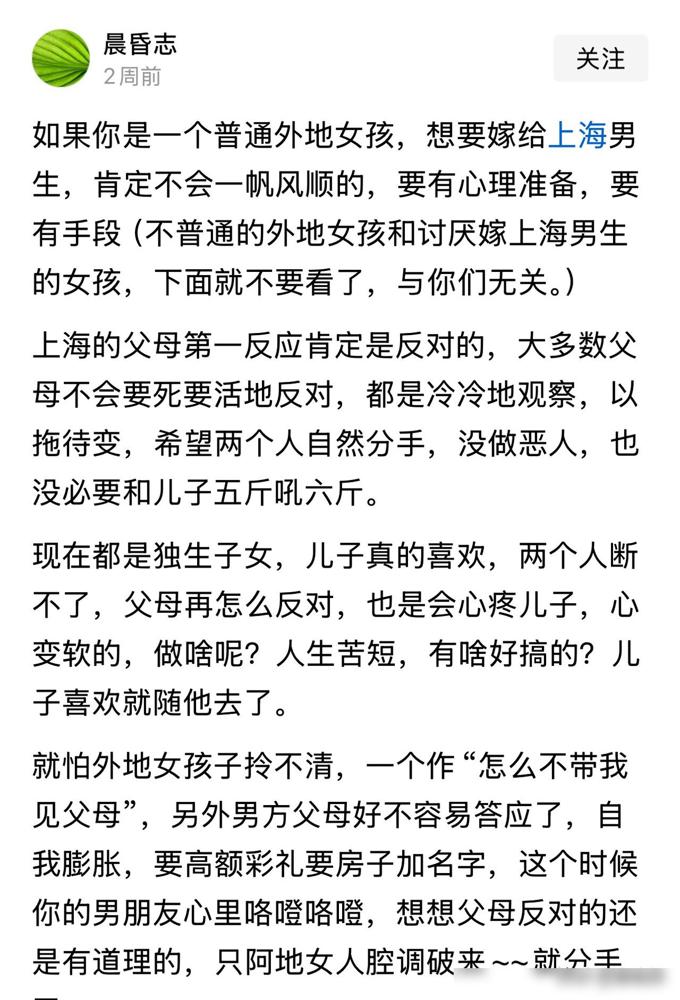我二妹是一个住家保姆,她是一个市场上不流通的保姆,是因为她来上海以后就在一户人家工作,从来没有在第二户人家做过保姆,二妹在这户人家已经工作了9年。 陈叔叔走后这几年,家里就真的只剩她和林阿姨了。客厅那台老电扇,每到夏天就吱呀吱呀地转,像在替谁叹气。日子一天天过,二妹以为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直到上个月,林阿姨夜里起床上厕所,脚下软了一下,没摔着,但吓着了。第二天,她儿子就从苏州赶回来,这次态度很坚决,说必须接走。二妹在厨房切菜,听见他在客厅说:“妈,您这岁数一个人住,我能放心吗?二妹再好,也是外人。” 二妹手里的刀停了一下。窗外的天色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那天晚上,林阿姨把二妹叫到跟前,没说话,先递过来一个厚厚的红包。“这钱你拿着,”林阿姨声音很轻,“不是工资,是路费。你……你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 二妹没接。她看着林阿姨床头柜上陈叔叔的照片,照片边角都磨得发亮了。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第一次用洗衣机,把陈叔叔一件衬衫染了色,吓得不行,陈叔叔却笑着说:“正好,想换件新的了。” “阿姨,”二妹开口,嗓子有点紧,“小刚……我儿子,他在学校附近租好房子了。合租的,便宜。”她顿了顿,“他说,我要是不想干了,可以去他那儿住段时间。” 林阿姨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那好,那好……”她喃喃道,手无意识地搓着睡衣的扣子。 接下去几天,家里格外安静。二妹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其实就一个小箱子。林阿姨则整天坐在阳台那把旧藤椅上,看着陈叔叔留下的那几盆茉莉花。 临走前一晚,二妹照例给林阿姨热了牛奶。林阿姨接过去,忽然说:“你等等。”她慢慢走到自己房间,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些旧照片。她翻出一张二妹刚来那年,三个人在客厅的合影。那时候二妹还扎着两条麻花辫,笑得怯生生的。 “这个,你拿着。”林阿姨把照片塞进二妹手里,“想我们了,就看看。” 第二天早上,二妹拎着箱子走到门口。林阿姨执意要送她到电梯口。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二妹看见林阿姨还站在那里,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朝她轻轻挥了挥。 电梯下行,手机亮了一下,是小刚发来的消息:“妈,到了吗?我给你熬了粥。” 二妹看着电梯镜面里自己的脸,九年光阴,都刻在上面了。她深吸一口气,按下一楼的按钮。铁门缓缓打开,外面是阴天,风有点凉,但街道上车水马龙的声音涌进来,充满了陌生的、鲜活的气息。她握紧了手里的箱子拉杆,迈步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