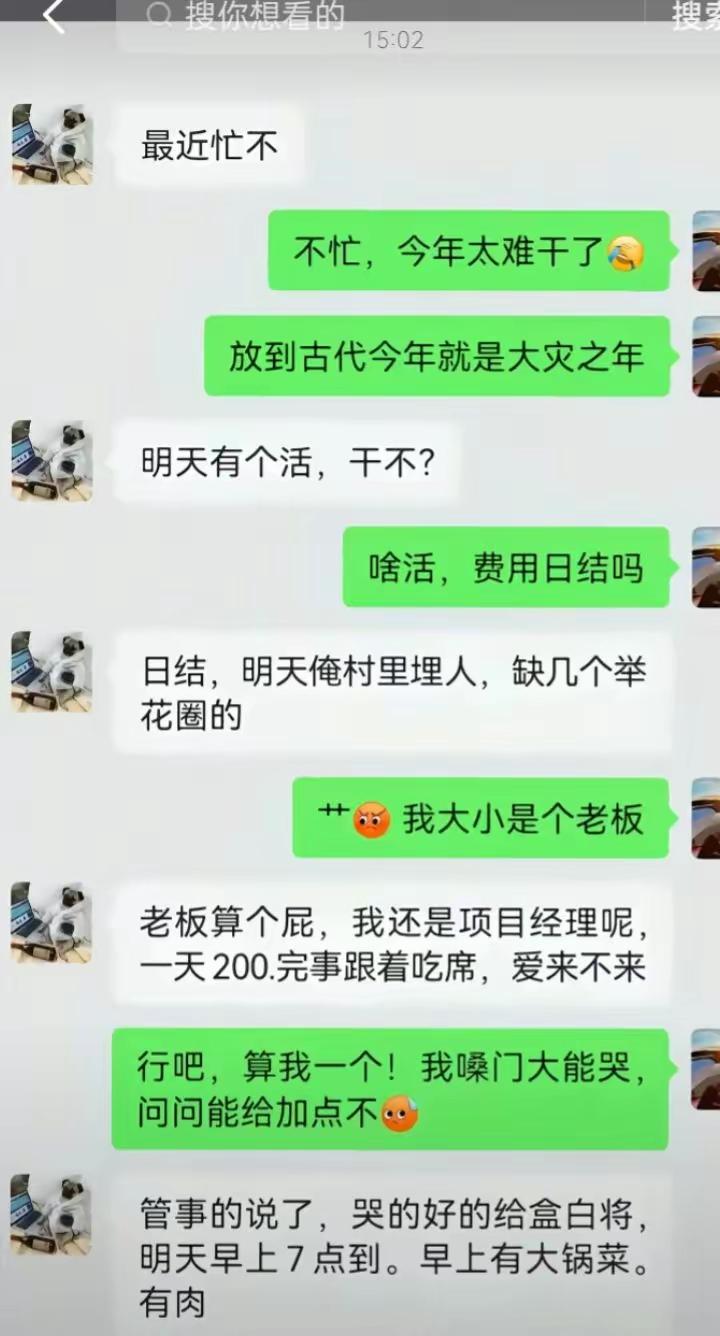郭选荣做的绣花鞋。

新平百岁老人郭选荣。
□玉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饶平文/图
金秋十月的一天,在新平县古城街道阿秀小区里,102岁的郭选荣老人安坐在竹椅上,指尖轻搭扶手。午后的阳光裹着暖意,漫过窗台上的蕨类叶片,落在老人的红帽檐上。她向记者说起年轻时骑马上山摘黄泡的往事,眼尾纹的褶皱里便漾开细碎的光。这位生于1923年的百岁老人,把一生种种的艰辛与安逸,都融入平和恬淡的讲述中。
做了大半辈子鞋
1923年,郭选荣生于新平县扬武镇的一个富足之家。私塾里的诗书墨香浸透了她的少女时光,后来因病辍学,却也算略通文墨。22岁的她嫁给一个叫可光的男人,24岁生下儿子可顺清,怎料儿子三岁时丈夫病逝。临终前,丈夫嘱托:“好好带着这个孩子,他长大后会养你的。”这句话成了她一生的锚。
“奶奶从小家境殷实,出门去哪儿都骑马。”孙女可焕玲回忆说,“她上山摘黄泡也是骑着马去的。”那个绣花骑马、裁衣做鞋的妇女,在丈夫离去后挽起发髻,把锦瑟年华封存在旧时光中。从此,她的针尖挑破晨昏,细线缝补岁月。
1969年,郭选荣的大孙女可焕玲出生时,她已做了大半辈子鞋。布底鞋、胶底鞋、羊皮底绣花鞋……孙辈的脚丫都是在她做的一双双鞋子里长大的。“最早是布底,后来捡废旧轮胎做胶底。”可焕玲抚摸着竹篮里簇新的绣花鞋说,“奶奶做的鞋,头小小的,针脚密得像女人的心事。”
那些年的夜晚,油灯总是亮到三更。可焕玲记得,奶奶的指尖总缠着线,她们的鞋、衣服都是奶奶熬着夜做的。冬日的冬瓜被郭选荣熬煮成蜜饯,花生炒得酥脆,裹着甜香塞给孙辈;年关杀年猪,她要忙上足足三天,灌香肠、腌腊肉,让寡淡的日子浸满烟火气。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郭选荣捡菜叶腌渍,把清贫日子过出了滋味。
家族记忆里的“光”
94岁前,郭选荣常把绣花鞋送到可焕玲开的“小玲绣坊”。因为是老人亲手刺绣制作,鞋子一送到店里就被抢购一空。可焕玲把卖鞋的钱交到她手里,她能高兴好几天。她常说:“不是为钱,是觉着自己还有用。”后来可焕玲不再卖鞋,便将奶奶做好的那些点缀碎花、盘金线的绣鞋收作传家宝。可焕玲说:“奶奶把生活的温馨,都融进了针线里。”
令人惊叹的是郭选荣的矫健。她80多岁仍能梳理长辫,辫子剪下后还卖了20多元;她能上树摘果,惊得儿孙连连劝阻。可焕玲说:“奶奶以前打秋千能飞起来,磨秋也甩得高高的。”那些飞旋的身影与蜜糖的香甜,成了家族记忆里的“光”。
儿子可顺清60岁离世时,郭选荣的天地裂开一道缝。她常独自哭泣,哭够了便抹泪站起说:“哭出来,心里就轻松了。”家人曾带她上坟,她在山间大哭一场后,再不忍去。可焕玲说:“自从我爸爸走后,奶奶还种菜卖菜,92岁才歇下。”
糖是郭选荣一生的慰藉。“奶奶说靠糖养着命。”可焕玲笑道,“如今全家人爱吃糖,都是受奶奶的影响。”生活中,即便饭馊了郭选荣也舍不得扔,放上腌菜炒了吃。她对凉卷粉的念想从不含糊,总会催着孙辈去街上端来吃。那是郭选荣一生不容商量的任性。
郭选荣的旧物里有个深褐色的皮首饰盒,搭扣蒙着岁月的锈迹。打开盒盖,暗绿的衬布沾着细碎红痕,似藏着说不尽的心事。空盒盛满时光,与绣花鞋一起,成了她一生的隐喻。
时光里的长情之人
前几年,郭选荣老人的腿跌伤后,再也不能逛街,却求孙辈推她出门。她总是说:“我要出去看看人。”从前在生产队,她挣工分从不落后;晚年被困轮椅中,仍要触摸人间烟火。
“奶奶最会生活。”可焕玲说。这种“会”,是秋千飞起时的胆魄,是炒馊饭时的惜物,是绣鞋换钱时的骄傲,更是握紧儿孙手时的沉默与温柔。
秋日的午后,郭选荣仍靠坐在竹椅上,看阳光掠过窗台上的绿植,指尖偶尔碰一碰喷壶。“这花今早刚浇过水。”她缓缓地说着。风裹着草木香进来,掀动她的红色衣角,时光便在这温柔里成了长情的模样——她把苦日子缝成了“甜”,把岁月织成了“暖”,她的一生活成了一本摊开的书,每一页都闪烁着晶莹的光。她不曾读过万卷书,却用百岁光阴写就生活真谛:生命不是熬煮苦药,而是冲泡陈茶——淡如清风,余味绵长。百岁老人那些针脚、糖果、泪痕与欢笑,最终织成一束暖光,照亮寻常日子里的永恒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