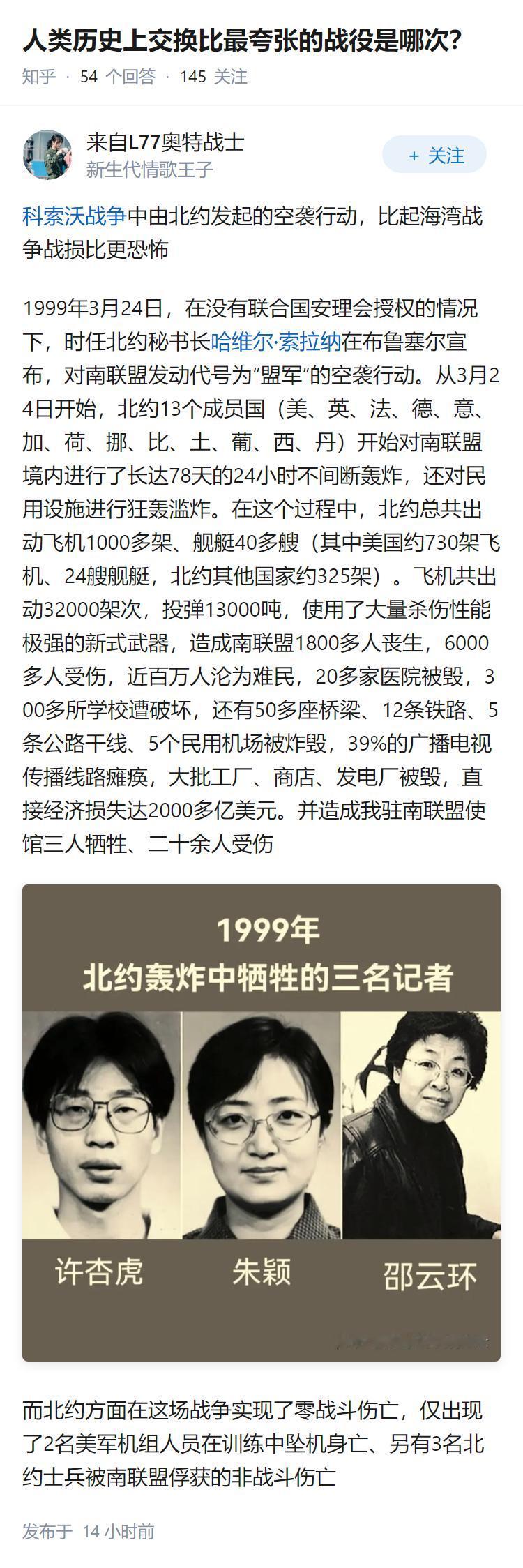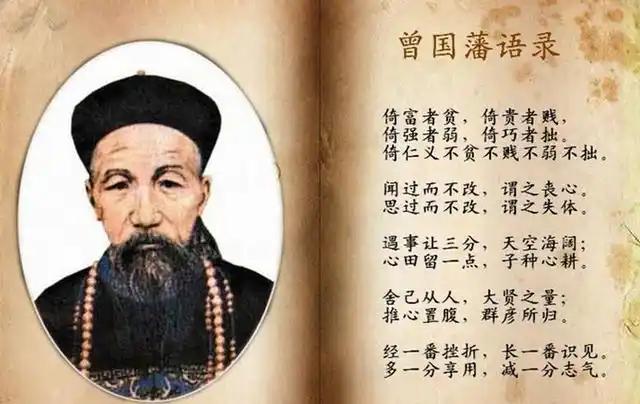提到儒家,很多人会先想到“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仿佛它天生带着“压抑”的标签。但很少有人知道,儒家并非一成不变的“古板学说”,从春秋到清末,它像一棵不断生长的大树,根系扎进不同时代的土壤,枝叶也跟着长出不同模样。要理解它为何会让人感到压抑,得先看清这棵“大树”两千年的进化轨迹。

儒家的起点,其实充满“人文温度”。春秋时期,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乱世,提出“仁”的核心思想,不是要求人压抑本性,而是教人们“爱人”“克己复礼”。这里的“克己”,是克制过度的欲望,比如不抢夺、不暴虐,而非压抑正常的情感;“复礼”也不是死板守旧,而是希望用“君臣有义、父子有亲、朋友有信”的秩序,让社会少点混乱。孔子甚至认可普通人的欲望,说“食色性也”,还鼓励学生“各言其志”,此时的儒家,更像一套“教人好好做人、社会好好运转”的生活指南,全无后来的压抑感。

到了战国,孟子给儒家注入了“刚劲”,却也埋下了“约束”的种子。孟子继承“仁”,进一步提出“仁政”,主张君主该善待百姓,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普通人的地位抬得很高。但为了让“仁”落地,他开始强调“义”的重要性,比如“舍生取义”,认为人要为道德原则放弃个人利益。这本来是对道德的追求,可一旦走向极端,就容易变成“用道德绑架个人欲望”。不过此时的儒家,仍保留着“人性本善”的乐观,还没到压抑人的地步。

真正让儒家开始“变味”的,是西汉的“独尊儒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了迎合中央集权的需求,把儒家和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结合,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原本孔子说的“君臣有义”,是双向的责任,君要仁,臣才要忠;可“君为臣纲”变成了单向的服从,臣必须无条件忠于君,妻子必须无条件顺从丈夫。董仲舒还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家从“百家之一”变成“官方唯一学说”,失去了和其他思想碰撞的机会,开始朝着“为皇权服务”的方向靠拢,压抑的苗头就此埋下。

到了宋明时期,儒家彻底走向“内省压抑”。宋朝理学兴起,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为了对抗佛教、道教的影响,把儒家思想哲学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里的“天理”,指的是封建伦理秩序,比如君臣、父子、夫妻的等级;“人欲”则被窄化为“超出基本需求的欲望”,后来甚至演变成“所有个人欲望都是罪恶”。比如朱熹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求寡妇不能再嫁,把对女性的束缚推到极致;王阳明的“心学”虽然强调“致良知”,但也要求人不断“反省克制”,不能让私欲违背“天理”。此时的儒家,完全成了维护封建等级的工具,“压抑”也成了它最显眼的标签。

清末民初,儒家迎来“崩溃与重生”。随着西方思想涌入,封建王朝崩塌,“三纲五常”被当成落后的象征,新文化运动甚至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人们渐渐发现,儒家并非只有“压抑”的一面,孔子的“仁爱”、孟子的“民本”,和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平等思想”仍有契合之处。如今的儒家,不再是官方强制的学说,而是变成了文化符号,人们从其中汲取“尊师重道”“孝老爱亲”的正能量,同时抛弃了“压抑人性”的封建糟粕。

回头看儒家的进化史,它的“压抑”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不同时代为了满足统治需求,不断被改造、被固化的结果。从孔子的“爱人”到朱熹的“灭欲”,从“生活指南”到“统治工具”,儒家的命运和封建王朝绑在一起,也跟着染上了封建制度的“压抑病”。如今剥离了封建外壳的儒家,终于又找回了最初的人文温度——这或许才是它能流传两千年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