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乱世,群雄逐鹿,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瓦岗军的兴衰。李密凭借过人谋略,将翟让创立的瓦岗军打造成拥兵20万、占据三大粮仓、云集秦琼、徐世勣、程咬金等绝世名将的天下第一势力,巅峰时威震中原,连李渊都要暂避锋芒。
这样一支看似能问鼎天下的雄师,却在公元618年的邙山之战后一夜崩塌,李密从云端跌落泥潭,最终叛唐被杀,年仅37岁。手握王牌却满盘皆输,是时运不济,还是决策失误?
 潜龙在渊
潜龙在渊李密出身北周八柱国之后,妥妥的关陇贵族后裔,却因参与杨玄感谋反沦为亡命之徒。大业十二年(616年),走投无路的他投奔瓦岗军,谁也没料到,这个落魄贵族竟能让这支农民起义军脱胎换骨。
彼时的瓦岗军虽剽悍善战,却局限于劫掠运河商旅,缺乏长远规划。李密到来后,立刻展现出顶尖战略眼光:他先是献计奇袭荥阳,在大海寺设伏,斩杀隋军名将张须陁,一战成名,让瓦岗军威震河南;随后力主攻取隋王朝最大粮仓兴洛仓(洛口仓),这座可容纳两千四百万大石粮食的粮仓,成为瓦岗军崛起的关键。
攻占兴洛仓后,李密做出了最明智的决策:开仓放粮,不问身份,任百姓自取。消息传开,河南、山东一带的饥民蜂拥而至,“老弱幼童,道路不绝,多达数十万人”,瓦岗军兵力从数万猛增至二十余万,瞬间成为隋末起义军的绝对主力。
更关键的是,李密凭借“开仓赈民”的义举赢得民心,各地义军和隋军降将纷纷来投,秦琼、程咬金、罗士信等猛将就是在此时率部归顺,徐世勣、单雄信等核心将领也对其信服有加。
大业十三年(617年),翟让自知才能不及李密,主动让贤,李密被推举为“魏公”,建立政权,颁布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一时间“东至海,南至江”,各地郡县望风而降。瓦岗军随后又攻占回洛仓、黎阳仓,彻底切断洛阳隋军的粮道,对东都形成合围之势。此时的李密,手握20万大军、三大粮仓和一众名将,进可攻洛阳,退可守中原,俨然成为逐鹿天下的头号热门。
可就在瓦岗军如日中天之际,一场血腥的内斗,悄悄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自毁长城
自毁长城李密的崛起,离不开翟让的胸襟。但随着李密威望日隆,瓦岗军内部逐渐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李密带来的贵族嫡系和隋军降将,另一派是翟让起家的旧部,以翟让兄长翟弘、部将王儒信为首。
翟弘和王儒信野心勃勃,多次劝翟让:“你才是瓦岗军的创始人,为何要给李密当副手?应自任大冢宰,总领众务!”翟让虽拒绝了这番话,但消息传到李密耳中,本就对翟让旧部的骄横有所不满的他,心中生出了忌惮。
再加上李密的谋士房彦藻、郑颋从中挑拨,称翟让旧部“贪暴无度,恐为后患”,李密最终下定决心:除掉翟让,巩固权力。
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密以庆功为名设宴,席间突然发难,命人斩杀翟让、翟弘和王儒信。混乱中,翟让的心腹徐世勣被砍伤,单雄信吓得跪地求饶,才侥幸活命。李密虽事后安抚徐、单二人,将翟让旧部交给他们统领,但这场火拼彻底撕裂了瓦岗军的信任基础。
翟让待人宽厚,深得底层将士拥护,他的惨死让许多老部下心寒;徐世勣作为翟让最信任的将领,虽表面顺从,却始终对李密心存芥蒂;单雄信更是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为日后的临阵倒戈埋下伏笔。
更严重的是,李密经此一役,变得多疑猜忌,对旧部刻意疏远,反而厚待后来归顺的隋军降将,导致瓦岗军内部“新老不和,人心涣散”。
如果说火并翟让是瓦岗军的“内伤”,那么李密接下来的战略失误,则直接将这支大军推向了深渊。
 邙山惨败
邙山惨败大业十四年(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杀隋炀帝,率军北上,欲取洛阳回长安。此时洛阳由越王杨侗留守,与瓦岗军相持不下。面对宇文化及这个共同威胁,李密做出了第一个致命决策:接受杨侗的册封,向隋廷称臣,联合洛阳隋军夹击宇文化及。
这个决策看似明智,实则是饮鸩止渴。瓦岗军本是反隋义军,向隋廷称臣瞬间失去了“替天行道”的旗帜,民心士气受挫;更重要的是,与宇文化及的童山大战异常惨烈,瓦岗军虽最终获胜,却“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敝”,元气大伤。而洛阳的王世充趁机发动政变,掌控大权,成为瓦岗军新的劲敌。
此时的瓦岗军,经过连番恶战已疲惫不堪,将士们渴望封赏休整,但李密却被胜利冲昏头脑,变得骄傲轻敌。他拒绝了部下“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的建议,执意与王世充决战,甚至连军营壁垒都懒得修筑。
公元618年十月,邙山之战爆发。王世充早有准备,连夜派200余骑兵潜入北邙山埋伏,次日凌晨趁瓦岗军尚未列阵,突然发起猛攻。更致命的是,瓦岗军内部出现了叛徒:长史邴元真暗中勾结王世充,出卖军情;镇守偃师的守将也临阵倒戈,打开城门献城。
激战中,李密被流矢击中坠马,一度昏厥,瓦岗军群龙无首,阵型大乱。秦琼拼死护住李密突围,收拢残兵反击,虽暂时击退追兵,但瓦岗军已溃不成军。最让人痛心的是,单雄信因记恨李密杀翟让,坐拥重兵却按兵不动,坐视瓦岗军惨败。
此役,瓦岗军10余万人被俘,裴仁基、祖君彦等数十名将领被擒,秦琼、程咬金、罗士信等猛将被迫投降王世充,徐世勣则驻守黎阳,与李密失去联系。李密带着仅存的两万残兵逃至河阳,昔日的20万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入地狱。
 穷途末路
穷途末路邙山惨败后,李密陷入绝境:“欲守无粮,欲战无兵”,河北窦建德、河南王世充、关中李渊三足鼎立,他已无立足之地。部下劝他投奔黎阳的徐世勣,但李密因当年火并翟让时曾重伤徐世勣,担心其记仇,最终选择率残部西入关中,投降李渊。
李渊对李密的到来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封他为邢国公,赐婚表妹独孤氏,表面上极尽笼络。但李密很快发现,这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他空有“上柱国”、“光禄卿”的虚衔,却无任何实权,昔日的魏公如今要为唐廷的宴会安排膳食,受尽屈辱。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旧部秦琼、程咬金等人归顺李唐后,都得到李世民的重用,战功赫赫,而自己却被闲置,这让心高气傲的李密愈发不满。
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李渊命李密前往黎阳招抚旧部,实则想将他调离长安。李密行至桃林(今河南灵宝)时,终于忍无可忍,借口“献地”突然率部叛逃,企图穿越熊耳山投奔旧将张善相,图谋东山再起。
但李密的行踪早已被唐军察觉,唐将盛彦师在熊耳山设下埋伏,伐木堵路,待李密大军进入山谷后,乱箭齐发。一代枭雄李密中伏身亡,年仅37岁。他的首级被传至长安,李渊为显示宽宏,下令厚葬于黎阳山西南,由徐世勣主持葬礼。这位曾搅动天下风云的英雄,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结语
结语李密的悲剧,并非偶然,而是性格缺陷、战略失误和权力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手握20万大军和顶级名将,却落得一败涂地,核心原因有三:
1. 内斗失人心:火并翟让埋下祸根
翟让虽无争霸天下的谋略,却是瓦岗军的精神支柱,他的宽厚让这支农民起义军保持着凝聚力。李密为巩固权力,不顾“兔死狗烹”的忌讳,悍然诛杀翟让及其核心部下,不仅寒了老将士的心,更让徐世勣、单雄信等将领心生戒备。此后瓦岗军看似统一,实则派系林立,关键时刻离心离德,邙山之战中单雄信的按兵不动,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2. 战略短视:错失良机,腹背受敌
李密最核心的失误,是始终纠结于攻打洛阳。麾下谋士柴孝和曾建议他“西袭长安,抢占关中”,这与李渊的战略不谋而合。关中地势险要,粮草充足,是问鼎天下的根基。但李密固执地认为“洛阳未下,不可西进”,浪费了最佳时机,让李渊趁机攻占长安,站稳脚跟。后来又错误地联合隋廷夹击宇文化及,导致瓦岗军元气大伤,最终被王世充捡了便宜。
3. 刚愎自用:骄傲轻敌,众叛亲离
巅峰时期的李密,逐渐迷失在权力的光环中,听不进不同意见。邙山之战前,部下多次提醒他“王世充狡诈,需防偷袭”,但他刚击败宇文化及,骄傲自满,连军营壁垒都不修筑,最终被王世充打了个措手不及。降唐后,又因不甘屈居人下,不顾实力悬殊贸然反叛,最终走上绝路。
反观李渊父子,不仅战略清晰,更懂得笼络人心。李世民对秦琼、徐世勣等瓦岗降将推心置腹,委以重任,让他们甘愿效命;而李密却对旧部猜忌提防,厚此薄彼,最终众叛亲离。
李密的故事,印证了“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千古真理。他有掀翻乱世的谋略,却没有驾驭群雄的格局;能聚起百万之众,却不懂如何凝聚人心。20万大军、三大粮仓、绝世名将,这些看似牢不可破的“王牌”,最终都因他的失误化为泡影。

真正的强者,不仅要有破局的勇气,更要有容人的格局、清醒的头脑和长远的眼光。权力可以带来一时的辉煌,却无法弥补人心的离散;谋略可以赢得一场战役,却不能挽救战略的失败。
参考文献
1. 《旧唐书·李密传》(刘昫等著)
2. 《新唐书·李密传》(欧阳修、宋祁著)
3. 《资治通鉴·唐纪一》(司马光编著)


![司马懿:需要我来回答不[吃瓜]](http://image.uczzd.cn/4722309673445035490.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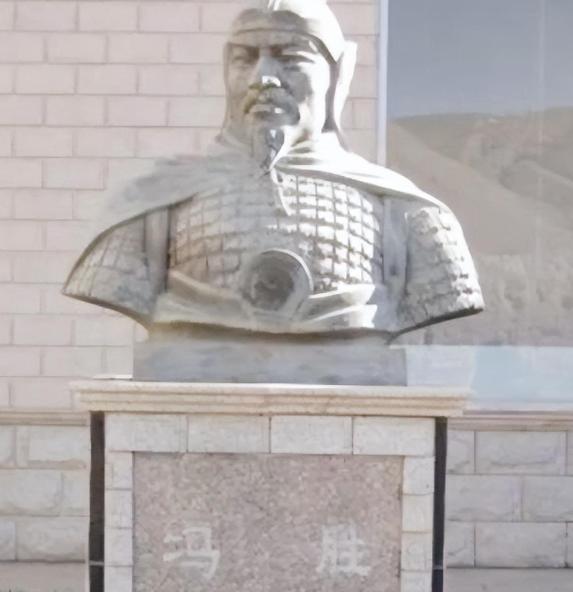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