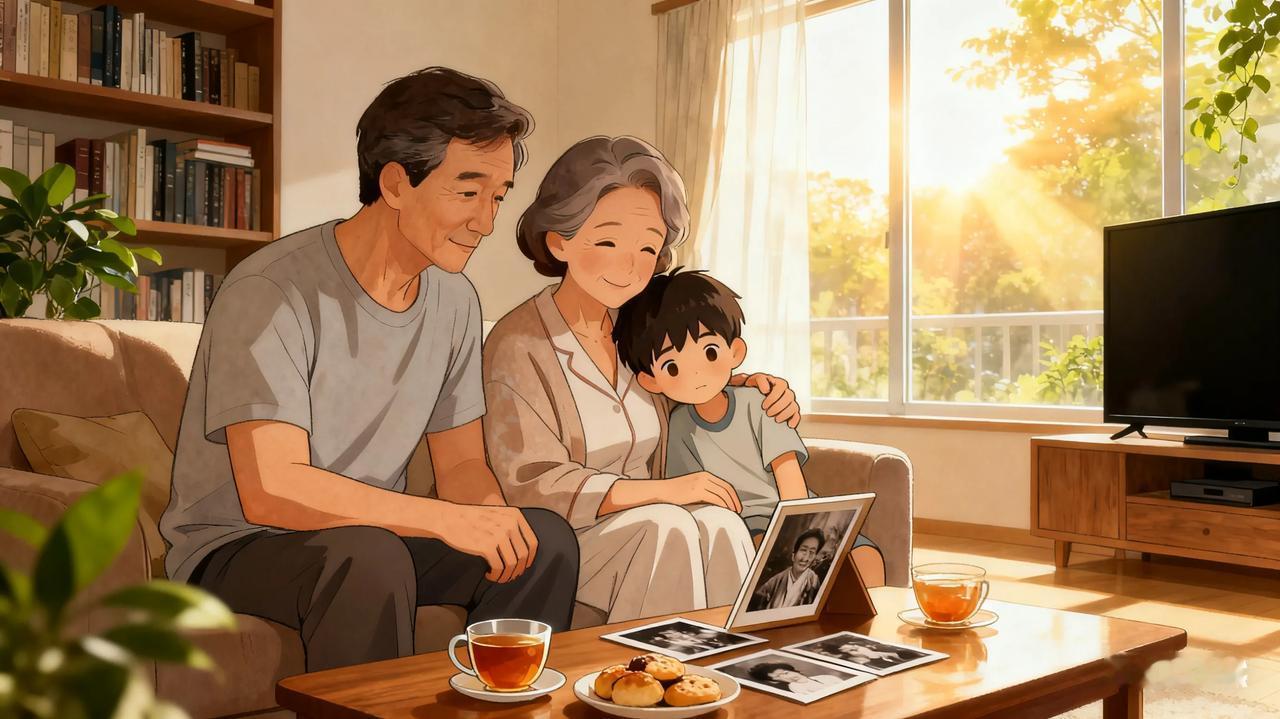交朋友嘛,谁都不愿意碰上那小气吧唧的。
当然,这倒不是说想图他点什么东西,而是他身上那份算计和拧巴,让人心里着实不痛快。
往深了讲,小气这事儿,不单单指钱上,更在情分和心胸上。
要是你身边的朋友有下面这三件“小事”行为,那八成是有点小气了。

钱上分明过了头,人情味儿就淡了
朋友之间嘛,平时聚会什么的,总会有经济来往。
但是谁心里都清楚,这些个东西,讲究的是有来有回,大体上差不多就行。
但是吧,那些小气的人,他们的心里可不会想得这么简单,算盘打得比谁都精。
一次两次,你觉得是懂过日子似的,但回回如此,你就会觉出味儿不对了。
那份精明像是无形的墙,最后把人情味儿都隔开了。
明朝有个文人叫李贽的,他有个朋友叫耿定向,是当时的理学大家。
两人后来闹翻了,而李贽曾经就在书信里就抱怨过耿定向一件事:
平日里高谈心性,一副超脱物外的样子,可真到了涉及利益、需要他实际支持的时候,便锱铢必较,半步不让。
李贽觉得,这种人在大道理上无比慷慨,在实实在在的小利上却寸土必争,是一种更深层的,也是令人厌恶的“小气”。
尽管李贽他自己后来生活清苦,却常常接济更穷的学生朋友,在他看来,钱财流通起来,人情才能活络。
古人云:“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
的确,在钱上看得太重,攥得太紧,人心自然就散了。
英国有句俗语说:“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在便士上精明,在英镑上糊涂。为小钱计较,反而会误了大局。
其实吧,一个人在对待金钱这份上,若过于分明,不是谨慎,是狭隘。
甚至还暴露了自己内心的匮乏感,总觉得给了别人,自己就少了。
殊不知,人情上的投资,回报远大于那几分几厘。
自己的事是大事,你的事是闲事
这种人吧,他的事再小,也是火烧眉毛的急事,你得放下一切来帮他。
可一旦你有事,哪怕再重要,再着急吧,在他那儿也常常是“等等再看”、“最近太忙”。
他找你,随叫随到,你找他,千难万难。
以至于对于这种自私自利,还小气容易得罪的人,在真相看来,那份关心和帮助,从来都是单向的。
五代时期有个叫冯道的人,历仕数朝,人称“长乐老”。
他在为人处世上可谓是极其圆滑精明,也善于保全自己。
史书曾这样评价他,对上级和能给他带来好处的人,他的言行举止则是极尽周到。
但是吧,对下属和无关紧要的人,则颇为吝啬,不愿多费一分心力,势利眼无疑。
他的精明算计全部用于“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事务上,至于那些对他无益的“闲事”,则懒得理会。
其实吧,这种待人接物上的“小气”,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
《论语》里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凡事学会将心比心,才是交往的基础。
而小气的人,信奉的往往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可以说,一个人在情分上的小气,比金钱上的小气更伤人。
因为自己小气的行为会清晰地划出了界限:你是你,我是我。
最终,所谓的朋友,不过是成了自己单向的索取,后面也会失去相互扶持的温暖。
连一句好话,都舍不得给你
人与人之间有时候的相处,最让人憋屈的,还不是钱和事,而是话。
你取得点成绩,满心欢喜跟他分享,他不但不为你高兴,反而立马泼冷水。
甚至呢,还会挑出各种毛病,或者轻描淡写地说“这没什么”。
你要明白,他这不是心直口快,他是见不得你好,舍不得那几句不要钱的赞美。
北宋文人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有个叫吕惠卿的官员,最初极力巴结奉承王安石,被称为“护法善神”。
但是后面他觉得自己羽翼丰满,能取代王安石时,便立刻跟他翻脸,在皇帝面前极力诋毁、中伤王安石。
后来吧,王安石复相,吕惠卿又写信极尽讨好,被识破真面目之后,王安石直接扔还。
吕惠卿这种人,在连口头上的认可和支持,都要计算着往后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
一旦得不到给予,就过河拆桥,无论做什么,都只是为了换取最大利益。
可满足了之后,有朝一日一旦无利可图,便吝啬到一字不言,甚至反咬一口。
古人讲究“与人为善”,“成人之美”。
由衷地赞美别人的成功,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气量。
赞美上的吝啬,暴露的是自己内心的嫉妒与贫瘠。
一个连口头认可都舍不得给予的人,他的内心是荒芜的。他无法欣赏别人的风景,也永远种不出自己的花园。
▽
我们交朋友吧,图的是个轻松愉快,是那份相互支撑的情义。
若一个人在钱上算尽,在事上躲闪,在话上刻薄,那这份交往就成了自己心里上的负担。
而小气的人吧,其实穷的不是口袋,是心胸,是心穷。
遇到这样的朋友,我们则要适当远离,甚至断交,这也不是什么势利,是一种聪明的自我保护。
余生,把你的热情和真心,留给那些在金钱上不让你难堪、在事情上愿意为你搭手、在言语上能给你温暖的,大方的人。
这样,我们自己也能活得自在,踏实,随性,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