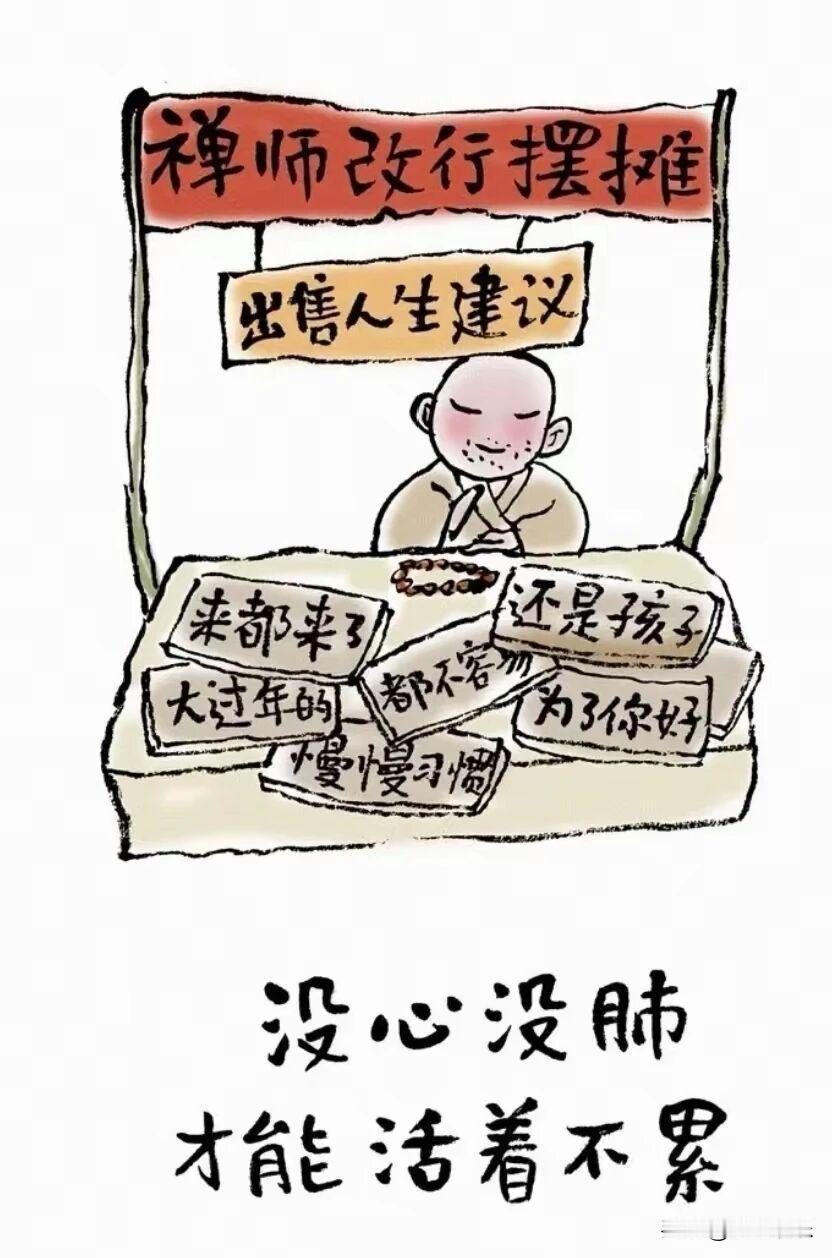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出身没落大家庭,童年在父母反目、继母苛刻中长大,又经历与胡兰成的失败婚姻,她对亲情和婚姻已有一种本能的戒备。 三十多岁时,她断开与父亲的关系,只身赴美,在公寓里接校对翻译养活自己,一边写作,想在新大陆重新站稳。 为了换取一段安静写作的时间,她申请进入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那里给艺术家短期住宿和创作空间,也让她遇见了比自己年长近三十岁的作家赖雅。 这个同样境况窘迫、带着女儿的老人懂得她的文字和孤独,两人在交谈与书信往来中渐渐靠近。驻留结束时,他先离开,她临走前把手里大半积蓄留给他。 不久,她在纽约被告知怀孕。那年,她三十六岁,他已年过花甲,一个靠稿费和校对费勉强维生的华人女作家,一个只剩退休金的老作家,眼前首先是房租和账单。 赖雅提出结婚,却明确表示无力抚养孩子,希望把这个生命终止。现实的冷酷和她对做母亲的迟疑叠加在一起,她知道,任何浪漫想象都经不起细算。 她从唐人街带回一瓶堕胎药,药瓶放在写满批注的稿纸旁,医生的纸条夹在一摞账单里。那天屋里光线暗沉,她长时间盯着药片,最终端水吞下。 剧痛袭来时,她像童年无数次那样独自咬牙熬过去,直到感觉到那个尚未出生的生命离开身体,只是低声吐出一句“终于下来了”,然后把那团血肉丢进马桶,任水流冲走。 同年8月,他们到市政厅登记结婚,只领了一纸证明。婚后,他们在简陋公寓里一边写作一边挣生活费,她翻译《红楼梦》和旧作,他写散文,收入不多,却勉强支撑房租与日常。 偶尔到唐人街吃一碗馄饨,聊起上海旧事,是他们少有的温暖时刻。对生育,她不再认真考虑,把尚未给出的爱转移到书页上,在小说里反复书写母性与命运。 很快,病痛逼近现实。赖雅先后多次中风,最后瘫痪在床,需要长期服药和照料。她卖掉母亲留下的古董首饰,频繁搬家,在看护与写作之间来回奔波。 白天给他翻身喂药,推着轮椅晒太阳,夜里守着打字机赶稿,那个曾在上海滩衣着精致的才女,变成为生活奔忙的看护者和翻译者。 1967年赖雅去世,这段维系十一年的婚姻告终。送走丈夫后,她没有重新投入热闹人群,而是把自己退回更狭窄的世界。此后,她辗转香港和美国几座城市,最终定居洛杉矶,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来,常为房间可能有虫患而焦虑,房里堆满纸箱,生活简到近乎清苦。 外界看到的,是她写出的《倾城之恋》和天才女作家的名号。现实里,她把几乎全部心力沉入文字,考据《红楼梦》,翻译《海上花列传》,反复修改旧作,让纸张成为唯一可托付的“子嗣”。纽约那瓶药,并不是惊心的戏剧桥段,而是在有限条件下做出的选择。她没有多加辩白,只是在此后漫长的孤独岁月里,把愧疚、温情与无奈,一点点写进那些冷静的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