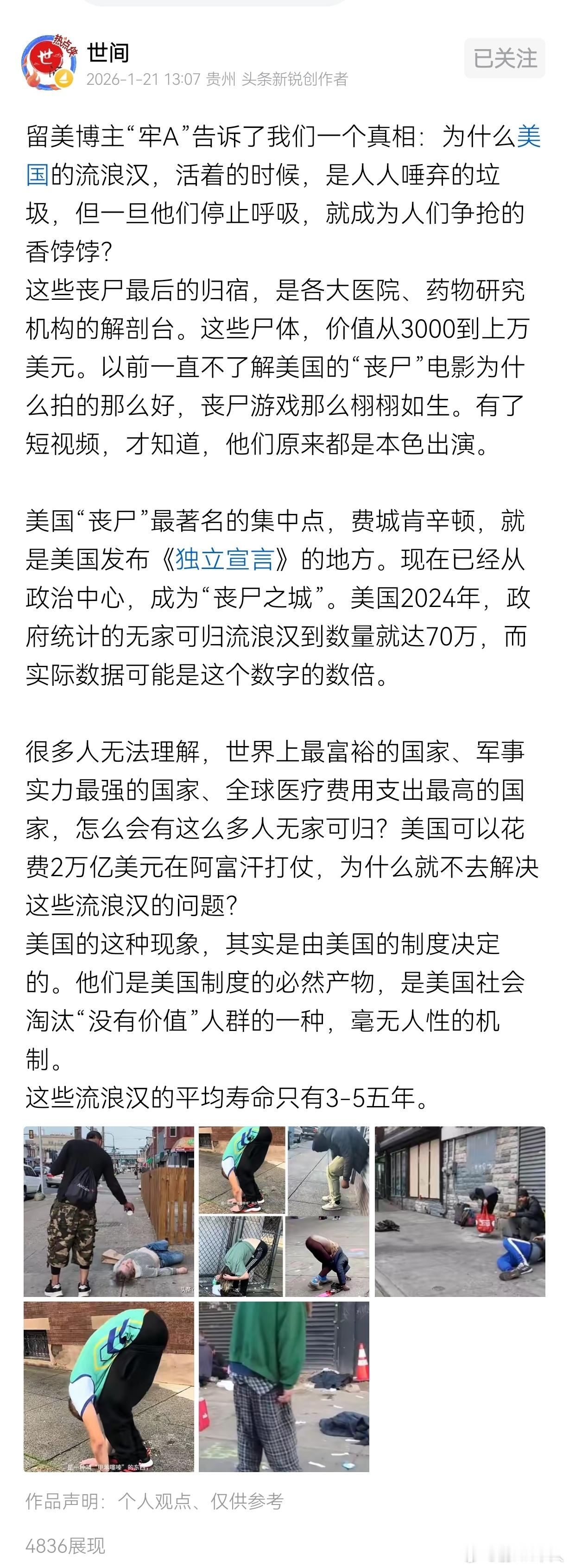马晓春不认为自己是聂卫平徒弟,这是不是“忘恩负义”?和中华的传统美德相悖吗? 2026年1月,“棋圣”聂卫平的告别仪式上,围棋界名流云集,唯独缺席了曾与他并称“聂马”的马晓春九段。这场缺席让一桩跨越半个世纪的公案再度发酵:马晓春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聂卫平的徒弟,只认可师生关系,这究竟是坚守边界的清醒,还是背信弃义的凉薄?是否与“尊师重道”的中华传统美德相悖?答案藏在师徒关系的时代语境、制度背景与人性复杂的交织之中,绝非简单的道德评判所能涵盖。 要厘清这一争议,首先需界定传统师徒关系与现代师生关系的本质区别。中华传统伦理中,“师徒如父子”的观念根深蒂固,“天地君亲师”的排序赋予师父近乎亲情的伦理责任,确立师徒关系需经过庄重的拜师仪式,伴随“传道授业解惑”的全面培育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终身义务。而现代师生关系则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多为特定阶段的知识传授关系,更强调教学相长与人格独立。聂卫平与马晓春的交集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78年国家队推行“一帮一,对儿红”制度,聂卫平受组织安排指导年少成名的马晓春,手把手带他复盘、实战,累计对弈上百盘,从让四子逐步降至让三子,这份指导无疑为马晓春的棋艺精进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种基于体制安排的“传帮带”,本质上是教练与运动员的工作关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契约——既无拜师仪式,也无明确的师徒名分约定,更不符合当时“反对封建糟粕”、不提倡传统师徒制的时代氛围。 马晓春拒绝“徒弟”名分,并非否定聂卫平的指导之恩,而是对关系性质的理性界定。在聂卫平逝世后,马晓春发表千字长文《我与聂老早年二三事》,详细回忆了当年受指导的点滴,明确称聂卫平为“永远的老师”,言辞间满是敬意。他始终强调的是“师生有别”:聂卫平的指导是体制内的教学责任,自己的成就更多源于后天钻研与赛场拼搏,不愿用“徒弟”名分捆绑彼此的人格与成就。这种态度背后,既有天才棋手特立独行的性格因素,也有对关系边界的清晰认知。反观聂卫平的“师徒执念”,更多源于老一代棋手对传统师门观念的坚守——他将倾囊相授等同于收徒,将自己的恩师过惕生逝世时马晓春未到场守灵视为“失仪”,本质上是用传统师徒伦理要求现代师生关系,难免产生认知错位。1993年围棋界明确恢复传统师徒制,聂卫平收常昊、周鹤洋为徒,马晓春则收罗洗河、邵伟刚为徒,这一标志性事件更印证了二者的同辈关系,若马晓春真是聂卫平徒弟,后续的收徒行为便会造成辈分混乱,显然与行业共识相悖。 评判是否“忘恩负义”,关键看是否践行了感恩的实质,而非纠结于名分标签。传统美德中的“尊师重道”,核心是铭记教诲、感念提携,而非形式上的名分依附。马晓春虽不认可“徒弟”身份,却以自己的方式回报着这份情谊:他在棋坛崛起后,与聂卫平展开的“聂马大战”成为围棋界的经典篇章,既推动了中国围棋的发展,也间接成就了聂卫平的“棋圣”地位;在聂卫平晚年,他虽因过往芥蒂减少往来,但始终保持着对前辈的基本尊重。至于缺席葬礼引发的争议,更需回归人情常理:葬礼的核心参与者是至亲,旁系亲属或友人到场是情分而非义务。马晓春以“担心感冒”为由缺席虽显生硬,但他通过挽联、悼念文章等方式完成了悼念,未必符合大众期待的“尽孝”形式,却也履行了学生对老师的基本礼数。将这种选择扣上“忘恩负义”的帽子,本质上是用传统师徒伦理进行道德绑架,忽视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多元性与自主性。 更深层的争议,实则是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的适应性演变。“尊师重道”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内涵,从未过时,但它的表现形式理应与时俱进。在封建宗法社会,师徒关系承载着技艺传承、生活照料、伦理延续等多重功能,名分绑定是必要的;而在现代社会,人格独立、关系平等成为主流价值观,师生关系更多聚焦于知识传授与精神引领,感恩的表达也应更注重实质而非形式。马晓春的选择,恰恰体现了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他铭记指导之恩,却不盲从名分绑架,用理性界定关系边界,用文字传递感念之情,这与“忘恩负义”毫无关联,反而彰显了对美德本质的深刻理解。反之,若将“徒弟”名分作为道德枷锁,强求他人履行超出关系性质的义务,才是对传统美德的僵化解读。 半个世纪的“聂马公案”,终究是时代语境与个人观念碰撞的产物。马晓春不承认是聂卫平徒弟,既非忘恩负义,也不违背中华传统美德——他坚守的是现代师生关系的边界,践行的是实质意义上的尊师之道。传统美德的生命力,在于其核心精神的传承而非形式的固守。“尊师重道”的真谛,从来不是名分上的依附,而是心底的感念与行动的回馈。这场争议更提醒我们:在评判他人的伦理选择时,应摒弃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结合时代背景与具体情境,方能读懂人性的复杂与美德的多元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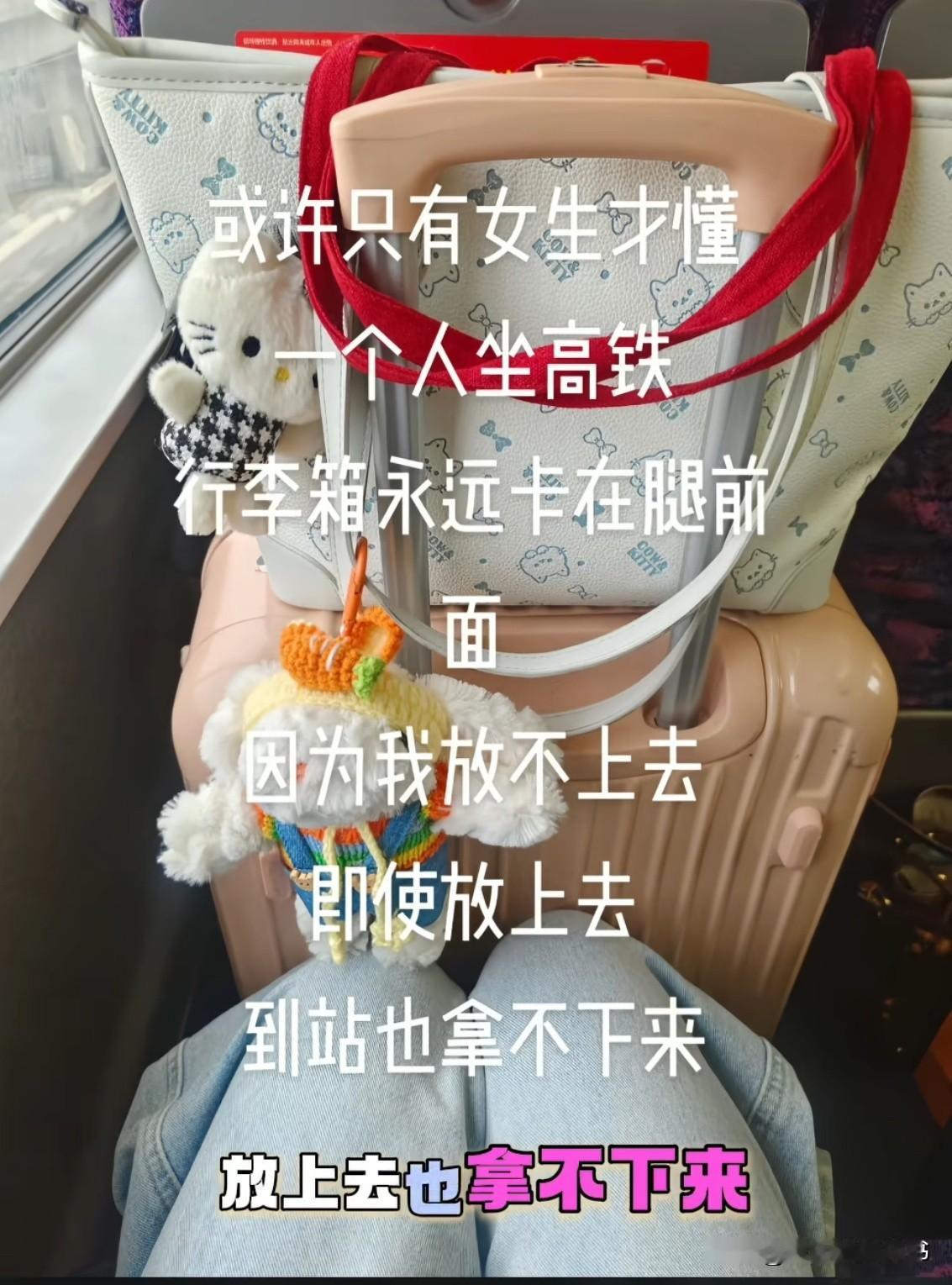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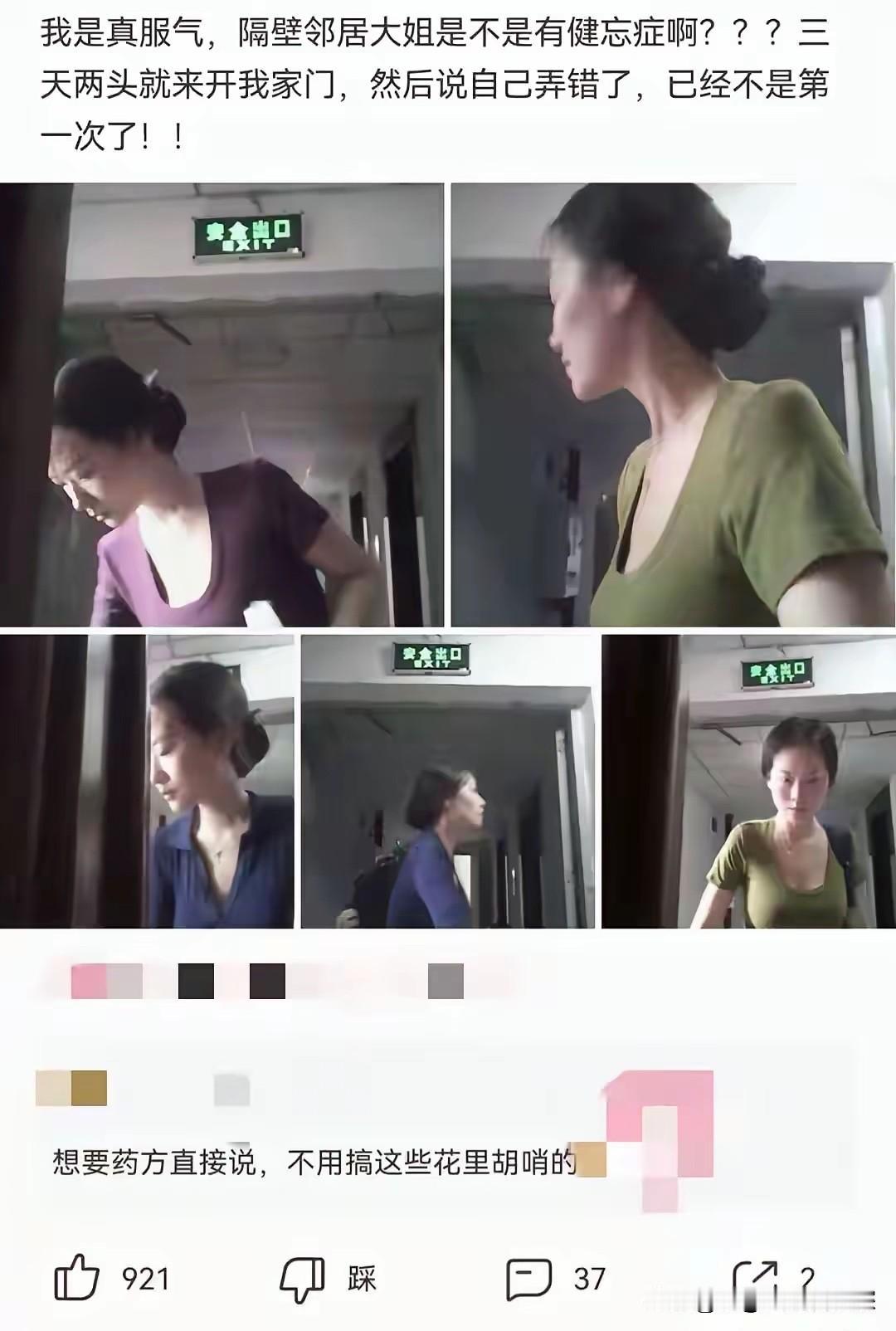
![就是明知道是现代的[吃瓜]](http://image.uczzd.cn/9214646918951723550.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