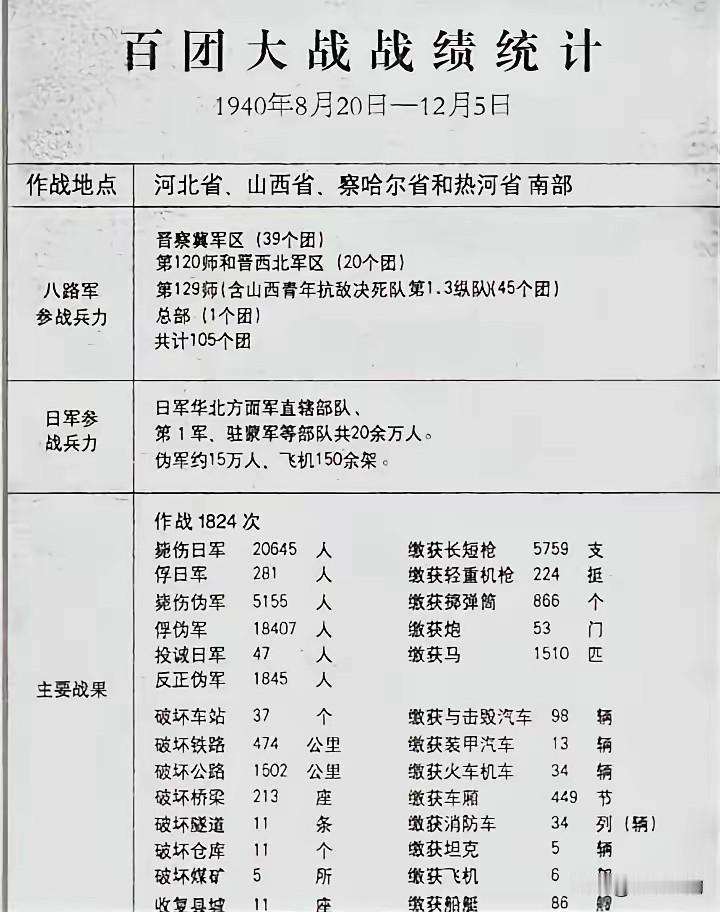鬼子让她招,她就真招了。 老虎凳、烙铁都招呼上了,她说,我说,我全说。 周三傍晚,道里区的粮栈有接头,她还把我们同志的名字,一个个报了上去。 只不过,报的都是已经牺牲的同志。 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一个遍体鳞伤的女人,用最平静的语气,给一群如狼似虎的鬼子,导演了一场注定空无一人的大戏。让他们像傻子一样,在一个空荡荡的粮栈外,苦等一夜。 这是何等的智慧和胆魄?这根本不是酷刑能摧毁的意志,这是把自己的命当诱饵,把敌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更绝的还在后面。 她丈夫,是个汉奸。她怎么做的?她用一封“密信”,故意让鬼子截获,信里全是她丈夫通敌的“证据”。 借刀杀人,杀的还是自己曾经的枕边人。 那一刻,她心里该有多疼,又该有多痛快。 1939年的哈尔滨,曾经穆棱县的“田大小姐”,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疯女人”。 她挎着那个装满情报的蓝布包袱,走在道外区的街上时,可能就没想过能活着看到胜利。 有时候我们总说信仰,到底什么是信仰? 可能就是,在所有人都觉得你疯了的时候,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又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