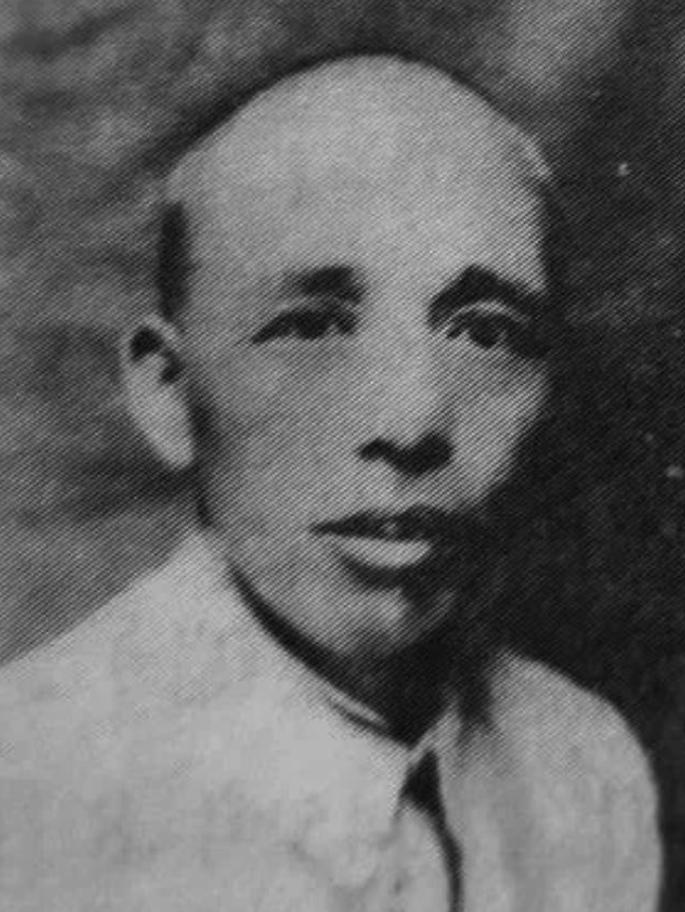1933年,红25军军长吴焕先率部途经家乡,路上遇到一具女尸,有人翻转身尸体,他走近一看,脸色大变,因为这具女尸,竟是他的妻子。 在黄安,一列行军队伍里,红25军军长吴焕先勒住马缰,目光落在路边那具盖着破草席的女尸上。 草席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半截熟悉的蓝布衣裳。 当他亲手掀开草席,看清那张脸时,那竟是他的妻子? 1926年,吴焕先加入共产党。 在黄安组织农民运动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就盯上了他家。 1930年,父亲吴维棣和大哥吴尚先被敌人绑在村口槐树下杀害,母亲带着他和弟弟躲进深山,靠野菜树皮活命。 曹干先嫁过来时,吴家只剩三间漏雨的土坯房。 她没抱怨,反而把陪嫁的银簪当了,买了纺车。 白天帮人洗衣,夜里纺线织布。 “你放心去闹革命,”她把织好的土布缝成衣裳递给他,“山里冷,这布厚实,能挡风。” 后来部队转移,吴焕先总穿着这件蓝布衫。 1933年部队途经家乡,他本想绕路看看母亲和妻子,却撞见这具尸体。 吴焕先用袖子擦去她脸上的尘土,突然想起离家前夜,她挺着微凸的肚子说:“等这孩子生下来,咱们就叫‘红军’,让他跟着你干革命。” 可孩子还没出世,她就饿死在了送粮的路上。 曹干先的死,不是意外,是为红军“省”出来的。 1933年红军缺粮,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 曹干先和婆婆吴老太得知后,背着破筐挨家挨户乞讨。 婆媳俩三天没吃一粒米,靠喝凉水充饥,才换来半筐红薯和玉米。 警卫员后来回忆,那天曹干先到临时指挥所,把筐护在怀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笑着说“给同志们垫垫肚子”。 当时吴焕先正召开作战会议,为前线战事焦头烂额。 警卫员本想汇报此事,见他眉头拧成疙瘩,便把粮食悄悄收进库房,打算会后禀报。 等吴焕先开完会,只看见空筐和警卫员红着眼眶的模样,他捏着筐底的红薯皮,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几天后部队返乡,路边那具尸体就是曹干先。 她手里还攥着半块红薯,胃里空空如也。 更让人心碎的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已四个月大。 吴焕先的悲痛,早被家人的血浸透了。 父亲吴维棣是个老实佃农,租种地主三亩薄田,交完租子全家喝西北风。 1926年吴焕先参加农会,父亲偷偷把攒了三年的鸡蛋卖了,换了笔墨纸砚给他:“你要真能为穷人争口气,爹死也闭眼。” 可第二年,地主带着民团砸开他家大门,把父亲和大哥吴尚先吊在槐树上毒打,逼问吴焕先的下落。 父子俩宁死不屈,被乱棍打死,尸体扔在村口的臭水沟里。 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小侄子躲进山洞,民团放火烧山,小侄子被烟呛死,母亲从此落下咳血的毛病。 曹干先嫁过来后,一边照顾婆婆,一边帮党组织传递消息。 她把情报藏在发髻里、缝在婴儿的襁褓中,多次掩护受伤的同志脱险。 敌人抓不到吴焕先,就把怒火撒在她身上。 抄家、辱骂、逼她说出丈夫去向,她始终咬着牙:“我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会说!” 这些血债,吴焕先都记在心里。 他把妻子的铜哨子挂在脖子上,带着红25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打游击,重建被敌人打散的部队。 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后,他临危受命担任红25军军长,带着3000多人突围,在陕南开辟新的根据地。 发现妻子尸体那天,吴焕先没哭出声。 他蹲在路边,用军帽盖住妻子的脸,对身边的战士说:“把她埋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跟我父亲、大哥葬在一起。” 说完翻身上马,继续率部行军。 那天晚上部队宿营,他一个人在帐篷里坐了整夜。 可第二天清晨,他又出现在队伍前面,腰杆挺得笔直,仿佛昨夜的悲痛从未发生。 战士们知道,军长心里比谁都疼。 父亲、大哥、妻子、未出世的孩子,都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可他更清楚。 “哭完了,还得接着打反动派。只有把他们都赶跑,才对得起死去的亲人。” 后来红25军长征,他带着部队冲破敌人围追堵截,一路打到陕北。 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他为掩护部队渡河,被子弹击中胸部,牺牲时年仅28岁。 临终前,他攥着那枚铜哨子:“干先,咱们的孩子……”,手却永远垂了下去。 有人说革命是“抛头颅洒热血”,可对吴焕先来说,革命是妻子饿死时护着的半块红薯,是父亲大哥吊在槐树上的尸体,是孩子还没出世就被夺走的命。 这些痛,他没说出口,却刻进了每一次冲锋、每一次战斗、每一次对“好日子”的期盼里。 就像他常说的:“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为了让更多人家不用再经历这些。” 如今,黄安的孩子们不用再躲藏,不用再挨饿,不用再看着亲人死在敌人手下。 这大概就是吴焕先和曹干先用生命换来的“好日子”。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客户端——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 ▎军魂吴焕先 澎湃新闻客户端——【党课开讲啦】百年奋斗丨吴焕先:鄂豫陕苏区创建人)